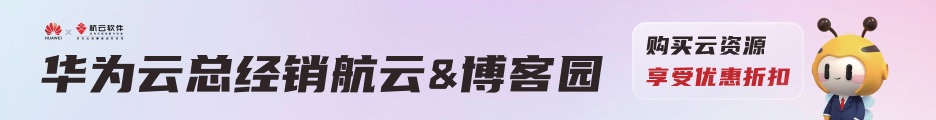十九、只诉温暖不言殇
有生之年,只诉温暖不言殇,倾心相遇,安然相伴

四十岁生日,一个人走在异乡城市,突然发现这半生活的梦一样不真实。
总是回想往事,想起八十年代那透明时光,像一只蝴蝶在那片天空翩飞轻舞,寻找那个年代的每一片印记。
许多年了,我发现我的根仍在那里,我的心跌落在一个根本回不去的年代。我走在马路上想着牛嘶马叫的田野,在咖啡馆遥思河边泉水,在高楼间想那开满喇叭花的篱笆,在暖阳中遥望北方的雪花,在高楼大厦间迷失了脚步。
我在电话的这头笑着流泪。
我想我太过于感性,以致总是陷入那早已回不去的过去。
这是我的原罪,也是我的宿命。
我们这代是幸运的。
出生赶上分田到户,赶上八十年代政治清明风调雨顺,而不至挨饿受冻,也没觉什么动荡。
待长大懂事,父辈开始出去打工,又避免了留守儿童的盼望与悲哀。
想起达、四叔出去打工时,辉娜景武那么小,老子辈也是负着思念在外,孩子们咋会不想!都是感叹时事变化,竟都是那么剧烈。
九十年代开始人心思变,田野再无昔时多彩。扯了电有了电视,孩子们便不再出去玩。
所以总是想起那段时光,与童年一起陪伴,刻骨铭心,永世不忘。
我生在一个有担当的大家庭,父辈对老人孝道,对孩子辈亦没得说。

大学放假期间去厚街,五叔看我鞋破,脱下脚上好鞋给我穿,带我去白濠市场买鲶鱼,亲自下厨,当时父亲低谷爹达四叔姑父怕我没钱,比住给我。
刚个小怕是媳妇不好寻,张庄郭老黑有个头儿,只待刚吐口同意,四叔活都不干五找郭老黑,就差没怼他,这样水英来了我们家。
后来刚对婚姻有点自己看法,奶拿起电话日娘八辈不留情面去谲,为孩子们可怜。
待辉楞中春丽,四叔也是跑前跑后张罗亲事,不遗余力,他对这些后辈们,当真没一点惜力。
涛盖房子,为宅子事,几个老子更是左右找人,解决问题。
爷奶头疼发热,住院输水,他们不管谁搁家,都是跑前跑后不懈怠,小姑离的近,更是前后照顾济事。
令别人羡慕啊,咋不好哪!
奶曾说过,啥时有空,坐那给她的过去原原本本地说一遍,叫我记下来。
奶里命生来坎坷,出生即被弃,捡了条命回来,在那缺吃少穿重男轻女人鬼不分的时代,如同弃儿,顽强活了下来。
七岁上俺家做童养媳,碰上爷脾气阁僚,后来又赶上大跃进大灾荒,苦啊,命真是苦!
这不是奶一个人的苦,而是她们那一代人背负的苦,生在战乱,长在祸乱,活在混乱,终于晚年赶上好的时候。却因打工浪潮,孩子们都远去,老人留守空巢。
我没法写一个人的苦。

爷何尝不是一样背负。他们那一代人所谓的多子多福,养了那么多孩子,拼死拼活干,积些家底给儿子娶个媳妇然后分家,送闺女出门,然后再拼着干,为后面的孩子。
以至爷奶说起五叔,心中竟是感激,因为五叔是自己搁东莞给五婶娶了。
老了,干不动了,五叔一成家,他们心里没负担了。爷脾气脸色,也渐渐缓了起来。
无压一身轻么!
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想当初苦难日子,能否预料如今子孙满堂?
我无从知道奶八十岁生日许的什么愿望。
想必对老人家来说,家人健康平安,应为最大愿望。

都过去了,再苦都过去了!现在与爷为伴,守在乡下老院,所有回忆已那么遥远。

相守一生没有诺言,就这样脚步匆匆,不离不弃……
每个人心里都有脆弱的一面。如果放大这种脆弱的话,没人想活。

我心底始终流着一股无法融解的悲伤,我不是一个快乐的人。
人的性格与生俱来。我生性静而无争,人的命运在你做出选择时候已决定。性格的弱点在年轻时犹能为盛气所掩,待中年渐弱,便更感觉怠倦。
那个午间第一次看见她的背影,本不自信的心,在刹那间沉得更无着落。
因为没有一个人,面对爱情,生来自信,青春无悔不死,是永远的爱人。
夫人家里排行老末,我是老大。老说法是性儿不搁八字不对,一个只会付出,一个只等收获。
我偏不信。
我一旦决定就不许自己后悔,岁月总在证实它所留下的古老预言,预言,一直在狠狠惩罚那些僭越规则的人。
是的,性格,与生俱来的性格,我想,这是宿命。
我也曾经温暖,我也曾经轻柔,只是你一再打击,叫我如何承受。
于是我渐渐凝固成形,于是我渐渐变得安静。
让那曾经炽热爱你的心,化为一颗拒绝溶解的冰,孤独,是我今生的宿命。
如果真有天谴,我们已在承受,那么十数年的分居生活也早该偿还,无悔当初相遇相知,爱情化为亲情。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回头发现我身上印记了太多母亲的影子,慢慢活成当初不喜欢的样子。夫人性格则与父亲有太多相似之处,我远离了父亲,却走进了另一个强势。
强势也无所谓,只要你有智商,可现实总在证明,这不过是个一厢情愿的奢望……
命运总像是不可预料的玩笑,笑我这半生寂寥!
父亲上了岁月,也落生身病痛,仍然坚持着干着。
九二年出去,至此在外二十六年。
对家仍然负责,对爷奶亦孝,只是性里争强好胜刚愎自用,不随年岁磨灭,仍然喜欢在酒后与人一较长短,头疼至极。
借酒发疯,令人避之不及!
母亲这些年都是照顾着姥爷,围着我的孩子们转,特别是朵朵,可谓一手带大。从乔坟到方城,从方城到南阳,为她的孙子孙女,付出无怨无悔。
什么才是人生啊?
父母一别二十多年,中间一起生活日子,屈指可数。不打了,老了,也知道开始关心彼此。青梅竹马,形容父母是再合适不过。
我们一家的生活,七零八散,是时代啊,还是我们的命运!
翻滚的时代,我支离的家庭。
与母亲通电话,她看到了这些文章,让我不要再写下去了。
她说这是个黑白不分的年代,不能说真话的时代。
我无声叹息。
她进城十多年,从方城到南阳,身子离开乔坟,怨恨仍留在心里。
当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正在凝视着你。
如果说我这半生有点收获的话,那是上天看我不算太懒的份上,在人生转折处,一点垂怜。

我是输在天格上。
三份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人之天格尤为重要,深刻于命理,它决定人能怎么走,走多远。
天性安静敏感,家庭有生无教,童年经历使我远离烟酒赌玩,性儿无争,久之发觉人之半生,工作之外无所爱好。
骑行之路,亦被交警堵在人行道上。
犹柔于进退之际,摇摆于得失之间。
于是对此世界,无深切感受,交游亦无心情,所为者,身后一个家。很难想象我这样的男人,如果连家都没有,会怎样存活于这个世上。
我与父亲当初一样,薪资留够吃饭之外,悉数上交。
我怕她们受冻挨饿。
至于我,一个人多年习惯,已无所谓苦与乐!男人不为家,枉立于天地,枉活于人道。
男人不爱护自家女人,枉负当初不计贫苦毅然相从。
我错过了留在这城市最好的机会。或者心里一直没有爱过外面哪一个地方,对以后也从未坚定,导致我半生依然漂泊。
人流越来越拥挤,我不喜欢这里,我的心遗落在回不去的地方,这是宿命。
四十岁,程序员生涯尽头指日可待。仍然能坚持做,只要依旧起早贪黑,我想我是倦了,倦在一天一天的早出夜归,这把椅子一坐十五年。
也倦在这没有尽头的离别。
我需要家,我需要孩子们,孩子们也需要爸爸,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爸爸,两个哥哥真讨厌,说好一起去偷糖,他们却要我去,偷回来还给我要。”
“爸爸,你敢惹我,老娘跟你没完!”
“爸爸,明天你能不能接我放学?站在天桥上就可以。”
“爸爸,是不是过完今天,你就要走了?”
“爸爸,你能不能不走?”
“……”
“爸爸,你会不会不要我们?”
“……”
“儿子,如果爸爸再工作三年,咱们就会有一笔钱,如果工作一年,就会有少些的的钱。你是要多些钱呢,还是要爸爸陪你们?”
“我要爸爸。”
“我也要你们……”
童话清澈,声声击我胸口,叫我夜不安寐,枕手待旦。
这是两个可爱的孩子,孩子是自己的好。

一年一年空许约,只为这生存艰辛。
十年前,我们犹为奶粉钱而愁,十年后,倾全家之力,在末线城市有了一些房产,落得一身债务。
这些债务,让我不能随意,男人得养家,这是男人存在的价值。
我的工作机会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因此,还是离别,他八辈的离别!
体检报告医生建议一年比一年多,该死球朝上。
我思归心急如焚,我怕我回去时候,他们再不需要我陪伴;我怕我陪伴老人时间,日日无多。
我坚持,为这生存。
如果落在方城我可稍从容,而去南阳,为孩子更好的教育机会,住房成本即刻压力,所以我得坚持,即便思乡极甚。
坚持吧!总是家在远方,归期可待。活着,几人可随心所欲!
“你的梦想是什么?”
“放羊。”
“为什么要放羊哪?”
“挣钱娶媳妇。”
“娶媳妇后哪?”
“生孩子。她做饭,我放羊。”
“生小孩来干什么?”
“放羊……”
我期盼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是几千年不变的农耕生活吗?一方土地,生生不息,长大生子,子又生孙,儿孙就近,亲戚遍布方圆十里。
地球表面这层土地一年两遍,翻去日月轮回,翻去生老病死,一眼可见这一生,是我们想要的吗?
那人来如燕人去如虹又为的是什么?我们与牧羊娃儿又有什么分别?不过是另一形式的放羊罢了。
是时代,永不停止的时代脚,我们生成一个伟大的时候,动荡的时代,它终结了几千年传统的农耕生活,丰富物质同时,也失去了很多的东西。
回忆录过程中,发生了许多事。
写《过年》篇时,25区城改,住处拆迁,另寻落脚,写《马庄》搬家,终至星海名城与同事合住。
写《岁月悠悠》时,公司过会,写《四叔相亲》时,上市公告。
至今1月18日,参加敲钟仪式。
必定是上天安排。
若是前年上市,我想夫人我们可能不会回撤。可是,类似莫须有的理由,没有过会。
如果我能再年青十岁,未来多么可待,可是没有如果,历史只会记录我们怎么做。

岁月禁不住太长等待。
空是思念积尘土,归期若彩虹。
然而既存思念,此情终究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