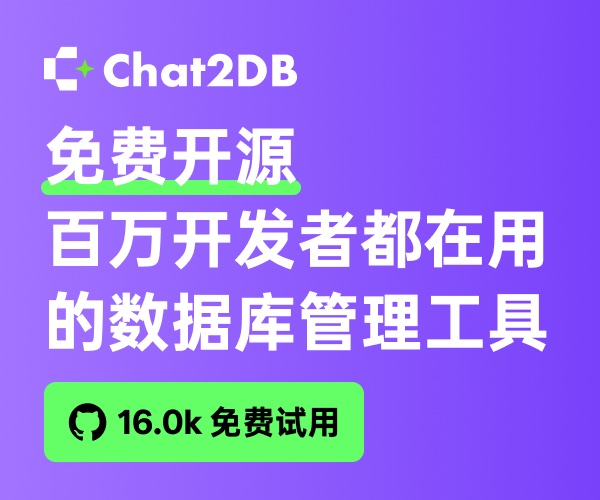十八、二十年后
我们每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是独自旅行,即使有人相伴,终究各奔东西

走着走着就散了,回忆都淡了
看着看着就倦了,星光也暗了
听着听着就厌了,开始埋怨了
回头发现你不见,突然我乱了……
昔日喧闹的村庄早已安静,像少年时那个秋夜。
奶家院子斜阳照黄花,猫狗慵懒依,叔姑我们的笑声犹在回响,我有幸出生在一个政治清明风调雨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时代,阅尽那透明时光。
如今为了生存,年青人多已背井离乡谋生于外,只在夏秋忙季与过年时分,才如候鸟般从各地回来,忙过欢过又飞走,留下老弱孤守村庄,而有的则一去再不回,留下旧宅空蒙尘。
房子越盖越漂亮,院墙也越垒越高,却再也没有当初没有院墙时的亲切。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离太久了,儿时故知再见半生,几句客套之后,竟不知还能说些什么……
田野安静只听见风吹过苞谷地的声音,地里再无当年喧闹,也没有了当年多样庄稼。这片土地带给人们丰富多彩的收获,也停留在了那个年代。
利哥和老常燕过成了一家,海生叔和霞姨走到了一起,李金淼寻去浙江,会贤姐嫁了唐河,海宇叔落了广州。
那天有人加我微信,牧童,标注海宇叔。我想是他心系故乡,忆那北河放牛的日子。
清慧国强哥海亮哥赵华姐红坡春果他们去了方城,有的去了南阳郑州,有的去更远地方,更多的是撇了老小去远方打工。
学五的铁砂掌功和屠龙刀技也恰到火候。


学全叔做了人民教师,从独树教到方城;小姑父搁基层一干几十年,杨楼古庄店博望来回转,司法岗位兢兢业业尽心尽责,终于感动中国上了央视露了把脸。
喔,想起来了,赖孩是他外号,大号张学豪。

回头看看已半生,都不再年青!
“威?是威不?“
搁金军吃过烩面,结账时候,我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
我以为我听错了。来去匆匆,我在方城停留时间太短,不记得有其它熟识的人,因此没有在意。
“威?是威不?“
又一声,很真切,我确定是在叫我,我抬头看向声音传的的方向。
烩面间,热气缭绕中,烩面师傅看着我。
“广伟叔?是你么?真的是你?”再见故人,我颇感意外,亦很惊喜。
“是我……”
几句话,几十年时光浮现。上次见他,是九五年,暑假去东莞找父亲,他在一家菜馆掌勺。
现在再见,面容轮廓依旧,只是不再年青。
后来听说回来在王庄转换开如源烩面城,再后来消息尽无,不想今日于此以这样方式再见,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他们三兄弟,广州不知何处,广献在家做村上工作。想想当初舅回来一时显赫之后老人黯然离即将,人生如梦令人无限感慨。
所谓三十年河东河西,时代变化太快,惟愿一切安然!
天之涯,地之角,故知有零落。
建国爷没了,二姑没了,长立爷也去了,仁义也早逝,学力伯学力母也没了,斌爷身体也不好了,海生叔身子也差了许多,叔们身上也落了伤病。
回看当年村庄,荒草没径,野树蔓生,老弱留守,触目尽凄凉。
建德爷也没了。
都说他是个好人。每个人都有个标签,就像说起我会是善良一样。
好人与善良表达的意意差不多,都是没用。
他是爷的叔伯弟弟,一生与随德爷相依为命。他比父亲没大几岁,少时聪颖但是木讷,老三届,独树高中毕业,当过红卫兵,跑过大串联,见过世面。
听说他年青时相过亲,到姑娘家他只拿本书在那看谁也不搭理,结果不了了之。
与宾爷给一腔文化付与家乡教书育人不同,他是肚里有嘴里倒不出来,于是开了个代销店儿,待过年时候卖红纸与写对联,以钢笔字写法写毛笔字,那些年半截庄子对联都是他写的。
那时候也是他家最热闹时候。人没事都喜欢过去玩,都是没用人,说说话儿扯扯淡怪得劲儿。
后来代销店叫仁义赊得也开不下去了,他就喂猪,再后来粮食涨的喂猪也不赚钱了,他算是停了下来。
父亲爹达叔们出去打工,家里但凡有刨地晒粮食这些力气活,喊他或他瞅见,不吭声就帮我们干。

他成天乐呵呵,没有脾气,守村一角,与世无争。
村里偶尔来了神经不正常的女人,有好事者给他领家里,他乐呵呵收留。再后来,他领回来个瘸子奶奶,算是老了有个伴,日子悠悠过。
过年过节回去,多少留点钱给他,他是死活不要,塞他口袋里。

好人通常没有好命。
食道癌。他这样的好人,不应该遭此天谴有口不能食,像张姥娘一样,都是多么善良的人,偏遭遇此绝病,天心冷漠。
终究是一天一天衰弱下去。拴叔那些姑们带他去化疗,以期望延续生命,但都是徒劳。
最后的日子,奶每天做好饭掂过去,八十多岁的婆婆,照顾她六十多岁的弟弟,想想年青时光看看眼下,着实令人心酸。
他依然乐观。我终于有空回去了一次,谈笑依然,乐呵如旧,只是生命眼可见尽头,心生悲怆。
终于还是去了!
知此消息,我良久无语,往事浮现,给父亲通电话,家人互通消息,悲伤不已,却是没能赶回去送他一程。
愿他在天堂安好……
爷奶守住这个院子,守住我们对家的思念。
爷奶在家等着我们。

父亲还在外面拼搏着,母亲帮我带孩子们。
爹娘在家带孙子们,三娘也带孩子,达四叔还时而出去打工,小姑五婶带孩子们去了方城,待周末了回来看看。
刚涛辉常年在外头打工,景武在求学的路上越走越远,昔日漂亮的孩子越长越倒处,表弟表妹们也都有了自己事业。
我呢,也是常年流落在外面,任这思念给我淹的透不过气来。
曰归曰归,心亦忧止;曰归曰归,岁亦暮止!
不打了,打不动了,都不打了。
几十年时光足以磨灭一切。当初年青,戾气至今耗尽,爱情化为亲情,以老为伴。
故人似客来。


二十年,青葱姑娘成大婶,少年成大叔,这一身肥肉头顶半谢的,是当年风华绝代的五叔。
五叔烧火,五婶下苞谷糁儿。
我们离家太久了,老宅尽管修葺一新,但已少人气,于是每次回来小停,就在奶家院吃住。小姑四婶三娘五叔五婶不管谁在家,都是褊起袖子站锅台做饭,多是爷烧锅,一家人忙活而热闹,如当年院子多欢笑,只是容颜改。
奶前后忙张个不停,脚下生风。
从这里出去,仍然象当初一样再回来这里。本就是这里的人,却归来似客,岁月啊变化太快!
不想走啊,这里是家,是我们长大的地方。
反正能多待就多待,刻在骨子里的眷恋,岁月你如何消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