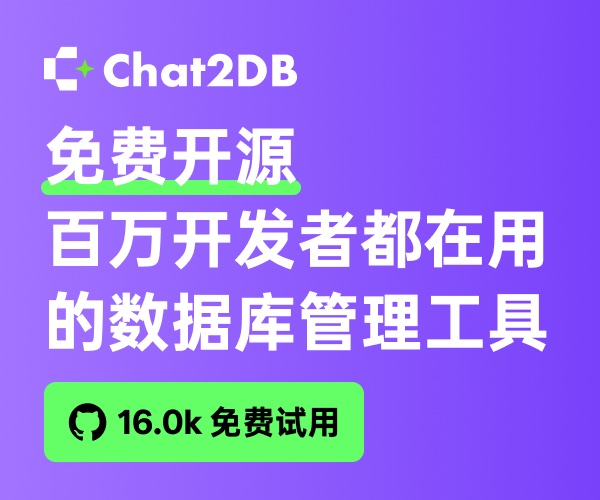十三、做瓦做回个花娘
父母之言,媒妁之约,抵不过那晚的月色轻柔……

一张槐木瓦架,一条生铁瓦杠,两个人。
水泥掺沙加水和好,四叔铲一铁掀堆到架上的覆纸瓦模上,达翻过铁杠给水泥推平,再翻过来推瓦形。三五次下来,瓦形初显,撒上一层干水泥,瓦杠一推,一片瓦就成形了。达脚底一压脚踏杆,给瓦升了上来,四叔托起瓦放旁边日头地儿晒,达再放瓦模,压纸,用两只小铁铲子铲架边上水泥上瓦模上,再推瓦,四叔回来端走,再铲水泥接住做。
半分多钟一片瓦,一会儿地上就晒出一大片来。待晒上半晌,水泥干了,立那一磕,一片水泥瓦就做成了。
就这样,达领住四叔十里八乡的做瓦,赚点辛苦钱。做完一家又一家,这一天来到了杨楼东邢岗,郭小孩姑父的老家。
达二十四五岁,虽柴了点模样却也不难看,大概做瓦姿势太过潇洒,或者那样的天气适合眼缘,这主家的女儿,楞中达了。
想是娘的开朗热情撩动达少年的心,从邢岗做瓦回来,达说要娶娘。
达与杨楼南张庄代英是有婚约的,代英肤白而恬静,奶无法面对这个现实,做瓦就做瓦吧,咋给媳妇也做回来了?在这个我家仍然不富足,娶媳妇仍然做难的年代,达这样意外的缘分却没给爷奶带来惊喜。
婚姻大事不是儿戏,咋给代英家开口呢?悔婚,对人家来说这是丢人事啊!
能有什么办法!
在达说要儿子还是媳妇这件事上,奶无可奈何只得要这个儿子,代英家的订婚钱也不要了。
缘分就是这么奇怪,兜兜转转,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遇见所遇见的人,也没有什么别的说,做瓦都能给娘领回来。
那一天,娘来到了我们家。
烫了波浪形的头发,一身得体的衣裳,坐在奶家院里木椅上,笑声爽朗,看着我们每一个人。达肯定给娘描绘过我们家,但对头一次来的娘来说,仍然陌生。
家人热情,谈笑风生,不觉间天已黄昏。喝过汤,娘大摇大摆地进了达的小西屋。
我们趴在窗户边看他们说话诉衷肠,达背对住门,娘一抬头就看见了我们,达也回过头来,我们一哄而散。
几回反复,冬季来临,婚期约定。
爷早开始出树做家俱,央人买菜打鱼做待客准备,亲友邻居能抽出手的都来帮忙。候姑父从耿庄回来,搁南沟一网下去捞出两条大鱼;小姑她老公公给凉粉缸里粉欠搅里转个不停。
帆布架蓬,砌砖为灶,摆桌借瓷,杀猪解肉,央厨子做菜烩汤。
我们小孩子啥活也伸不上手,不坏事就是帮忙,前窜后跳凑热闹。
娘是带住辉来的。
待客那天,邢岗送亲队伍浩浩荡荡,自行车一大溜,乱花媳妇乱里达娘吃不住。
陪送的床头柜很漂亮,镜子边上还有一串彩灯,可惜村上没有电。
那一天娘家人是光棍的,一个个喝的醉熏熏脸杠红,陪客者以给客人喝趴为荣,但因路远还要骑车回去,因此也是尽心为止。
亲戚领居则端盘拈水撒烟分酒,悉心待客。
曲终人散客人散尽,收拾桌椅,娘正式成为我们家一口人。
那夜我去压床,达给我叠了个小被窝,新被子很暖和我睡的很香,也没忘搁床上浇上一泡,不负我尿床精之名。
根据尿床的频率,我是尿床精,涛是尿床司令,他比我尿里还在行。
冬去春来,夏天时候辉出生了。
膘好里很,一身都是肉,逗逗他就哈哈大笑。我们都稀罕,一放学都去抱,挟住可沉啊~
“不兴说沉,说沉不好。”娘说。
人口多搁一锅里吃饭多少不方便。分家了,达娘分了西头一间房子还有北头一间灶火,他们上街赶集买回来做饭厨具,开始过起了小日子,但还经常搁一个锅里吃饭。
再后来达搁南边宅子盖了三间东屋,搬了过去,还养了头小牛犊。
日子平淡如水。冲突,也在日常生活中慢慢积累,娘性儿要强如其名,达调蛋娘不忍他。
那天又打了起来,激烈之极,难舍难分,耳巴子啪啪响,拉都拉不开。辉哭里哇哇叫,奶抱住辉谲住达,奶要再年轻些肯定上去撕他。
打人不打脸,娘伤住心了,哭住往东跑去,娘家在东南方向。奶叫五叔赶紧去撵,丢人事啊!
一路哭一路跑,过了三间房,眼前东沙河挡住去路。娘跳了下去凫水过河,五叔也跟住跳下去,哭住撵住。
秋水冰凉,到底也没给娘撵回来。
淇水汤汤,渐车帷裳,昔日的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化成滴滴泪水,随这河水东流。两千年前这首《卫风·氓》过淇水回娘家这节,竟如此贴切在娘的身上。
是啊!回去了,娘家兄弟会不会笑话?不管了,只要回家,那是长大的地方。
到底是娘家好,受了委屈总是有个去处,达挨收拾是少不了的。生气是生气,气过了还得回来带辉,孩子牵娘心啊!
再后来有了小娜,达也出去打工了,渐渐的也没那么多事了,日子就这样平静的过。
四叔挑起了干活的大梁。
爷奶整日劳碌不息,又开始给小姑准备嫁妆。
--------

2021年7月28日晚7点多,达突发心梗卒于舞钢工地,年五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