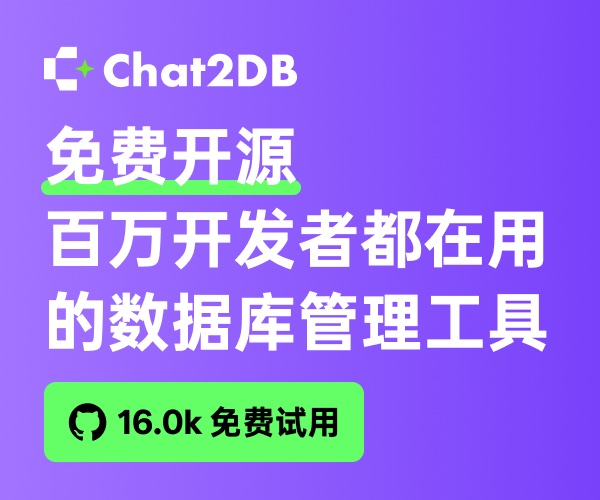十二、岁月悠悠
时光如水,岁月嫣然,流年不忘,斯人若虹。来自梦境深处的花朵,以最柔软的姿势,定格了这段时光

我的头脑到底寻常之极。
三年级结束连除法都学不会,考试及格都成问题,抄同桌朱小拴结果他也没算对。
于是父亲让我去前河小学溜一期,以期望多少有点奇迹,花了一大笔钱,二十一块。
黄土洼小学在前河东头,属黄土洼大队,黄土洼、前三里河、李庵学生在这里上学,所以我们也叫它前河小学,宾爷在那教书。
这是所老学校,教学质量值得期待,我的父母辈小学中学都学习于此。
宾爷和曹金玉校长说了说,渠锡和老师同意了我的转学要求,给我安排他儿子渠芳兴和娄天增一个桌。学校有板凳,桌下有斗。
从此我开始了在前河小学读书的日子。
早上与利哥一起出门,他到村西头学校,我继续往西上前河小学。早晚自习勤学不辍,每天与秀玲姑一起跑,西头双文叔、卫东、伟叔、全州也在这上,路上常碰到。
三里河,三里河!从我家出门到前河小学,刚好三里。
认识了曹延军、曹延锋、娄清杰、张延杰等一帮同学。课间去井边打水,他们给我喝。
很久以后我一直想,一位老师,一个父亲,给转学来的学生挤在自己儿子中间,两人位变三人位,不影响其他学生,这是怎样的做人风格,心中无私而伟大,以己身为正而育人,转的值了!
渠老师是黄土洼的,四十来岁,教语文,幽默而有趣,讲到有趣处以书掩嘴自个先嘿嘿笑。我对作文的兴趣似乎也从此开始,期中作文比赛,我得了个一等奖,奖品是个圆规。我有生以来第一个奖状。
数学曹福有教过,曹金玉、宾爷也客串过。
福有老师是班里同学延锋他爹,个头小,多才懂音乐,后来初中再见,教我们音乐体育。
金玉老师是校长也是位老教师,也教过我的父母,浓眉大眼肥头大耳体形高大如山岳,一身福相,讲课很有特点,记我们盯住他鼻头看,那是他要我们集中精力听课。后来初中再见,他教我们历史。
那次宾爷讲课,黑板上写了题目正讲,我卖了野眼,只听得一声断喝:刘威你干什么!扭头一看他在讲台正怒目而视,吓得我以后再不敢听课跑毛。
我想这一期我是有进步了。春期回了村上小学,成绩应该可以不需要从后面数起。
每日早晚自习与相涛叔海洋叔一起。
我们拉土垫校园,学校后面垒个花池种了几棵松树,立了根旗杆,越发像回事了。
早自习我们来的早了没有开门,就给蜡烛粘在花池上看书,老师来了开了教室门,再给煤油灯点上读书,灯火如豆书声琅琅。煤油灯是墨水瓶上加个破车胎上的气门圈做的,中间以棉线为稔,火柴点灯。
调位了,老师叫男女坐一位,我给会贤姐一位。害羞不坐,抱住板凳回家不上了!挨母亲一顿收拾又搬回来接住上。
五年级时老师大调整,早庄马欣堂领班老师来到小学,父亲也不做村干部了,当了四年级的语文老师。五年级李建军教我们语文,黄狼山樊巧老师教数学,历史地理自然忘是谁教了,我的成绩似乎也可从前面去数。
石磊跟他妈来了我们学校上我们一班,他家小稻田的,他妈教二年级语文。
大生叔海霞姑胡龙威,还有西头双文伟卫东全州,都考上了初中。
放学后海生海洋又谲后河魏海亮,海亮气里没门,搁坑尾拈块砖头摞过来,坑头厕所里应声跑出个老头破口大骂,他正蹲坑,那一砖头给他棉帽子确了下来,头没事,但吓里不轻。
刚、妮蛋、涛这些弟妹们也都入学,荣姨姥娘家小三舅来到我家,在我村里上学。小三舅长里排场,上学不中。
鉴于外村老师过来,吃饭是个问题,学校又找随德爷打了口井,给西头郭归找来做饭。郭归会做饭,以前搁油坊做,见过他蒸里馍又白又大。他有郭要郭小菊俩孩子,后来他老婆领住孩子跑了。
那年西北山大规模军事演习,我们称之为打靶,山里整天炮声隆隆,飞机编队搁天上来回飞。
再之后来了南水北调勘探车,整天搁后河西地、胡庵南地立架打井钻探,二十多年后渠成,一渠绿水向北流。
几年后叔达买了小四轮,达叔开住犁地打场可有劲,牛用不上了。
秋天一个清晨,牛被卖给一个人,牵走了。陪伴几年的老牛,生了三个牛犊,每年犁耙几十亩地,终于还是带着它的小牛犊,一步一步的离开了我们。
通人性的青狗,有天早晨被发现死在了学亭家院里,它倦着身体卧在草堆上,像是平日睡着。大抵是父亲当村干部得罪了小人,几日后,房后灶屋的锅也给人拈走了。
奶家那条黑狗也老得走不动了。一天早上,被发现死在了烟炕里。
我童年不会说话的伙伴,陪伴那些快乐的日子,朝夕相处终于缘尽今生,各归各路……
我是瞅住仁义被撞飞出去的。
那天坐小拖去保安赶集,仁义骑自行车去取钱,到地方后我坐在边上等,瞅住许南路上车来车往。就听见嘭的一声,一辆从南往北的货车给个骑自行车的人撞得向前飞去,头撞到块大石头就一动不动了。
司机也马上下来,人们吃了一惊,小心的围上去看。
“是仁义么?”“瞅住像”是仁义!一起赶集的村人都赶紧往医院抬。司机是走不了了也跟本没走,村里人和他坐在那里。车是襄樊的,司机四十多岁,头顶半秃,安静坐着一句话也不说。
后来仁义被送到了平顶山医院。
命是保住了,俏皮依然,却少了之前的灵性,人们为之叹息。父亲与他大哥运平跑后面的事,最终人家赔了些钱,运平用这钱给仁义买了胡德成的房子,后来又给他娶了个蛮子媳妇,生了一串孩子。
仁义在平顶山住院时,姥爷带我和妮蛋去看过,那我们第一次去大城市。
他爹没了后,姥爷与他妈老何扔相互为伴,孤独这一生最后有伴,多么值得令人祝福,我能感受到两个老人的温暖与从容,人到老了谁又愿意去孤独。可惜苍天不与,几年后仁义他哥搁义、他妈先后因肝病去世。
二十多年后,仁义也是肝病去了!想想曾经一起的日子,心里为之难受。
至今看姥爷孤影对夕*,人之一生命运定数,何忍诉说!相信他记忆中,始终存在几年温暖时光,在孤独中回忆……
张姥娘的房子在一场雨中没有坚持住,塌了。父亲搁村西南头仓库边上给她找了一间住。
这是个一身乐观的八十多岁的小脚老婆婆,历经满清、民国与现代,母亲的姥姥。
娘家寨后冯家,寻西头张家,于是西头张家多是母亲舅姨,亲戚扯亲戚。生了四个女儿后张姥爷撒手西去,我姥也在母亲二岁时去了,张姥娘命运也是多亟待。
年轻时候织布,一只眼睛被纤子崩坏,她就用另只眼睛看这世界。
乐观,惜福,整天乐呵呵。有时到东头我家小住几天,做饭扫地,做些小活。
每天挑水过她家门前的人,都看看水缸少不少水,少了就添上。春种夏收,是姥爷、姨姥还有父亲,还有村西张家人帮她,她很是知足。有时表舅表姨会来看她,我也经常在她家玩,有时晌午放学不回去,搁那吃饭。
这样乐观开朗的老人,终于还是抵不过病魔,姨姥娘和母亲拉住她找医生看。
治不好的!食道癌令一个老人最后的时光,变得那么艰难,姨姥娘与母亲陪她走完这最后的日子。
一个秋天,张姥姥平静的去了,晴天落雨,我和银海燕也哭成泪人。埋在学校西边的路边,一座孤坟。
给她治过病的张庄*林,原村卫生所医生,也是癌症,竟然先她而去。癌,如此可怕!
几年后,银河燕她妈也因病去了,银国林又找了个范湾的女人,与孩子搁不住分了,从此海平海燕两个苦命的孩子相依为命。
年华如水,岁月悠悠。

前河*狗嗪老头常弯腰拉住酱油醋来庄上卖,李庵老娄隔些日子挑个担子来庄上剃头。
初夏的嫩蒜苔,初秋的小萝卜,都是我所喜欢。
广播放每天叫我们起床,放着中共中央******会见XXX的大事,还间播放插些歌曲,街上的录音带也多了起来。
村里房子都在渐渐更新,平房也有人建,主流还是瓦房,前头带个出前檐。
建堂叔领回了小改,大白天搁破屋里研究传宗接代的大事,有天给小改惹毛了,小改大吼:“离了恁家也照样挨球!”
学锋也领回了小春,结束打光棍的日子。
村里依旧平静,岁月悠悠,身边事物也在悄悄的改变。
农闲季节,万忠爷学吹喇叭,断断续续,呜呜啦啦。
东邻建堂叔家喂了头叫驴。这院喇叭一响,墙那边驴就嗯啊嗯啊地叫,才准头里。
驴应该是听到了知音。或者它以为,隔墙有一头母驴。
爷爷成天做木工活,刨子锛舞个不停劲,拉大锯解板儿。槐木结实,锯住费劲里很,四叔五叔搁那使劲拉锯。
一地锯沫刨花儿。
没事我们喜欢看爷做木工活,墨斗弹线,斧凿钻眼,菜桌衣柜就这样一件一件做出来。
刚系上了五叔的滚轴腰带,急往拉屎却解不开,越拽它越紧,期急里不行使菜刀割开了。五叔气里没门,找刚时刚装住睡着,于是只好找个布条当腰带。
远远看见涛蹲那拉屎,拉完后撅起屁股搁后面小树干上跐跐,算是擦了屁股。
爹达四叔学会了做水泥瓦,农闲之际,达带四叔四近跑住给人家盖房子的做瓦。
做到杨楼东邢岗,给娘领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