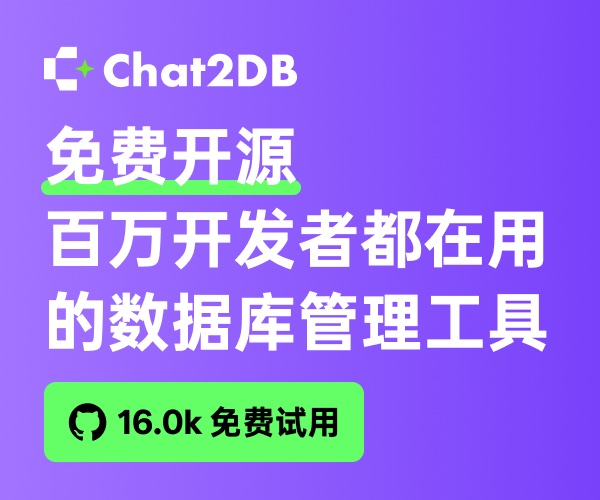七、冬去春来
七月在野,八月在户,九月萧霜,十月蟋蟀入我床。岁月悠悠,佳期如梦,我孤独回忆那段时光。

菊姑出门了。
婆家是东北六里马庄拴柱,东院彭妮奶奶娘家庄。我是娘家侄儿去带钥匙,就这样热热闹闹给菊姑送走。待到五月当午时分,挎住油馍篮儿回娘家。
大爷留的三个女儿一个儿子,香姑头脑正常,二姑就憨些,菊姑相对二姑,又少了些脑筋。待到儿子坡叔,直接成了哑吧傻子,整天歪带个破帽抄个手满村转,二姑做饭就给坡叔留一碗,吃过碗放在烟炕的烟囱上。终于有一天坡叔还是丢了,再傻再痴也是个儿子,大奶整天的思念,费尽工夫央人去找,多年过去终于是没有音讯。
香姑二姑的孩子人们,倒是一个比一个聪明。
拴柱也是实在人,头脑较常人也不够灵活,菊姑的孩子,后来也少听有消息,听说也是有点憨性儿。
大爷去世后,大奶又招了问爷,生了恩叔,脑子依旧不正常,但干活不惜力。父亲不喜欢干活,没少使他,几根烟几句好话就忽悠干里起劲。多年后,这个恩叔在保安街被车撞住,也去了。
有时在想上天对我家是怎么样的眷恋,同个老坟,爷奶就生养七个健壮而能干的孩子,及后孙子一代又满地跑,偏偏大爷这一支痴的痴傻的傻,二姑在十多年后病逝,大奶在恩叔去后一个人孤独的活着,而后终于一切都消失,利哥在他们老宅子上起了房屋,大爷一家从此就成了历史。
秋冬农闲也是盖房子的季节。
奶家的土墙草房很老了,叔姑们也渐大不够住了,于是又开始盖房子。村里盖房是件大事也是个热闹事儿,四里八乡亲朋友好友,邻居也都来帮忙。
爷爷们和土磕坯,起窑烧砖,挑水洇窑;套牛车去东沙河拉沙和水泥请人做瓦,核桃寨拉石灰,架网筛沙,砍树为檩削木为梁,打石头挖土扎根脚,泥瓦工搭架垒墙,帮工掂泥兜摞砖头,一个冬天,五间瓦房盖起了。前河金生姑父,奶里外甥女婿,人实在干活也是一把好手,从扎根脚到拆架子,从头干到了。
终于搬进了新房子,爷奶家住房条件得到了改善,达也有了自己的小西屋睡觉不用像书凯建华样再拱麦秸屋了。安徽来的做瓦蛮子八斤,却把德运爷家大妮书青姑给拐走了,日他八辈!
三年后我家盖房,请个叫船儿的安徽蛮子做瓦,爷恁他超人的心性与记忆偷画铁杠瓦模,凭木匠手艺设计瓦架,终于使这外地的做瓦技术留在了我们家,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为家里创收做出了贡献。
晚上喝过汤,爷奶家也是我们玩的地方,煤油灯下,灶火屋里,家人齐聚一屋,看我和刚表演叼机,我却叼不过他,涛表演开拖拉机,俩手转住呜拉呜拉进退嗷嗷叫。我们把皮帽子横扣头上,前后点头甩提帽子边上一摆一摆咵嗒响,学恶老雕飞。
家人们哈哈大笑!玩累了,各自回家睡觉。
大雁结队南飞,秋尽冬来。
我家的母猪开始拉窝,每天拖个大肚子把干草破布住它窝里拉,猪窝被它铺的厚厚的。没过多久,它就生了十几只猪仔,黑的白的花的乱哄哄,咕咕叫着抢住吃奶,那头母猪惬意的躺在那里,耳朵耷拉在眼上,喂它的孩子们。
勤劳的母亲啊!就这样养猪养牛,卖猪娃牛犊攒钱,为以后盖新房而努力。
奶家母狗生了一窝小狗娃,满月时我们逮一条小青狗去养,绒绒的可爱至极,我喜欢的很,整天放学就抱着玩。冬天冷晚上它喜欢卧在煤炉下面,一天早上母亲起来捅开煤封生炉子时,一块火炭掉在它背上烫伤它一块皮,它疼的哇哇叫,母亲舀一瓢水沷在它身上,很久以后这片毛才又慢慢长齐。
那头母牛听说在上一家不会生的,买回来后不久它就有了做牛妈的倾向,父亲就牵它找公牛配种,几个月后,它就生了头漂亮的小牛犊儿,想是上天感动于母亲的吃苦耐劳而特别照顾吧!
冬夜的天空暗蓝而幽远。
弯月如钩寒星闪烁,没有叶子的桐树枝指向夜空,不时有夜鸟飞过的声音。柴鸡在黄昏时分就开始从矮墙飞上树杈,它们还保留着祖先宿树的行为,待天五更公鸡便开始打鸣,叫人开始起床。
农在煤油灯下剥苞谷择花生,秋收积下来的棒子在冬夜慢慢剥粒,一个一个的苞谷棒儿,在大人的故事中变也了苞谷芯儿,待夜深而困上床睡觉。
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来的特别早。
皂角树叶子尚自青翠,下午鹅毛大的雪花就漫天飞了下来,我听到叶子离开大树飘落地面的声音,落在雪层上面,风犹吹动。第二天打开门窗,我看到了一个银妆素裹的世界。檐飞冰棱,踏雪寻梅,宛如童话。坑里上冻了,小鱼被冰封在岸边,我们敲开冰块就能给小鱼取出来。
冬去春来斗转星移,燕子从南方飞来,猪娃长成小猪仔,待逢集市就拉到保安街卖了,小狗娃也长成了半大青狗。
青狗极通人性勇敢又可爱,隔三差五还会去姥爷家张姥娘家串串门儿,待到上街赶集它也跟住我们往西北走。母亲说:青狗啊,回去吧,到人家那地儿,人家打啊!青狗摇摇尾巴止住脚步,瞅着我们走远。待到赶集回来,早见它等在路口,摇尾撒欢跑上来前后跳跃。父亲打兔子就带住它,枪一响兔子一跑它窜出去就撵,往往能给惊跑的兔子撵回来,谁要也不给。到父亲面前就丢下,摇摇尾巴。
再后来,它字会了跟它老子,奶家那条老黑狗咬架。
我家也打了压井,终于不用去井边挑水,四叔没少出力。两丈多打过石层就有水了,井水清甜,煮红警苞谷糁好喝里很!
崔姥娘日渐衰老后来还是去世了。
姥爷的家门便整天锁着,他是个喜欢到处悠的人,而经常在当街屋角与绍房、小松、大明、长明那一群老人,打长条牌儿赌博以过时光。
野油菜开满麦田,组成黄白相间的花布,我们就去薅啊薅以做牛草,我手总是很慢,别人薅满箩头时,我才收获一点点。大瘦小了,要样没样要力没力,干活不沾球弦!
干达时尔骑个二八大杠从郏县来。
他是个跑住卖兔子药的,就是土枪所用的火药,与喜欢打兔子的父亲对劲儿,而非认为当干儿。他车前杠搭个帆布包,有时带点饼干有时是糖,在这卖几天兔子药,然后再蹬回郏县。
终于有一天母亲再也受不了父新的醉酒打骂,跑了。父亲也只好给我们做饭,他哪里会做啊!蒸里馍瓷里石头蛋样吃不成。那几天真是体会到没娘孩的痛苦,天天想念母亲,想一想孤儿更是难过。
几天后在黄狼山姨姥娘家找到了母亲。
父亲从此似乎是收敛了一点,日子就那样慢慢过,他仍是喜欢外面到处跑不着家。
学四家猪给药死了,爹去买了刀血脖肉,晚上做了肉面条吃。吃过不久就难受干哕,中毒了,刚涛难受的哇哇大哭,涛那含泪的大眼瞅住心疼人!赶紧上前河给铁功找来,又打针又是输水,忙活半夜终于给毒消了。从此爹与张四家有了交情,闲忙两家经常走动。
群中爷娶棉奶奶,乱花媳妇乱里实受,延岭延坡更是上样,棉奶奶使高跟鞋摔他们一头疙瘩。
四月八范湾起会,孤山脚下热闹非常。卖冰糕的糖果瓜子的甘蔗的都来了,还有卖糊辣汤炸油镆摊儿。
其村多戏子,有时村前河边相隔百米搭俩戏台唱对台戏,锣鼓笙弦梆,生旦净末丑,你罢我上场,精彩纷叠出,大抵是些《小苍娃》《李豁子》《火焚绣楼》之类。四近村庄上的人都来看戏,时常碰上亲戚。老人看的如痴如醉,上班一样照时照晌看,有时还有夜戏;我们只是喜欢那热闹异常,可以买糖吃,还能看热闹。
谁家娶媳妇了谁家又生孩子了,就请牛庵爱军放场电影,热闹事啊!
幕布是扯在主家附近空场处两棵大树中间。
喝罢汤,磨电机的声音就响了,我们搬着小椅子就去把位了,小孩子总是性急,给手晃着看那银幕上乱的手的影子。老人家喜欢戏片,我们喜欢打仗片,于是通常上片为戏,下为战争片,只盼着戏片早点放完。我更喜欢武侠片,想来都有些《黄河大侠》《南北少林》《鹰爪铁布衫》《破袭战》《湘西剿匪记》之类。
待四近村庄有电影,庄上亲戚有时捎信儿告知,于是喝汤后我们就跑去看,牛庵张庄前河后河,甚至更远一点,几里地的跑,往往跑到村边就听到电影早已开始,看完再跑回来,都二半夜了。
小火车依旧在每天正午时分来回保安街。站在村头西北望,能看到七八里外它冒着黑烟的车头和长长的车身,依稀能听那悠长的汽笛声。
葫芦藤爬上篱笆篱笆,槐花开满村头时候,大姑带住姑父付生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