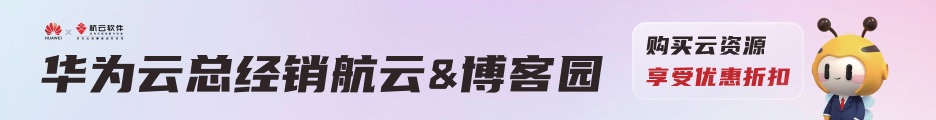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
身不下堂,而单父治。
——《吕氏春秋》
对于读武侠的人来说,世界上的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喜欢武侠的,一类是不喜欢武侠的。前者如北师大的几个年轻学者,视金庸为文学大师,并定下座次,将其在百年中国中排位第四,后者如王朔,把之与琼瑶等并列,讥之为“四大俗”。看来文坛的纷纷扰扰丝毫不亚于武林,只不过任如何笔战,总是“双赢”,大家皆名利双收,而不像以武相斗,不免两败俱伤。对此,我想在这篇文章中比较聪明的作法应该是暂不表态,这样不致因“路线问题”,一开始就让一部分读者产生抵触情绪。
好在“思想和文字都只是工具,其本身并不具有贬褒的意味”,看讨论一个问题是否恰当,“要害在于这个问题是否具有法理学的意义,是否可以让我们对社会和法律更多一些理解”。八十年代以来,武侠小说在大陆的风靡和其在九十年代引起的势若水火、冰炭不容的争论,决定了它是学术界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现象所无法绕过去的一个问题,至于它是否具有法理学意义,这正是本文下面所要阐发的。
一、 千古文人侠客梦——研究进路及其意义
一个最基本而又最易被人们忽视的问题是,所谓“武侠小说”,其实是“文人小说”。在写武侠的人中,以近现代而论,只有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和郑证因算得上精于技击,其他大多是真正地“纸上谈兵”。梁羽生倒是练过太极拳,但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很多北大女生也练太极拳。而这些人是不折不扣的文人却是事实。出身书香世家、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后来又写电影又办报的金庸自不必说,梁羽生古文功底深厚,典章诗词俱佳,甚至连思想也沾染着一点传统文人气。而古龙,看其在《多情剑客无情剑》的开篇:冷风如刀,以大地为砧板,视众生为鱼肉。万里飞雪,将苍穹作洪炉,溶万物为白银。雪将住,风未定,一辆马车自北而来,滚动的车轮辗碎了地上的冰雪,却辗不碎天地间的寂寞。李寻欢打了个呵欠……
非文人,而且还是有点才情的文人,不能有此笔墨。
各行各业大多有自己供奉的祖师爷,其实武侠小说这一宗供奉的还是太史公司马迁。追根溯源,《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是中国武侠文学的源头,荆轲、豫让、聂政、郭解、朱家等一批中国最早的豪侠之士藉太史公之笔得以流名后世,其事迹多动人心魄,荡气回肠,颇具传奇色彩。以此为滥觞,之后武侠文学曾经历了隋唐武侠传奇、明清侠义公案小说和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现代旧派武侠小说等发展阶段。一批文人创作了一大批描写侠士事迹的作品,隋唐传奇如《虬髯客传》、《聂隐娘传》,侠义公案如《水浒传》、《三侠五义》,旧派武侠如《江湖奇侠传》、《十二金钱镖》等皆是中国文学史不可或缺的部分。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随着梁羽生《龙虎斗京华》的问世,在港台迅速掀起了一阵武侠小说热潮,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萧逸等人不断突破旧派武侠小说的局限,吸收了西方文学的表现手法和叙事结构,并体现以现代人的情感,创造出一个虚幻的武侠世界,江湖恩怨,刀光剑影,更兼爱恨情仇,迅速风靡华人世界,至今未衰,被称为新武侠小说或新派武侠小说,这也就是当今一般所理解的,也即本文所要讨论的所谓“武侠小说”。
由于武侠小说在读者中的风靡,造成巨大的市场效应,诱使不少人弃文从“武”,如过江之鲫,纷纷投奔“武林”,其中当然也就包括不少好利而才力不逮者,因此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文化的商业化使得有着巨大商业价值的武侠小说更易受到商业化侵害而确有既“泛”且“滥”之势。但正如我们不能因村妇村夫们诌几首打油诗就否定所有诗词,也不能因某些领导人喜欢题字而认为这就是中国书法一样,对此不应以偏概全。大浪淘沙,真正能被读者所接受并流传下来的,新派武侠中确不过廖廖十数人而已。但正是这部分人的武侠小说成为经久不衰的力作,风行于华人文化圈。它们代表着真正的武侠小说,因而也具有分析的样本意义。
“戏剧,只有当产生观众以后才可以说真正诞生”,戏剧之外的其他文化形式同样如此。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是统一的,文化产品是作者和读者共同的创造物。作者创作出作品,读者则通过阅读与传播使它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读者对于作品,是以自己“生活的和文学的期待视野出发去看待的”,所以作品的被接受程度反映了它对读者期待心理的满足程度,因此,作品也就具有了对社会心理的表征意义。作品的流传时间愈长,影响人群愈广,对社会文化的反映也就越深刻,透视出的社会心理也就越普遍。——我在这里说的是反映心理的“普遍性”,而非对作品价值高低的判断,作品的价值是多维的。
作品的流行是时代的集体无意识的反映,我们通过剖析作品就可以解读社会心理。
明乎此,则讨论武侠小说的意义也就不言自明。我无意参与武侠文学的雅俗高低之争(当然现在可能就已经介入了),而且我仍然认为武侠小说起码在当代确实是俗文学,但有两点,我们不能不注意,而这两点正关系到下面我们对其意义的开掘:
首先,从创作者来看,它是文人小说,则非民间文学。武侠小说不同于瓦舍勾栏间的评书演义,不是民间流传的口头文学,而是自始即由文人有意识创作的,但它一经创作出来,即广泛流传于市井之间,因此,它是文人传统与市俗社会的共生物,在反映社会心理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普遍意义。
其次,从接受者来看,它是大众文化,而非“亚文化”。前人言有井水处,即有柳永词,今人称有华人处,即有金庸小说,这并非夸张之词。如果还认为武侠小说仅是不求上进的中学生从书摊上租来在课桌下偷看的破烂读物,那就有些罔顾事实了。不可否认,很多创作武侠小说的作者在一些人眼里,即使是文人,也是末流的、甚至不入流的文人,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那些很“入流”的文人却也很喜欢读武侠,这可以开出长长一串名单。[5]接受作品是对作品所表达的东西的一种认可(起码是部分认可),更遑论喜欢该作品了。当讲堂上的大学教授和逃课的中学生同样热衷于虚幻的侠义世界时,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意识到武侠小说可能是这些读者群中一种深层心理无意识地体现。由于这个读者群的庞大,从少年到成人,从学者到市井,并有代代延续的趋势,因此它也许是解读“中国人的精神”的一个极佳样本。
但武侠小说源远流长,名家众多,风格迥异,思想不一,比如梁羽生的正统、古龙的奇变和金庸的博大,如果仅以“武侠”二字统之,可能会犯大而化之的错误。正如外星人来到地球,在他们眼里,也许就以地球人文明而概之,而不分什么东方文明、西方文明,更不要说还有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了。但再反过来一想,以“地球人文明”统之也对,因为在非人类看来,地球人文明的共性可能正是他们要考察的,而对我们地球人来说,由于身在庐山,反只顾计较此峰与彼峰的不同,却不知峰峦叠翠的庐山到底为何物了。所以,以“武侠”这一看似大而化之的进路去把握武侠小说的精神,我想是合适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不愿作进一步具体分析的遁词,但在事实上,如果要求每一部武侠小说都印证我的分析是不可能的,比如,我说武侠小说的主人公往往武功高强,读者就很容易举出《鹿鼎记》中几乎不会武功的韦小宝,我说江湖世界往往无国无法,而起码梁羽生的很多小说里国家的背景是很突出的。我只能选择符合大部分武侠小说特点、更能反映武侠特质的例子为分析样本,而不可能面面俱到——《鹿鼎记》被称为“反武侠小说”,而梁羽生则往往被人批评写得太实,所以即便是金、梁作品,也不是所有东西都应该拿来作为分析武侠小说整体精神的范例。当然,我也不会全然放弃具体的分析。
未完待续
该是看待武侠小说,但是我摘录下来,是想把他的观点引述到看待佛学上,这一切都是社会心理的表现..
身不下堂,而单父治。
——《吕氏春秋》
对于读武侠的人来说,世界上的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喜欢武侠的,一类是不喜欢武侠的。前者如北师大的几个年轻学者,视金庸为文学大师,并定下座次,将其在百年中国中排位第四,后者如王朔,把之与琼瑶等并列,讥之为“四大俗”。看来文坛的纷纷扰扰丝毫不亚于武林,只不过任如何笔战,总是“双赢”,大家皆名利双收,而不像以武相斗,不免两败俱伤。对此,我想在这篇文章中比较聪明的作法应该是暂不表态,这样不致因“路线问题”,一开始就让一部分读者产生抵触情绪。
好在“思想和文字都只是工具,其本身并不具有贬褒的意味”,看讨论一个问题是否恰当,“要害在于这个问题是否具有法理学的意义,是否可以让我们对社会和法律更多一些理解”。八十年代以来,武侠小说在大陆的风靡和其在九十年代引起的势若水火、冰炭不容的争论,决定了它是学术界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现象所无法绕过去的一个问题,至于它是否具有法理学意义,这正是本文下面所要阐发的。
一、 千古文人侠客梦——研究进路及其意义
一个最基本而又最易被人们忽视的问题是,所谓“武侠小说”,其实是“文人小说”。在写武侠的人中,以近现代而论,只有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和郑证因算得上精于技击,其他大多是真正地“纸上谈兵”。梁羽生倒是练过太极拳,但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很多北大女生也练太极拳。而这些人是不折不扣的文人却是事实。出身书香世家、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后来又写电影又办报的金庸自不必说,梁羽生古文功底深厚,典章诗词俱佳,甚至连思想也沾染着一点传统文人气。而古龙,看其在《多情剑客无情剑》的开篇:冷风如刀,以大地为砧板,视众生为鱼肉。万里飞雪,将苍穹作洪炉,溶万物为白银。雪将住,风未定,一辆马车自北而来,滚动的车轮辗碎了地上的冰雪,却辗不碎天地间的寂寞。李寻欢打了个呵欠……
非文人,而且还是有点才情的文人,不能有此笔墨。
各行各业大多有自己供奉的祖师爷,其实武侠小说这一宗供奉的还是太史公司马迁。追根溯源,《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是中国武侠文学的源头,荆轲、豫让、聂政、郭解、朱家等一批中国最早的豪侠之士藉太史公之笔得以流名后世,其事迹多动人心魄,荡气回肠,颇具传奇色彩。以此为滥觞,之后武侠文学曾经历了隋唐武侠传奇、明清侠义公案小说和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现代旧派武侠小说等发展阶段。一批文人创作了一大批描写侠士事迹的作品,隋唐传奇如《虬髯客传》、《聂隐娘传》,侠义公案如《水浒传》、《三侠五义》,旧派武侠如《江湖奇侠传》、《十二金钱镖》等皆是中国文学史不可或缺的部分。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随着梁羽生《龙虎斗京华》的问世,在港台迅速掀起了一阵武侠小说热潮,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萧逸等人不断突破旧派武侠小说的局限,吸收了西方文学的表现手法和叙事结构,并体现以现代人的情感,创造出一个虚幻的武侠世界,江湖恩怨,刀光剑影,更兼爱恨情仇,迅速风靡华人世界,至今未衰,被称为新武侠小说或新派武侠小说,这也就是当今一般所理解的,也即本文所要讨论的所谓“武侠小说”。
由于武侠小说在读者中的风靡,造成巨大的市场效应,诱使不少人弃文从“武”,如过江之鲫,纷纷投奔“武林”,其中当然也就包括不少好利而才力不逮者,因此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文化的商业化使得有着巨大商业价值的武侠小说更易受到商业化侵害而确有既“泛”且“滥”之势。但正如我们不能因村妇村夫们诌几首打油诗就否定所有诗词,也不能因某些领导人喜欢题字而认为这就是中国书法一样,对此不应以偏概全。大浪淘沙,真正能被读者所接受并流传下来的,新派武侠中确不过廖廖十数人而已。但正是这部分人的武侠小说成为经久不衰的力作,风行于华人文化圈。它们代表着真正的武侠小说,因而也具有分析的样本意义。
“戏剧,只有当产生观众以后才可以说真正诞生”,戏剧之外的其他文化形式同样如此。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是统一的,文化产品是作者和读者共同的创造物。作者创作出作品,读者则通过阅读与传播使它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读者对于作品,是以自己“生活的和文学的期待视野出发去看待的”,所以作品的被接受程度反映了它对读者期待心理的满足程度,因此,作品也就具有了对社会心理的表征意义。作品的流传时间愈长,影响人群愈广,对社会文化的反映也就越深刻,透视出的社会心理也就越普遍。——我在这里说的是反映心理的“普遍性”,而非对作品价值高低的判断,作品的价值是多维的。
作品的流行是时代的集体无意识的反映,我们通过剖析作品就可以解读社会心理。
明乎此,则讨论武侠小说的意义也就不言自明。我无意参与武侠文学的雅俗高低之争(当然现在可能就已经介入了),而且我仍然认为武侠小说起码在当代确实是俗文学,但有两点,我们不能不注意,而这两点正关系到下面我们对其意义的开掘:
首先,从创作者来看,它是文人小说,则非民间文学。武侠小说不同于瓦舍勾栏间的评书演义,不是民间流传的口头文学,而是自始即由文人有意识创作的,但它一经创作出来,即广泛流传于市井之间,因此,它是文人传统与市俗社会的共生物,在反映社会心理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普遍意义。
其次,从接受者来看,它是大众文化,而非“亚文化”。前人言有井水处,即有柳永词,今人称有华人处,即有金庸小说,这并非夸张之词。如果还认为武侠小说仅是不求上进的中学生从书摊上租来在课桌下偷看的破烂读物,那就有些罔顾事实了。不可否认,很多创作武侠小说的作者在一些人眼里,即使是文人,也是末流的、甚至不入流的文人,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那些很“入流”的文人却也很喜欢读武侠,这可以开出长长一串名单。[5]接受作品是对作品所表达的东西的一种认可(起码是部分认可),更遑论喜欢该作品了。当讲堂上的大学教授和逃课的中学生同样热衷于虚幻的侠义世界时,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意识到武侠小说可能是这些读者群中一种深层心理无意识地体现。由于这个读者群的庞大,从少年到成人,从学者到市井,并有代代延续的趋势,因此它也许是解读“中国人的精神”的一个极佳样本。
但武侠小说源远流长,名家众多,风格迥异,思想不一,比如梁羽生的正统、古龙的奇变和金庸的博大,如果仅以“武侠”二字统之,可能会犯大而化之的错误。正如外星人来到地球,在他们眼里,也许就以地球人文明而概之,而不分什么东方文明、西方文明,更不要说还有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了。但再反过来一想,以“地球人文明”统之也对,因为在非人类看来,地球人文明的共性可能正是他们要考察的,而对我们地球人来说,由于身在庐山,反只顾计较此峰与彼峰的不同,却不知峰峦叠翠的庐山到底为何物了。所以,以“武侠”这一看似大而化之的进路去把握武侠小说的精神,我想是合适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不愿作进一步具体分析的遁词,但在事实上,如果要求每一部武侠小说都印证我的分析是不可能的,比如,我说武侠小说的主人公往往武功高强,读者就很容易举出《鹿鼎记》中几乎不会武功的韦小宝,我说江湖世界往往无国无法,而起码梁羽生的很多小说里国家的背景是很突出的。我只能选择符合大部分武侠小说特点、更能反映武侠特质的例子为分析样本,而不可能面面俱到——《鹿鼎记》被称为“反武侠小说”,而梁羽生则往往被人批评写得太实,所以即便是金、梁作品,也不是所有东西都应该拿来作为分析武侠小说整体精神的范例。当然,我也不会全然放弃具体的分析。
该是看待武侠小说,但是我摘录下来,是想把他的观点引述到看待佛学上,这一切都是社会心理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