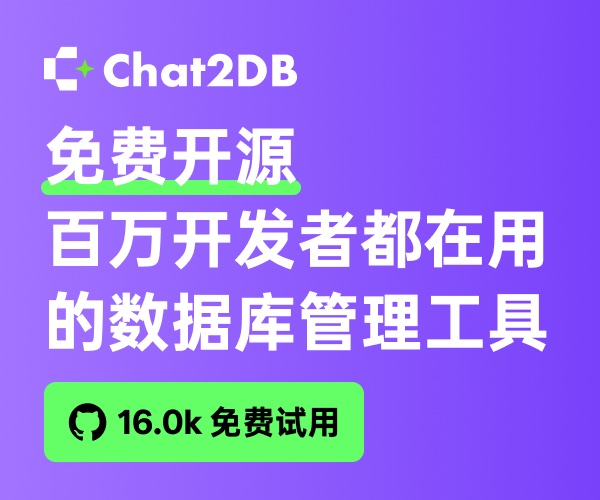不老梦
——终南山里不老坟,不老坟中不老梦。
终南有坟,名不老。客奇之,问何故,言乃淮南翁主媗冢。
元光二年上巳,媗于渭水之滨遇振翊将军韩衿,悦之。明年,河水决濮阳,上发卒十万救决河,使衿督。媗送别,诉心意。衿以其年尚幼,婉拒之。
后三年,衿戍定襄,媗托尺素,书:妾已及笄。
复三年,媗随姊陵探长安,约结上左右。每逢衿,且喜且怯。
又三年,媗疾,久不愈。衿随大将军青击匈奴,媗恐不复见,追大军十余里,终力竭。呛血白衣,形销骨立。
元狩元年,淮南衡山事发,陵媗皆下狱。衿欲面之,叩未央宫,额血流地,上弗允。媗殒,衿亲葬于终南。后长安有歌曰:茔茔蔓草,岁岁不老;风雨如晦,死生为谁。
终南有坟,名不老。
Chapter.1 初遇
——于万人中万幸得以相逢 刹那间澈净明通
元光二年,上巳。
虽然才是冰雪刚刚消融的初春,可是这日午时,阳光却格外的好,透过刚从树枝上钻出来的嫩芽,暖洋洋地洒在地上,投射下交叠的树杈的光影。
突然,有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步伐轻盈,听起来像个边走边跳的孩童。
一个看起来十一二岁的小女孩手中拿着一根狗尾巴草,蹦蹦跳跳地沿着河边走来。明眸皓齿,眼中波光流转,看起来十分机灵乖巧讨人喜欢,一看便知是个美人胚子。着一身水蓝色的短袄,头上简简单单绾了个发髻,垂下的发梢和她手中那狗尾巴草倒是很有默契一般,随着她跑跳的动作一起一伏。
小姑娘走着走着,忽然停下了脚步,眼睛直愣愣的望着前方。
只见一男子正蹲在河边,用手鞠了一捧水,轻轻地将水扑在脸上,然后闭上眼睛用力地甩了甩头,将脸上的水珠甩掉。睁开眼,却感觉到旁边似多了个人,便转过头站起身来,望向来人。
那男子身形伟岸,剑眉星目,英气逼人。却因刚洗了脸,长长的睫毛上沾了几滴没甩掉的水珠,给人的压迫感轻了许多,反而更平易近人了些。
小女孩从未见过生得如此好看的人,一时间竟是看呆了。
“你是何人?”男子声音低沉浑厚,吓得正发呆的小女孩打了个激灵。一松手,狗尾巴草掉落在地。
小女孩回过神来,脸颊上染上一抹绯红,不自在地大声回问道:“问别人是谁之前,难道不应该自报家门么?”
男子拱了拱手,“在下振翊将军韩衿。”
小女孩见他如此正经,竟未与她斗嘴,有些别扭地低头摆弄手指,小声道:“我,我叫刘媗。”
韩衿思索了一阵,问道:“刘媗?可是淮南王刘安家的千金?”
刘媗惊奇地抬头,“你怎么知道?”
“在下与令尊也算是老相识。”他说着,在草地上坐了下来
刘媗小跑了两步,也在他身边坐了下来,“我怎么从来没听我爹提过你啊?”
韩衿也拽了一根狗尾巴草,叼在口中,含糊道:“唔,不太熟,没提过也正常。”
刘媗“哦”了一声,便双手抱膝,将头放在膝盖上,直勾勾地看着他。
韩衿本来泰然自若地目视前方,被两道毫不收敛的目光注视了半天,也是有些吃不消。不自在地转头,“咳,小翁主,你一直看着我做什么?”
刘媗被抓了个正着,扭过头用后脑勺对着他,撅起嘴,“哼,长得这么好看还不让人看!未免也太小气了吧!”
韩衿无奈地笑道:“没有不让看,在下只是休整时间来河边歇息片刻,也该回军队了。小翁主也不要太贪玩,早些回家吧。”说着,站起身来欲走。
“那,那你明天还会来么?”刘媗也赶忙站起来,拍了拍身后的草叶,有些局促。
韩衿转过身低头看着她充满期待的眼神,“不知。”看着她瞬间垮下去的小脸儿,又有些不忍心。轻轻拍了拍她的头,道:“应该会的。”
刘媗水灵灵的大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嘴角止不住的上扬,喜滋滋地道:“好的,那我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来找你!”
Chapter.2 别离
——天意总将人捉弄 怎奈何身不由己情衷
元光三年,黄河于濮阳决口,经巨野泽东南流入淮泗,泛滥十六郡。
一年来,刘媗与韩衿几乎日日午后都会在渭水边相会。大多数时候是刘媗扯着韩衿,给他讲她每日发生的事和见到的新鲜事物。韩衿坐在她身边静静听着,偶尔讲一讲他在军中的见闻。虽然每日只有一刻钟左右的时间,那却是刘媗每天最开心的时光。
韩衿一开始尊称她翁主,刘媗嫌这称呼太过正式,他拗不过,便唤她媗儿。
她也从不称他为将军,每天“韩衿,韩衿”地直呼其名。
一日午后,两人照常坐在河边。刘媗正眉飞色舞地讲着她在茶楼里听的戏,偏头却看到韩衿蹙着眉头,似乎满腹心事的样子,她便停了下来,问道:“韩衿,你有心事吗?”
韩衿迟疑了下,还是开口道;“黄河决堤,皇上派了十万兵士去濮阳救灾,命我督查。”
刘媗愣了愣,“啊,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或许一两年,或许很多年,或许之后还会有别的任务……便不会回来了。”
刘媗听到最后一句时,身子轻轻颤了下,不可置信地望向他,张了张嘴,却什么都说不出口。
韩衿垂眸,目光中充满歉意:“抱歉,以后可能很久都不能来这儿陪你了。”
刘媗揉了揉已经开始微微泛红的眼睛,吸了吸鼻子,“那,那你什么时候走?”
他沉默了一会儿,“明日清晨。”
“这么急……”刘媗低下了头,声音中已带上了明显的鼻音,“……我可以去送你么?”
韩衿心里也很是不舍,抬手摸了摸她的头,“自然可以。”
第二日清晨,十万兵士已在城外集合,整装待发。韩衿立在最前面,却迟迟没有要出发的意思。
一名士兵上前问道:“将军,请问我们何时出发?”
“……再等等。”
这时,突然听到一道少女特有的软软的嗓音从大军后方传来:“韩衿,韩衿!”
韩衿回过头,看着刘媗跌跌撞撞地一路小跑过来。跑到他跟前时,竟没刹住,一头撞进他怀中。
韩衿将她从怀中轻轻扯出,蹲下身,帮她擦了擦额上的汗珠,责备道,“怎的跑这么急?摔倒了怎么办?”
刘媗还在喘着气,断断续续道:“昨晚……昨晚没睡好,起晚了,我怕,怕来晚了你就走了……”
韩衿无奈,正要起身,又被她两只小手按住了肩膀,便疑惑地看向她。
“韩衿……韩衿我有话对你说……”
刘媗的小脸上挂着一抹不自然的红,不知是因为跑得太急还是别的什么。
“?”韩衿不解。
刘媗却好像愈发的不自在,东看西看,就是不看韩衿的脸。
“媗儿?”
刘媗低下头,似是打定主意了不去看他。
韩衿蹙了蹙眉,“媗儿,有事情快点讲,将士们还在等。”
她像是做了什么重大的决定,猛然抬起头,深吸一口气,发出的声音却是蚊子般大小。
“韩衿,我……我心悦你。”
她声音虽小,可是二人离得极近,韩衿却是听得真切。
沉默了一会儿,韩衿站起身,摸了摸她的头。
“媗儿……你还太小了。”
刘媗抬起头,似是不服气,“我不小了!我今年十二了,还有三年就及笄了!”
韩衿面上露出一种极其复杂的神色,良久,还是叹了一口气。
“媗儿,我一直把你当妹妹看。”
刘媗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
“若你没有其他想说的,那我便上路了,将士们有些不耐烦了。”他说着,跨上了马背。
刘媗仰头看着马背上的他对自己微微一笑,说了句:“再会。”便带领十万大军绝尘而去。
再会……再会?
有生之年……还能再会吗?
刘媗蹲在地上,以手掩面,泣不成声。
年岁不可更,怅惘知多少?
Chapter.3 信笺
——爱若执炬迎风 炽烈而哀恸
元光六年,濮阳灾情渐缓,武帝命韩衿带领五万兵士戍守定襄。
一日傍晚,韩衿躺在床上,刚刚阖上眼。
突然,一名将士在帐外唤道:“将军,歇下了吗?有您的信!”
他只得睁开眼,坐起身来穿上靴子,“进来吧。”
将士将信送到他手中,便退下了。
韩衿拿着信坐到桌前,疑惑地看着信封上的几个蝇头小篆,“韩衿 亲启”。
字体隽秀雅致,而他并不熟悉。
拆开信封,里面的信纸上只写了四个字。
“妾已及笄”。
……刘媗?
这么快,小娃娃都十五了啊。
韩衿脑中浮现出刘媗手中拿着狗尾巴草在他身边蹦蹦跳跳古灵精怪的模样。
真不知道这小娃娃长大了是什么样子,会不会比小时候安静一些。
韩衿盯着这四个字发了一会儿呆,便把信装回去收好,又重新躺回了床上。
当天晚上,刘媗便入了他的梦。梦里,她还穿着那件第一次见到他时穿的那件水蓝色的袄子,却已然长成了少女模样。
Chapter.4 重逢
——倏忽天地琉璃灯 光阴过处徒留皎月几盅
元朔三年。
刘媗与刘陵二人走在热闹的集市上,刘媗初到长安,新奇的很。一会儿在这边的摊子上看看簪子,一会儿又跑到那边去看看胭脂水粉。
刘陵无奈,抓着她的手带着她向前走,“媗儿,咱们来长安是要办正事的,不是来游玩的啊。”
刘媗撅起了小嘴,“哼,长安也没什么好玩的嘛,簪子的做工还没有咱家那边的好呢!”
刘陵睨了她一眼,“哦?那是谁听说自己的心上人在长安,便死皮赖脸地拽着我,一定要跟着我一起来办事情的?”
她登时羞红了脸,将刘陵的手甩开,跺了跺脚,“姐姐,你总这样取笑我!”
刘陵看着自家妹妹的窘态,掩着嘴笑得开怀。
刘媗本来气鼓鼓地瞪着她,突然把目光移向她身后,微微张开了嘴,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
刘陵莫名的回头,顺着妹妹的目光,看向了一个器宇轩昂的男子的背影。
刘媗却已经追了上去,拍了拍那男子的肩膀。
男子回过头,一张熟悉的脸就这样出现在刘媗面前。
韩衿原本只觉得这姑娘很是面熟,一时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直到面前的女子脸颊绯红,眼中波光粼粼,泪水似是要夺眶而出,他才想起来,六年前,也有个小姑娘这样在他面前哭过。
“……媗儿?”
刘媗一下子扑到韩衿怀中,哭得梨花带雨。
韩衿没有防备,被她扑得向后退了两步,有些手足无措,“媗儿……?怎么了?哭什么?”
“韩衿……韩衿我好想你……”怀中的人儿将脸埋在他怀中,声音闷闷的,断断续续地道。
韩衿哭笑不得,轻轻摸了摸她的头。
目睹了眼前这一幕的刘陵有些不自在的咳了咳,“咳……媗儿啊,街上的人都看着你们呢,先从人家怀里出来再说话,别让韩将军太难堪啊。”
刘媗才反应过来,急急忙忙的从他怀中退了出来,眼睛有些红肿,从袖中拿出手帕擦了擦眼泪。
韩衿看着刘陵和刘媗有几分相似的面孔,了然道:“这位姑娘可是刘陵翁主?”
刘陵颔了颔首,“正是。久闻韩将军大名,今日一见,果真气度不凡。”
韩衿朝她礼貌地笑了笑,看向刘媗,“媗儿,你们姐妹来长安做什么?”
刘媗摸了摸鼻子,总不能说因为知道你在长安所以才来的吧……
“啊……我爹让我们来长安……咳,办点事情。”
刘媗说到一半,看着姐姐拼命地对自己使眼色,突然意识到自己差点说错了什么,连忙打住话头不再讲下去。
韩衿也不追问,点了点头,“恩,我也有事情要办,那就先走一步了,下次有机会再聊。”然后向刘陵拱了拱手。“告辞。”
刘媗正想叫住他,余光看到姐姐责备的眼神,僵了一僵,便作罢。
刘陵叹了一口气,“媗儿,有些事情,即便他是你的心上人,你也不能肆无忌惮地讲给他。”顿了顿,又道:“更何况……他还是个将军。”
刘媗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低头心虚地绞着手帕,“知道了,姐姐。”
她嘴上道着歉,心里却在期待着,不知下一次什么时候还能再遇到韩衿?
Chapter.5 追逐
——天光落笔波折 岁月都干涸 只剩别离来不及说
元朔六年。
刘媗不知患了什么病,一年以来,看了许多郎中,开了许多药方子,每日把药当水喝,却迟迟不见好转,身体每况愈下。
她只能待在屋中,连下床走的久一些都会力不从心,只得日日躺在床上。是以,愈发的沉默寡言。
这几年来,偶尔和姐姐在外拜访达官贵人时能遇见韩衿。每每遇见,都能让她高兴好几天。可是自从患了这病,她便再没出过这院门,终日郁郁寡欢,人也清瘦了许多。
一日,病魔再次袭来,她支持不住,昏睡过去。
梦中全都是韩衿。
在她耳后别了一朵花的韩衿,听她唱歌的韩衿,下水帮她捉鱼的韩衿,给她演示自幼习得的剑法的韩衿,离别时婉拒她的韩衿,久别重逢后的韩衿……
满满都是韩衿。
刘媗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额头上满是细细密密的汗珠。
刘陵正愁眉不展地坐在她床边,见她醒来,眉头立马舒展开来,“醒了?可有哪儿不舒服?”
刘媗摇了摇头,坐起身来。
刘陵倒了一杯水给她,边拿着手帕帮她擦额上的汗,边念叨着:“你昏睡了整整两天,一直在叫你那心上人的名字,把我给急坏了……”说着,愣了愣,“对了媗儿,韩将军昨日领命随卫青将军出击匈奴了……应是今日出发。”
刘媗拿着杯子的水抖了抖,被水呛得止不住的咳嗽,刘陵忙接过水杯帮她拍背。
咳嗽好不容易止住了,刘媗却已红了眼眶,颤声问道:“姐姐……现在几时了?”
“巳时。”
刘媗直接翻身下了床,奔出了屋门。
刘陵愣了愣,赶忙追了上去:“媗儿,你去哪儿?”
刘媗跑到马厩边,牵了仅剩的一匹马出来,翻身上马,对刘陵道:“我去追他。”
“你疯了?他们卯时就出发了!追不上的!”
刘媗顿了顿,还是坚持道:“能的,快一点就能的。”说着,双腿一夹马肚,一拉缰绳,“驾!”马儿便飞奔了出去。
快一点就能的。
似是告诉姐姐,也似是告诉自己。
刘陵气不打一处来,在身后追却又追不上,只能远远地喊道:“刘媗!别胡闹!快回来!你身子吃不消的!”
刘媗却毫不迟疑地驾着马奔向城门,一路上引起了阵阵骚动,掀翻了集市上许多摊子,她却也顾不上了。
她自然知道自己的身子吃不消。
可是……凶狠如匈奴,这绝不是一场好打的仗。更何况他还是将军,可是要带兵打头阵的。
如果这次见不到他,这一别……或许就再也见不到了。
刘媗越想越急,急火攻心,竟咳出一口血来。她却毫不在意地用衣袖抹了抹,驾着马出了城,越跑越快,“驾!”
大概走了十余里地,刘媗便有些撑不住了。她自患病以来,连走动都很少,更何况是骑马?马背上的颠簸实在是太过难受,她只觉得腹中翻江倒海,脸色愈加苍白。
现下已是入冬时节,天寒地冻,她又走得急,只穿了一件中衣便出了门。寒风凛冽,已经吹得她露在外面的皮肤毫无知觉。
可是她不能停,不能放弃。
如果她放弃了,可能就真的见不到韩衿了。
再跑快一点,再快一点,就能追上他了。
大概又行了二三里,刘媗已经冻得双手握不住缰绳。突然,眼前一黑,手一松,便落下了马。
身子重重地砸在地上,疼得刘媗倒吸一口凉气,眼前又清明了些。
马儿却不顾主人已经从背上掉了下来,继续撒开蹄子向前跑去。
刘媗从马上落下,内脏受到重创。旧疾未愈,再填新伤,她捂着胸口,咳出一口血来,雪白的中衣上沾染了大片血迹,触目惊心。
她试图爬起来,双手却因为牵了太久的缰绳,颤巍巍的使不上力。一用力,牵动了内脏,便又会咳出一大口血来。
刘媗别无他法,只能无力地躺在地上,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不知不觉中,眼角有冰凉的液体滑落。
终于再也支撑不住,连眼前的天空都变得模糊,刘媗闭上了眼睛,气若游丝。
失去意识的最后一刻,她嘴里还在念着。
“韩衿……”
不一会儿,便下起了雪。雪花纷纷扬扬飘落下来,在地上覆盖了薄薄的一层。
一望无垠的冰天雪地中,刘媗衣上的血如傲然的梅花一般,静静地绽放。
Chapter.6 媗殒
——摩肩人步履匆匆 多少相遇能有始有终
元狩元年,韩衿随卫青出击匈奴,歼灭匈奴军过万,大胜而归。
刚回到京城,便听说了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密谋反叛之事彻底爆发,刘陵、刘媗都被关入狱中。
韩衿马不停蹄地赶回大朝正殿,虽然已经心急如焚,可是不得不先跟随大军按照规矩在殿内领赏。
宦官在武帝身边念着圣旨:“大将军卫青,赏千金,不益封;将士霍去病独自领八百骑出击,俘虏匈奴单于的叔父和国相,斩单于的祖父等2028人,封冠军侯;将军韩衿……”
“且慢!”
韩衿走了出来,跪在大殿正中央。一时间,大殿内所有人都看向他。
韩衿叩首,“皇上,臣不想封侯,也不想要赏赐,只求皇上能让我见淮南翁主刘媗一面!”
武帝面色不善,“哦?难不成你与那反贼刘安也有所勾结?”
“臣不敢!臣只想见一见他的女儿刘媗!一面也好!”韩衿再次叩首。
武帝挑眉,“放肆!那可是反贼刘安的女儿!岂是你说见就见的!”
“那……那臣便在这未央宫跪着,跪到皇上应允为止!”
武帝拂袖,怒道:“随你!想跪便跪,朕不拦你!”
于是,韩衿便在未央宫叩首不止,直至额头破裂,血流满地,从清晨到黄昏,一刻都没有停过。
到了快要退朝的时辰,忽然有宦官来报。
“皇上,那反贼刘安之女刘媗本就病入膏肓,刚才似是旧疾复发,在狱中已无气息,请问如何处理?”
韩衿如遭雷劈,猛然直起身子,额头上血流如注,双目发红地盯着那宦官,“你说什么?”
宦官后退了两步,被他身上散发出的可怕的气息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哆哆嗦嗦的说不出话来。
武帝揉了揉太阳穴,无奈地挥了挥手,“罢了罢了,既然人都死了,你便带他去狱中,将尸身交与这小子处理吧。”
“谢皇上。”韩衿深深叩首,立即站起身来,身形不稳,晃了两晃,才跟着那宦官走了出去。
跟着宦官到了狱中,便看到了刘陵抱着刘媗哭得满脸是泪。刘媗闭着眼睛,除了面上没有一丝血色,倒像是睡着了一般。她骨瘦如柴,身上脏兮兮的,领口和袖口上还有大片的血迹。
看到这样的刘媗,韩衿的眼泪毫无预兆的大滴大滴砸落在地上。
刘陵抬首看向来人,更是怒从中来,边哭边指着韩衿骂道:“韩衿你这个时候来有个屁用!媗儿她已经走了,走了!她……她临走前还在喊着你的名字,却还是没能见你一面!”
韩衿低下头,颤声道:“……对不起。”
刘陵的脸上还挂着两行泪,竟是气的笑了出来,“对不起?哈哈哈哈哈,对不起!事到如今,你说对不起?真是可笑至极!
“你知道媗儿有多喜欢你吗?自你十年前去濮阳救灾的那次,她便每每缠着我爹打听你的动向!
“七年前,她到了可以出嫁的年纪,来提亲的人踏破了我家门槛,她却闭门不见,口口声声说着非你不嫁!
“四年前,她听说你来了长安,便执意要我带着她来长安办事,只为了那微乎其微的可能性,为了见你一面!
“去年,去年……你出击匈奴,她卧病在床,昏睡了两天,醒来听说你走了,不顾自己的身体,骑马一路向北去追你的军队!因为她怕你回不来,便再也见不到你了!可是,可是她的身体根本无法长途跋涉……
“我找到她的时候,她只穿着一件中衣,那样躺在荒无人烟的雪地里,胸前全都是血,只剩一丝气息……若我再晚一点,恐怕你现在连她的尸身都见不到了……
“韩衿,这些你都知道吗?你又知道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她有多爱你!事到如今,你说对不起,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啊?”
刘陵声嘶力竭,抱着刘媗泪如泉涌。
韩衿再也听不下去,双腿一软,跪在了地上。双手扶着监狱的铁栏杆,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媗儿……媗儿,对不起。
Chapter.7 尾声
——唯有亘古寒峰 能安葬浮生 至死不渝的一场梦
听说,刘媗身故后,韩衿亲手将其埋葬在终南山。
那以后,长安城内便流传着一首歌谣:茔茔蔓草,岁岁不老;风雨如晦,死生为谁。
佛说人生有七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 最苦不过求不得。
许多人是因为不敢追寻才不得,然而更可悲的是努力了、尝试了,依然不可得。
终南山上有一座坟墓,叫做不老坟。
终南山里不老坟,不老坟中不老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