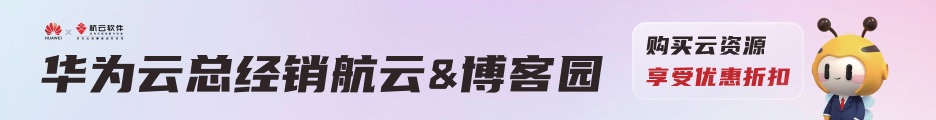1998年,我在读大二, 12月31日的凌晨5点多, 还沉浸在睡梦中的我,被急促的电话声叫醒。是父亲来电话悲伤的告之,爷爷已经在几个小时前去世了。我原以为正遭受病魔折磨的爷爷能坚持到1999年的元旦,这样孙辈能利用放假时间回家探望他,但老天无情,在年末带走了他。赶回家的我看了爷爷最后一眼,他双眼闭合,眼眶凹陷,脸庞廋削,似乎沉沉的睡去,但我们不得不接受他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的事实。父亲说,爷爷最后几天虽然身体虚弱,但脑子还是依旧清醒,在去世的头天晚上还从病床上坐起,观望了一下陪伴在自己身边儿子、女婿的纸牌牌局,甚至插了几句话。大家都高兴的说爷爷病情稳定了,还能迎来新春佳节,但天不成全,爷爷在这年终走完了依靠不断辛苦工作自食其力并抚养一大家人的一生。
爷爷1919年出生在湖北黄陂,家族以驾船运输为生,本来家底还算殷实,但爷爷的奶奶与叔叔由于染上吸鸦片烟的恶习,造成入不敷出。家里最后实在支撑不下去,爷爷与他父亲一起从黄陂走到汉口讨生活,当时爷爷才十岁左右。太爷爷做黄包车车夫,爷爷开始时四处捡废品,后来也子承父业,以瘦弱的身躯拉起笨重的黄包车。
1938年日军刚刚侵占武汉时,爷爷一家人跑回黄陂避难,听说当时睡在四面漏风的破屋里饥寒交迫。为生活所迫,爷爷在武汉会战结束后,又返回汉口继续拉黄包车来养家糊口。可以想象爷爷作为一个穷苦人在当时恃强凌弱的环境下,为了生活,忍气吞声的在社会底层挣扎着的情景。即使他一再小心翼翼,趾高气扬的日军还是弄瞎了他一只眼睛。无钱医治,只能勉强维持,但疼痛时常折磨着爷爷,直到解放后到医院安装了假眼,才结束了这种折磨。
新中国成立后,人力车夫成为了光荣的工人阶级一份子,社会地位提高了,但对上侍奉父母,对下抚育依次来到人世的三儿三女的重任,还是爷爷扛着。收入是微博的,生活需要精打细算,才能保证米缸有米,油壶有油。在当时消灭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宣传下,坐人力三轮车的人几乎没有了,爷爷的车改成人力货运车。为了多挣点钱养家,他连那些从汉口运货跨过长江大桥到武昌的活也接,甚至更远的青山和洪山。这种活,他会叫上儿女中的一人同去,因为上桥时有斜坡,他一个人实在无法拉上去,需要孩子出把力帮着从后面推。
生活是艰辛的,但爷爷一如既往的努力干活,竭尽所能改善家庭生活。他是个孝子,有好吃的东西总想让自己的母亲先尝。我太奶奶本是宁波人,是太爷爷驾船到浙江时娶回来的。爷爷想着自己母亲出嫁后再没回过娘家,又跟着受苦,总想让她生活过得更好点。太奶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接近六十岁时去世,听说那天爷爷嚎啕大哭,伤心至极。他对自己的子女是希望能学到一门手艺以便生活过得更好些,别无奢求。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父亲才16岁想跑到上海串联,可身无分文,奶奶是不支持的,说家里没有钱同时也担心儿子的出行。爷爷当时没有表态,默默拉着三轮车出去了,傍晚回来时给了我父亲两元钱,说出去见见世面也好。后来大家都无法继续读书的情况下,他让我父亲跟着黄陂老家的侯姓师傅做泥瓦工,学习砌砖粉墙的手艺。他对自己的孙辈是充满爱的。我姐姐刚出世时,爷爷十分高兴,亲自踩着三轮车把我妈和姐从医院接回来,还给了十块钱的红包。后来他还每天用三轮车送我姐和我上街道办的幼儿园,每次进园前他都要在杂货铺买山楂片或其他零食让我们带着。我们刚上小学时,他常给两分或五分的纸币作为零花钱,让我们在认识了纸币上的飞机轮船等图案时,也学会买杨梅等解馋。
改革开放后,生活渐渐改善,儿女们也依次成家立业。爷爷终于有精力和时间花费在自己的爱好上。他喜欢看戏,有次带我去戏院,由于我当时太小实在听不懂唱词,只顾看热闹,但发现爷爷观看的津津有味,脸上露出平时难得一见的笑容。后来戏院消失,爷爷就开始摆弄收音机,通常他先旋转频道按钮,找到戏曲频道后,接着调整伸缩天线的方向,直到杂音基本消失为止,最后他靠着床头,闭目养神的聆听着戏曲。爷爷还喜欢打一种纸牌,称作“撮牌”,黑色的长方块朔料牌两端印着红色的不同数量原点,类似麻将中的七筒和八筒,规则比较复杂,我观战几次也没搞懂,但爷爷却轻车熟路,游刃有余。
1990年代初,爷爷70岁出头时,身体依旧硬朗,还偶尔踩着三轮车出去载客,回来时常常自豪的说乘客不相信他已经70多。儿女们常劝他别再干活,多休息。但他却将这一辈子的工作变成了习惯和寄托。
爷爷的弟弟作为家中的幺儿在解放前上过几年私塾,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勘测设计院成为一名工程师,其工资待遇是要超过爷爷的,但他常说“我二哥人聪明,可惜没机会读书。” 没有钱读书的爷爷,就这样为社会奉献了一辈子体力,挣着微薄的辛苦钱抚养一大家人,牺牲自己,泽福后代。爷爷那拉着人力三轮车走出街巷的微驼背影,黑白遗像中廋削的脸庞永远定格在我们子孙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