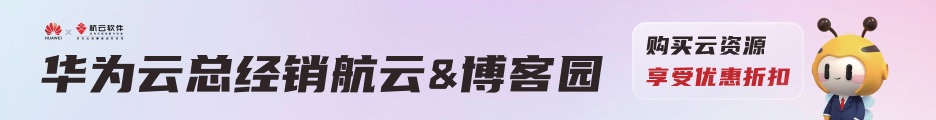《性情男女》--------徐坤
徐坤,1965年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毕业,文学博士,曾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现任北京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代表作有小说《先锋》、《热狗》、《遭遇爱情》、《鸟粪》、《狗日的足球》、《厨房》、《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爱你两周半》,话剧剧本《青狐》(改编自王蒙同名长篇小说)、《性情男女》等。作品被翻译成英、德、日语。曾多次获得《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优秀小说奖。获首届冯牧文学奖,首届女性文学成就奖,第九届庄重文文学奖,短篇小说《厨房》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作为一名写作风格犀利的新生代女作家,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徐坤在文学界几乎一直被人关注着,甚至有“女王朔”之称。从她刚刚踏上文坛时描写知识分子生活的小说《先锋》、《热狗》、《白话》、《鸟粪》,到后期描述女性生活和命运的《厨房》、《狗日的足球》、《遭遇爱情》、《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等,徐坤在一步步走向成熟的同时,始终不曾停止过其在艺术之路上的探索。2005年,徐坤第一次尝试写话剧,并连续写了两个话剧剧本:改编自王蒙同名小说的《青狐》以及眼下在北京人艺红红火火上演的小剧场话剧《性情男女》。《性情男女》从1月10日上演以来,首演15场场场爆满。从2月24日起,将开始第二轮演出———
爱情婚姻家庭是一个平常而又敏感的话题,跟每个人的经历都有瓜葛
问:《性情男女》是一出什么样的剧?
徐坤:简单地说,它是一则都市情感故事,是写一个中年成功人士,与他的爱妻、前妻及女儿之间的情感纠葛。一对离婚五年未见面的夫妻,被上初中的女儿诳去给过生日,两人突然间碰面,喜忧参半。丈夫因回家晚受到现任娇妻的审问***难,一气之下出门,不知不觉又走回前妻家。现任妻子追踪而至,打上门来。四人见面,一场冲突在所难免……
问:怎样想起来创作此剧的?
徐坤:爱情婚姻家庭是一个平常而又敏感的话题,跟每个人的经历都有瓜葛。“性情男女”原是我的一本散文集的书名,导演任鸣看到后觉得这是个话剧的好题目,就让我把它发展成一出小剧场话剧,并说最好能是写当下生活的。导演给框定了是小剧场话剧,势必要场景相对集中,戏剧冲突尖锐,人物也不能超过五个。我一直对古典戏剧的“三一律”着迷,就想尝试着做一下。没有什么比情感戏更能让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了。或许只有爱情能在瞬间内让人迷失方向、物我两忘,并能使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迅速达到白热化程度。
问:你想通过这个戏表现什么?
徐坤:爱情是什么?婚姻是什么?生活到底又是什么?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理解。剧中男主角结婚、偷情、离婚、再结婚、再偷情、再闹离婚……总也不能达到完满,似乎生活永远在别处。而剧中的两个女人,前妻和现任妻子,最终目标都希望有一个坚贞不渝的爱情和幸福的家庭。可见,婚姻生活当中,男人与女人的需求并不完全一致,剧中那个男人的表现让女人们十分失望。她们发现,想让一个男人守洁,简直是太困难了。这部戏并不在于给出答案,事实上也没有答案,只有对结果的预设和预期。但愿每个人都能从他人的故事中找见自己的影子,从他人的情感纠葛中省察自身的生活。对于男主角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怎样处理情感忠贞与肉体欲望之间的矛盾;对于女人来说,则在于如何修炼自己,让自己真正身心强大,能做到处变不惊。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情感变得特别脆弱,一撒手,就没了,再重拾,很困难。
问:你一直都在写小说,第一次写话剧顺利吗?
徐坤:对于一个寒窗二十载、又一辈子只在干一件写作职业的人来说,体裁和文体的界限不是问题,说到底,考验的还是个人对生活的认知以及艺术的功底。话剧比小说需要更剧烈的戏剧冲突,它把所有的心理描写和过程全删掉了,完全就是对话,句子更加精练,特别要功夫。另外,在写这部《性情男女》之前,我已经改编过王蒙先生的长篇小说《青狐》,那个剧本是一个真正艰苦的攀登高山的过程,整个写作修改过程长达半年之久。为了那部剧,我重读了从古典到现代的大量戏剧经典。《性情男女》正是在交那个剧本稿子的时候被提起动议的,几乎就是《青狐》剧本的副产品。写作过程很快,一稿出来大概用了不到一星期的时间,然后搁置了半年,到了九月份,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来修改。剧本拿去不到一个星期,就来电话说通过了。再有,我特别喜欢话剧,崇拜人艺,是北京人艺忠实的发烧友,人艺所有的大戏、经典戏全都看过,年轻时就憧憬着有一天自己的戏也能在人艺上演。后来当上了北京市青联委员,遇见任鸣,他是副主席,正好领导我们文化组的工作。承蒙他多次相邀写剧本,事情就这样促成了。
写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很珍重并热爱它
问:每次你有新作品出来时,都有媒体报道说:“女王朔”徐坤又出新作,你怎么看?
徐坤:我好像已经是第一千零一次回答这个问题了,说得已经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就连“右派”都有个摘帽的时候,我这个帽子,看起来却要永远戴着 !
问:是什么时候开始被这么冠名的?
徐坤:十几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刚刚迈入文坛的新人的时候,也是王朔写作风头正健的时候。
问:年头已经不短啦!怎么还在用?
徐坤:我也不知道,或许是媒体叫顺嘴了吧?这个冠名,我认为有“使用过度”之罪,建议王朔委托代理人定下一个规则,他自己的名字免费使用在别人身上的年限最长为一年,过期以后,就要酌情收取使用费。
问:当初是怎么来的?
徐坤:最初那会儿我写了一批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像《白话》、《先锋》、《热狗》等,被认为颇具颠覆性。王朔那时的一些作品如《渴望》等,也正针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弊病进行抨击。也许这就是媒体将两个风格似乎相像的作者进行“比附”的原因吧!
问:你认同自己是女王朔吗?
徐坤:我很尊重作家王朔。无论当下人对他怎么评价,我们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史以致思想史上,都会留下他浓墨重彩且颇具争议的一笔。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对于“女王朔”这个命名,根本不是我个人认同不认同的问题,也不是王朔厌烦不厌烦的问题,而是媒体和批评家的硬性评定问题,还有就是媒体可能说顺嘴了。不管这个称号是怎样造成的,凭良心说,我都要感谢王朔,不是人家王朔借我的光,而是我借着人家王朔的光出名啦!并且这么多年来还在免费使用,他都一声不吭,真是好人呐!回头想一想,也是呀!在那个年代,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还基本上是一个男权时代,尚不流行“美女作家”一说。一个小女作者要想露头,还必须将名字附属在男性作家的名字后头才能得到提携。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形势已大变,新一代女作家再没福分被叫做“女莫言”、“女苏童”、“女平凹”什么的,那样似乎显得对女性不恭。有的女作家就只能靠自己强调自己胳膊腿儿的一部分,比方说“下半身”、“宝贝”、“胸口”什么的来为自己的写作命名啦。其势也险!
问:写作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徐坤:写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珍重它、热爱它。假使有一天我不能够写作,生命也将失去意义。
“尖锐”是一种文化姿态,我比较喜欢那种有穿透力的东西
问:再回到戏剧本身。你第一次和演员见面时有什么想法?
徐坤:记得我第一次跟剧组演员见面,是去年11月30日,我刚从美国回来,还没倒过时差,被通知去看联排。迷迷糊糊的,走进排练厅,第一眼见到几个演员时,简直被他们的青春靓丽、美丽逼人吓了一大跳!《性情男女》写的是中年人的是非恩怨,而眼前的分明是几个二十出头的毛孩子!当时心里还在打鼓:任鸣怎么挑的演员?等到联排一开始,几个小青年的戏就出彩儿了!那时距离他们18日建组也只有十几天的工夫,就已经表演得相当不错。后来听任导演介绍说,他们都是很有成绩的优秀青年演员,男主角谷智鑫演过电视剧《骆驼祥子》和青年毛主席,“妻子”程莉莎演过《太祖秘史》里的妃子阿巴亥,“前妻”张培演过电视剧《不嫁则已》的主角,“女儿”韩清是话剧《hi·可爱》里那个小“可爱”。真没想到,他们青春欢快的肢体,却能把中年人饱经感情创痛后忧伤、惆怅、沧桑、疲惫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到底是人艺的演员,功底好,又敬业,为演戏,都舍得拼命。尤其演前妻的那个小张培,根据剧情,逢到伤心动情处,必得痛哭。演一轮就得十几场二十几场,一场一场地哭下来,那得多少眼泪、得耗多少神啊!
问:你觉得这个戏能引起观众共鸣的关键是什么?
徐坤:一部戏首先要打动创作者自身,然后才能真正打动观众。这个戏联排时,先由编剧讲创作经过。我记得在给张培讲那个前妻角色时,觉得他们的前夫前妻见面设计得太过刚性,前妻忿忿,吵得太凶。有一个场景是前妻先扭过脸去哽咽,然后回过脸来劈头盖脸数落前老公。我跟她说,他们见面时,前妻不是硬硬地数落,不是恨,也不是忿,是怨,是痛,是边说边流泪。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别说是一个人啊,就是养的一只猫,一只狗,在一起生活了十多年了,突然之间,说走就走了,你想想,我是什么心情啊……”说到这儿,我自己突然间就哽咽,泪流满面!在场的人都愣了……
问:在首演结束后的观众与剧组见面会上,观众提问任鸣导演,你的本子有什么特点,导演说你很“尖锐”,你认为是吗?
徐坤:“尖锐”是一种文化姿态,我比较喜欢那种有穿透力的写作,戳穿一切温和表象,揭示人的本质,并不断向生活发出拷问。相比较而言,任鸣导演的戏比较温和。我原来的本子比现在舞台所呈现出来的更具有杀伤力,他在二度创作中不断完善,能将戏调整到这个程度,非常不易。这个戏之所以能引起观众共鸣,我认为除了尖锐、毫不留情外,还因为有痛,我自己曾有过一段难忘的婚姻情感经历。因此,我是痛定思痛。这个戏演到伤心处,我看到剧场里很多人,尤其是女观众,都跟我一起落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