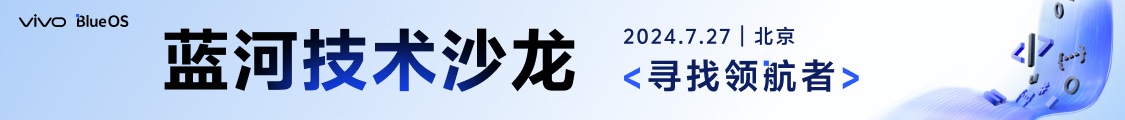棉田趣事
回乡以后,我就在生产队劳动。不管当时政策如何,乡亲们对我这个“知识分子”是很看重的。从一九七零年以后的几年,我一直在生产队当棉花技术员。
我当棉花技术员给别人不一样,从棉花一种上到收摘完,一直住在棉花地。一是地里有电;二是喜欢地里的夜景,反正是个光棍汉,住在哪里都一样;更重要的是也为队里守了夜,每夜二分工呢。
棉花地有口机井,机井上有一部电动水车。靠着机井台,我盖了一个小屋,这里就是我的精神家园了。夜里,我可以在电灯下看看书,弹弹三弦琴。三弦琴是借朋友的,由于没有音乐底子,好长时间才自学会了《国际歌》《东方红》两首歌。由于田野空旷,夜深人静,琴声传得很远。很久以后,无意中见到一位老教师的回忆录,其中一段是这么写的:“一个回乡知识青年,在田间野地,茫茫黑夜,弹着《国际歌》,度过了他最艰难最困苦的日子。”我很以为知己。
夜间寂寞,便想找点事做。我找了两个旧式电话机上的大电池,取出中间的两只碳棒,相距十五公分,固定在一片胶木板上,放在水桶里烧水喝。后来,便开始煮红薯,毛豆角,豇豆角。试想一下,夜色美好,朦胧而神秘,一边品着这新鲜美味的稀罕物,该是一种多么惬意的享受啊!
一个人玩得不过瘾,我让我的助手好朋友喜春也来参加。我们扩大了“?索”范围,凡是能吃的,花生,毛豆,南瓜,冬瓜,都弄来吃了个遍。反正生产队地块大,我们又小心,吃了之后,“痕迹”打扫利索,任谁也没发现我们的秘密。
有一天晚上,我们煮了半桶红薯,已经煮熟了,正要动手来吃,忽然听见地头有脚步声。借着朦胧的月光看去,看见一个人影朝我们走过来。我连忙拔掉电源,让喜春把水桶掂到棉花地深处去。来人走到跟前,原来是队长偏头哥。他在大队部开完会,看见灯光,就信步走过来。他走到小屋里,用鼻子嗅了嗅,说:“怎么有煮红薯味?”不用他说,煮红薯味儿大得很,谁都能闻得到。虽然在队里我以诚实出名,可这个秘密绝对不能让队长知道。我给他打哈哈,说:“什么红薯味?是你想红薯了。”“真的是煮红薯味儿。”“这里没火没灶,哪来的煮红薯味?是你的幻觉。”偏头哥想了想,自己先笑了,显然相信了我的话,随便给我聊了几句,便起身走了。等偏头哥走远了,我和喜春笑得肚子痛。完了,我们掂来水桶,大快朵颐,饱餐一顿。在我的印象中,包括后来发达,吃过的海参鲍鱼大宴,也没有那个煮红薯美味。
口福是享了,可心里总像有一块东西压着。每当夜深人静,我看着正北方向漯河市上空冲天的灯光,问自己:“难道我一辈子要终老在这无人知道的野地里吗?”
自己的心事,别人是不知道的。我努力工作,选种、育种,打叉治虫。第一年,我们生产队的十亩棉花就突破了百斤,成为全公社产量最高的棉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