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田中
“特蕾莎!”霍顿朝那个女孩喊道。“离开那里!不要破坏空间站!”
“呃,”田中心想,“我们不是搞砸了吧?”
那个女孩置之度外,撕扯着穿插进高级领事身体的黑线。这不在她的规划中,更不是她或特雷霍所预期和希望的。她必须很快做出一些独立决策。
女孩颤抖着跳开,但不是以一种正常的方式。有什么东西抓住她,把她从成了杜阿尔特的外星物旁边举起。霍顿脸上毫无掩饰的恐慌告诉她,他知道那是什么,而且不是善类。女孩尖叫着,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尖叫,霍顿抓住她,把自己拉到她身边。有一瞬间,女孩看起来像在变宽。田中差不多想象得到,有看不见的“天使”正拉扯着她的双臂和双腿。她想起,曾经有过这样的死刑。在囚犯的四肢上各拴一匹马,看哪一匹保留了最大的一块。但她看到霍顿竭力大喊,“天使”全都消失了,那个女孩安然无恙。
“我天,你失望了?没看到那个女孩被杀你很失望?”脑海中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你这人到底什么毛病啊?你是如何生活的?”然后,另一件事——事关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攫住了她,地点在伊尼斯行政官的办公室,那是11岁的她。行政官解释着她父母的死亡,言语之中透着无法言喻但清清楚楚的怜悯。这就是她出毛病的原因,这就是她伤害别人的原因,这就是她只和自己能控制的男人“双爽”的原因。她一直处于恐惧当中,环境造就了现在的她。
“我向上帝发誓,”她说,声音很轻,不至于让霍顿和那个女孩听见。“如果你不从我身上滚开,我就射穿我的脑袋。”
霍顿在跟那个女孩说话,田中毫不在乎。温斯顿·杜阿尔特扭动着,苍白的身体仍然裹着黑色的线,就像有人把它们缝进了他的身体一样。事实证明,父爱亲情的计划行不通。那个女孩没有用处了,而她的任务——把高级领事带回给特雷霍——现在也不可能实现了。即使杜阿尔特能够离开这个地方,特雷霍和拉科尼亚也不会以人类的方式存在。
这意味着她的欧米伽身份毫无意义。有比这更好的,她有了自由,可以做任何她认为合适的事情,除非有人胆大到阻止她。
急促、嘈杂的声音传来,像是士兵在行进。通往这个明亮、炽热房间的通道,一个接一个的昆虫形状的外星卫兵涌过来。田中感到自己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霍顿,我们有麻烦了。”
他低声说了一句脏话。女孩在哭,蓝色的萤火虫像篝火上的火花一样旋转着。
“如果你伤害它们,它们会把你扯碎,用你的身体修复你造成的损坏。”
“你能够保护那个女孩吗?”
霍顿迷糊了片刻。他的皮肤看起来不大正常。
他的皮肤下面,仿佛有珍珠母版本的他在生长。“我……可以吗?我想可以吧?”
田中把前臂上的锵换成穿甲弹。“很好。现在帮我忙吧。”
她的第一锵射向杜阿尔特,但是先锋卫兵撞过来,妨碍了她瞄准。她被撞到一边,旋转起来,但她紧紧抓住了袭击者。卫兵没有脸,没有眼睛,更像是机器而非有机体。她把拳头放在它所谓的胸部,指关节抵在它铠甲或外骨骼的奇怪板上,然后开火。尽管被她的动力铠甲所削弱,后坐力反弹也是极大。那个卫兵抽搐一下,再也不动了,然后又上来2个。她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拽着她,就像一股无法被铠甲传感器阵列识别的磁力一样,随后一阵钢针刺进身体的疼痛袭来。其中一个卫兵挥舞着长柄大镰刀般的手臂砍向她,刀锋掠过她的胸膛,她瞥见霍顿,他一边用身体护着那个女孩,一边奋尽全力,牙齿外露。
针刺的感觉消失了,她抓起卫兵镰刀形的手臂,用脚抵住它的身体,把手臂扯了下来。现在,她周围的卫兵更多了,它们猛烈地撞击着她,耳朵被撞击声震得嗡嗡作响。她在战斗的荣耀中迷失了片刻,摧毁能抓住的,射击无法够得到的。
卫兵太多了,获胜的希望极其渺茫。其中一个卫兵幸运地砍中了她,一片甲壳卡在她铠甲的左肩关节处。另一个卫兵把自己缠在她的右腿上,哪怕她朝她打了十几发子弹,它也没有松开。它们围着她,扑向她,然后死去,让路给身后的十几个同伴。她换回燃烧弹,周围的一切燃烧起来,但敌人继续穿过膨胀的火球扑来。其中两个抓住她的右臂,在它们之间把动力铠甲折弯。然后又有两个抓住她的左臂。她不知道自己杀了多少卫兵,但肯定不止一打。现在,它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对付她的有效策略。
她不停地射击,不过它们现在控制着她的目标。她最大的希望是其中一些跌入火线,死在那里。霍顿包裹住那个女孩,闭着眼睛,皮肤上大汗淋漓。在他身后,穿过卫兵,是杜阿尔特。
那个她为之而背叛火星的男人,像一块湿破布在微风中飘动。他那双明亮、没有聚焦点的眼睛让她想起奥科耶的宠物“催化剂”。蓝色的萤火虫沿着黑线穿梭,把他缝回原处。她不可怜他,现在对他只剩轻蔑。
那双发光的眼睛转向她,似乎像第一次见到她那样盯着她看。她意识深处有东西被打开了,是被扭开的,随后杜阿尔特流入了她体内。与他——它——那巨大的意识漩涡相比,艾莉安娜·田中这个意念显得遥远又渺小。一只反抗蚁丘的蚂蚁被撕裂了。没有哪只黄蜂背叛蜂群还能存活。
卫兵们把她拖向他和他的黑色巨网,这令她无地自容。她感到一股海洋般广大的耻辱,这种耻辱是一种违背她意愿的惩罚——一种操纵,一个表明她的意愿可以被命令左右的证据——这无关紧要。不远处,那个女孩在为她的父亲尖叫着,而在她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年幼的艾莉安娜·田中为失去父母而哭泣,为背叛精神上的父亲的邪恶行为而哭泣,为拉科尼亚的理想而哭泣。各种声音淹没了她,哀号和愤怒像喷砂机一样冲刷着她。她发现自己在他们的关注下崩溃了,最后只剩下悲伤。另一个声音在脑海中说“进行着的是亲密攻击”,那已不再是她自己的声音。她的私密空间被入侵,那是只属于她自己的部分。
接着又传来一个声音。这个声音不是来自杜阿尔特或他的蜂群思维,而是来自她自身,她的过去。如果不是疼痛继续,她也许不会听到。那是明里姑妈的声音,“你感到难过,还是感到愤怒?”她感到姑妈的巴掌刺痛了自己仍在愈合的脸颊。“你感到难过,还是感到愤怒?”
“是愤怒。”田中想,因为她真的愤怒了。
她抬起头。她距离杜阿尔特不足8米远,他就在那破裂、漆黑的摇篮里。她无法行动。卫兵们将她控制得很牢,要把她撕成碎片。但是它们紧紧抓着的是她的动力铠甲,而非她本身。
多年来,一直在不同形式的战斗中训练带给她的好处很简单:行动快于思考。不假思索,没有对应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权衡,不列计划——因为不需要。动力铠甲像花蕾盛开一样在紧急情况下炸开,紧抓她的昆虫形外星卫兵像花瓣一样散开去。她已经从它们的禁锢中脱身了。皮肤接触到的空气,护身内衣铠甲的轻盈,房间里难以忍受的热度,这些体验一闪而过,因为她清楚这些无需关注。她清楚,任一卫兵的一记重击都会让她皮开肉绽,但她毫不害怕。
她瞬即穿过缝隙冲向杜阿尔特,从他身边滑过,来到那个女孩撕扯后留下孔洞的地方。她一只手臂锁住他的喉咙,双腿缠住他的腰。他的身体极烫,几乎令人作痛,但她已经就位了。在这个位置,她可以用上全身的力量,经由背部发力,扭转杜阿尔特的颈部。那个女孩在某处尖叫着,霍顿大喊着什么。田中边拉边扭,杜阿尔特的脖子像锵声一样断裂。她感觉到了,也听到了。如果有重力,他的头会歪到一边,头骨的重量会让它下垂。而在这里,上述情况没有发生。
卫兵们乱颤,霍顿又在大喊。有什么东西像黄蜂一样刺中她的手臂,一缕黑色的细丝扎进皮肤。在刺中的地方,半球形的深红色血液涌出来。她把血液拍走,这时霍顿再次大喊。这次,她明白了。
他没死。
杜阿尔特在她仍然缠着的双腿之间移动。她脑海的声音演变成一声尖叫。本能在她身上博弈:推开它逃走,还是发起攻击。她俯身攻击。
霍顿漂浮着,在3个轴向上慢慢转动。他把女孩抱在怀里,她的头蜷缩在他的脖子上,遮住眼睛。他的皮肤斑驳明亮,因发力而扭曲。卫兵们抽搐着,向她跳去,然后又向后退却。卫兵只是工具,如今它们有两个主人,两人的命令互相冲突,令它们无所适从。她的最后一战,竟是和踏马的詹姆斯·霍顿并肩战斗。
田中朝杜阿尔特的肋骨打了两拳。第二次,她感觉到他的肋骨断裂了。又一次钉刺,又一根丝线,这次是她的腿。她将之拂去。之前那个女孩想把她爸爸从网中拉出来,虽然手法业余,但也造成了一些损毁。田中不知道杜阿尔特和丝线之间的关系,但她看出了弱点。对付它不适合刀手斜击①,但她可以自由发挥。她保持双腿缠住、手臂环绕杜阿尔特断折脖子的姿势不变,手掌做刀状砍向丝线和他身体接触的地方。每击一次,就有更多的丝线被撕开。黑色的液体渗到空气中,她不知道是出自杜阿尔特还是丝线。
杜阿尔特在她身上扭动着,他痛苦的挣扎令她更加难以控制。她的大腿内侧烫得生疼,就像被他泼了酸液一样,不过疼痛只是一个信号。她不必在意。她不停地把丝线砍下。等他侧面自由的时候,他的手臂挥向她,击打着她的脸和头部的一侧。现在,她脑海中的尖叫声不绝于耳。
她想改变姿势以便攻击杜阿尔特的另一侧,发现手臂上的皮肤已经破裂。杜阿尔特的喉咙里涌出细小的分泌物,像鼻涕虫一样又浓又黏。它们透过衣袖,渗透到她胳膊的皮肉上。她试图抽出双腿,但做不到。
“呵,你个混蛋!”她说。策略失效,她用拳头猛击杜阿尔特的一侧,每一拳都能击碎骨头。这个曾经是全人类领袖的东西痛苦地尖叫着,她从尖叫声中体验到快乐。有什么东西挤进她的肚子,像蛇一样蠕动着钻进她体内。她加重指力,用力按压杜阿尔特胸腔末端的柔软处,在她的重压下,他的肉体裂开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并不好玩,是不是,你个混账东西,”田中说。“不喜欢让它发生在你身上吧。”
墨黑色的血使她的手滑溜溜的,指甲下面开始刺痛。她的指尖穿过一层坚韧的肌肉,伸入他体内。那个像蛇一样的东西在她内脏里抽打和扭动,带来超乎寻常的疼痛。她把他紧紧地拉近自己,他胸膛里有什么东西像麻雀一样扑扑跳动。她抓住它,把它抓碎,然后用力把手往更深的地方伸去。
突然,一切全都变白。有几秒钟,她失去了意识。等她恢复过来,头脑异常清醒。这是从“普瑞斯”号变为“飞翔的荷兰人”又复活后,她第一次拥有自己。她咳嗽着,有血的味道。
穿插进她和杜阿尔特身体里的丝线松开了,漂浮在闷热如火炉的空气中,看着像来自地狱的烟雾。田中的呼吸细若游丝,尽力想深吸一口气都做不到。她把双腿从杜阿尔特的尸体上移开,丢失的肉大小如高尔夫球,里面聚集着血液。当她试图把他推开时,那个像蛇一样的东西断开了,但仍然卡在她的内脏里。
杜阿尔特漂浮着,慢慢地旋转,空洞的眼睛掠过她。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她一直担任拉科尼亚帝国的军官,而且做得很好。但在更长的时间里,她一直是她自己。
在她左边,霍顿和那个女孩一动不动。他们周围,一群卫兵变成了雕像。霍顿和她目光相对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仍有人性,她能从他的脸上看到恐惧和嫌恶。她希望自己能有一把锵,这样她就可以给他们每人一颗子弹,射穿他们,看着他们和自己一起流血。她伸出手臂,食指指向前方,大拇指抬起,瞄准霍顿的脸。
“砰,狗日的。”她说。
最后一件令她愤怒的事情是,他没有死。
译注
①刀手斜击:原文“shuto-uchi”,英文“Knifehand Strike”,示意图:

by 印象
译:22.6.17,22.6.18
校:22.6.18,22.10.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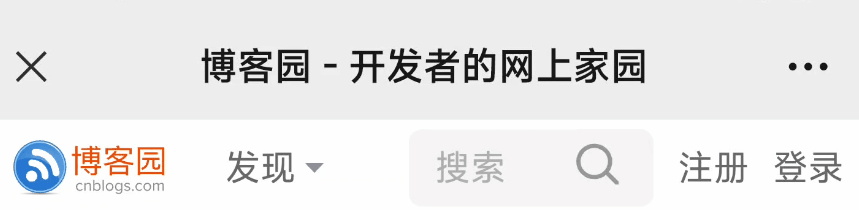
【推荐】国内首个AI IDE,深度理解中文开发场景,立即下载体验Trae
【推荐】编程新体验,更懂你的AI,立即体验豆包MarsCode编程助手
【推荐】抖音旗下AI助手豆包,你的智能百科全书,全免费不限次数
【推荐】轻量又高性能的 SSH 工具 IShell:AI 加持,快人一步
· 阿里最新开源QwQ-32B,效果媲美deepseek-r1满血版,部署成本又又又降低了!
· 单线程的Redis速度为什么快?
· SQL Server 2025 AI相关能力初探
· AI编程工具终极对决:字节Trae VS Cursor,谁才是开发者新宠?
· 展开说说关于C#中ORM框架的用法!
2021-06-18 “画饼”陷阱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