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HB To Ryby!)
“客人,请描述得具体一点。”
他似乎还是很难为情。
“呃……就是……一个女孩儿”,他又勉强启开嘴,“女孩儿”三个字几乎被咽进嗓子里,“背对着画面……”
“她的特征呢?我们从头部开始吧。”
“她……呃……有兔耳朵……”
攀上耳根的红晕烧的他心乱,他每说一句话都像在招供什么天大的秘密。
“嗯,我明白。为什么是兔耳朵呢?”
“我……她的名字是从一首歌名取的吧……这样似乎挺可爱的。”
“名字?她有名字吗?您方便告诉我吗?这或许有帮助。”
“她叫……哎,算了吧。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像是他的口头禅,虽然他现在一定真的很“不好意思”。
“没什么的。那么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兔耳朵呢?”
画师飞快的画出了几份样稿——或许只是他已经对时间失去了概念。
“没有那么长……这个样子吧”,他伸手指向其中一幅,“但要稍微搭下去一点点,略微向两侧倒一点……看上去没有那么精神。”
“我知道了。不过,她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小女孩儿吗?”
“嗯……不算是。”
“好的。头发呢?是白色的小兔子吗?”
“灰色。大概过肩吧,自然搭着的。我……我也不知道什么发型的名字。”
“眼睛呢?她的神情?”
“她背对着画面。”他回答了一个简单的问题。
“是红色的吗?红眼睛的小兔子。”面前的画师似乎很执着于这个问题。
“……是的。她可能背对着画面在哭吧,很冷淡地流着眼泪。或者……是在朝前面笑吗?我也拿不准……”
画师点点头,顺手用手杖敲了敲地板,“噔,噔——”,像是在确认着什么,然后笃定道:“她在哭。我觉得您其实很确定她在哭。”
“……”
“衣服呢?”
“白色的连衣裙。”
“哈……很朴素的选择。从背后看的话几乎是黑白的构图,不觉得单调吗?”
“或许是吧。”他沉沉地回答着,捏了捏拳头。
“没关系——您要喝点水吗?”
画师转过身,将杯子推到坐在身侧的他的手边。杯子轻轻撞在了他的手背,杯中的水面晃着波纹,摆弄着画室里唯一一支昏烛的烛光。他有些恍惚地接过杯子。杯子里倒映着他的影子。他的影子有着他很陌生的样子。他为什么会坐在这里呢?像是来求画师解梦一样。好像是黑得粘稠的梦啊……
“您似乎不太喜欢这蜡烛?”画师突然发问,没等他回话,伸手灭了烛,烛火的悉窣声匿入黑暗,烛光的残影也在他的眼中渐渐褪去。
“我们继续吧。女孩儿的动作呢?”
“她赤裸着双脚向前走。重心移到了迈出的左脚上,右脚正踮起……左手握拳摆在胸口,右手提捏起身侧的裙摆……”似乎只是在对着黑暗自白而已,他语言变得流畅了许多。
“提捏起身侧的裙摆?”
“啊,忘记说了……她站在一个很小的白色圆圈里,圆圈的大小刚好圈住她的身子。她前方圆圈边沿延伸出一条很细很亮的白线,她正沿着线走着……身后圆圈外的黑色攒动着,有一小块黑渍溅在了裙角,所以她把裙摆捏住提高一些……”
“纯黑的背景,纯白的亮路,被沾脏的裙角——对了,恕我冒犯,您也许有些洁癖吧?”
他不知道画师如何看出了这一点。是因为自己刚刚犹豫地转着杯子的动作?但她真的能注意到吗?
“为什么一定要沾脏她的纯白的裙子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他并不需要对着黑暗抑制泪水,又或许他并没有那么激动,只是单纯地仰起头,想象着看不见的天花板,想象着她纯白的身影,想象着她被玷污的裙角。她的左手握得那样紧,几道很深的皱纹挤在也拧在右手掌心。她哭得更伤心了,她一定想要用刀把这黑色割掉,哪怕残缺也无所谓。但她没有刀,她手里什么也没有。他没有给她那样的武器。好脏……她真的难以忍受,她想要跑得更快,跑到白线的尽头去。但圆圈怎么跟得那么慢,还越来越小,她怕自己的脚会踩到黑潭里。白线的尽头又如何?那里有什么?她不知道。她甚至不敢伸手去擦一擦那块黑色,她怕自己会想要砍断自己的手指……她哪里是冷淡地在哭啊,她明明快要因周身的黑色而崩溃了。
“我想,我了解得差不多了,请您稍等。”
画家开始了她的作画。他索性闭上了眼睛,寻找着黑暗中一种令他安宁的失重感。
远钟低振,子时过半。相对于太阳,地球回到了如十八年前一样的位置。仅仅是相对于太阳的重逢罢了,真的微不足道。
“噗——”暖暖的光凑上他的脸颊,画师似乎算准了时间,点上蜡烛,请客人过目已完成的画作。
耳朵、白裙、污渍。但她正面对着他。但她正迈出那一步。她的右脚已提到左腿侧。白线指向了他,在她即将落脚的地方滋长开像是幼根般的灰白纹丝。她的右手松开了裙摆,舒展开的褶皱正向身侧漾去。她的头略抬起,双唇微启,看着画面外的他,或是看着白线的远方。
他的目光却无法移开她的眼睛。
红色的眼睛,小兔子的温顺的眼睛,曾冷漠地流着泪的眼睛,被远远的绚烂点亮。涌出的泪泊上,倒映着她的前方,那是喧闹的光点,雀跃的光点。她的头顶仍是一片漆黑,她的身后仍是一片漆黑。他最熟悉的意象,他最惯用的隐喻,他笔端无休地赞美着的,那些光点,从她的天空消失,却聚萃着闪烁在她的眼中。
画师无声地掐灭烛光,起身,握着手杖,走近窗边,拉开厚帘,像是欣赏着窗外的夜色。
“噔,噔——”
用力的两声。手杖空旷的回声被困在画室里。
“很遗憾,我从未见过它们。你知道,盲杖的声音去不了天上。”
“——客人?”
他颤抖地哼了一声,又艰难地加重了回应,帮助转过头的她准确地面向自己。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零点,以她为中心的星空,该是什么样子呢?”
“啊……不知道您是否满意。我需要画出您想看到的画作……”
“于是呢,我学着您的诗行,在最黯淡的地方,涂上星星的糖霜。”
“——客人?”
他没有回应。她的手杖并未被敲响。她靠在窗边,听着黑暗中的哽咽。
“对了,客人——
“祝您生日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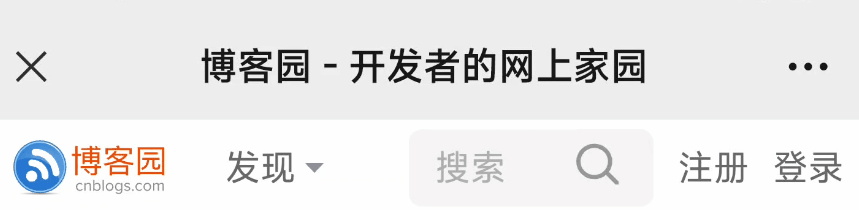
【推荐】国内首个AI IDE,深度理解中文开发场景,立即下载体验Trae
【推荐】编程新体验,更懂你的AI,立即体验豆包MarsCode编程助手
【推荐】抖音旗下AI助手豆包,你的智能百科全书,全免费不限次数
【推荐】轻量又高性能的 SSH 工具 IShell:AI 加持,快人一步
· 分享一个免费、快速、无限量使用的满血 DeepSeek R1 模型,支持深度思考和联网搜索!
· 基于 Docker 搭建 FRP 内网穿透开源项目(很简单哒)
· ollama系列01:轻松3步本地部署deepseek,普通电脑可用
· 25岁的心里话
· 按钮权限的设计及实现
2023-01-27 Solution Set -「DS 专题」兔年的兔子写 DS 会有小常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