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音乐
之所以把音乐划分为一些各自独立的阶段,是因为每个阶段都体现出大量的共性特征,这有助于我们厘清混乱无序连续出现的事件之间的关系。二十世纪音乐是一个时间范畴,也是一个风格范畴:这一世纪的音乐建立在明显不同的美学和技术基础上。1907-1908年,勋伯格第一次完全打破了传统的调性体系。从技术角度看,传统调性的瓦解在塑造现代音乐的过程中是唯一最重要的因素。这一瓦解不是一瞬间的,整个十九世纪都目睹了调性结构力的逐渐弱化。调性——某个特定的音高具有支配性地位的属性——能够使得音乐清晰无误、方向明确地运动延展,作曲家可以基于调性构思长时间、自律性地音乐结构。这样的音乐往往是组织上有逻辑、音响上有意义的:由乐句构成乐段,乐段构成更大的段落等等。就像小说的一句话、一段话、一个章节一样。这样的传统调性音乐是1700-1900年两个世纪内共用的音乐语言。十九世纪音乐的发展渐渐削弱了这一共性,造成这种偏离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音乐从更大的社会和文化框架中脱离,创作者不必担心广大普通公众的理解和感受,音乐能够独立地以个人情感表达的方式自由发展,对更加个性化音乐表达的诉求不断增长。从贝多芬开始,人们已经感受到一种不断增长的决心,要给予每一部作品属于它自己的独特印记。这是对那些过去公认的、长期习惯了的假定发起的攻击。为了体现出个性,半音化与不协和不断被强调,调的中心更多的是被暗示而不是实际表现出来,各种调的选取不再约定俗成,而呈现出“动机的”面貌,成为了作品具有的一种“独特性”。以往在调性明确的段落与转调的段落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现在这一界限却越来越模糊,音乐接近于一种几乎不间断的流动状态。这种模糊性是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很大的区别,清晰不再是一种必然的渴望,模糊甚至晦涩成为了一种新的形式感的共识。浪漫主义不再追求界限明确的形式单元,而是把音乐看作是不断生长演变的一个连贯整体,音乐由此获得了一种更加“开放”的性质。
古斯塔夫·马勒 (Gustav Mahler)
古斯塔夫·马勒(1860-1911)出生于波希米亚卡里什特,他的音乐活动中心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他成为了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作曲家和指挥家。这个时代的一大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致力于重构传统的信念,以发展新的思维模式、新的语言表达方式以及新的视听方法。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帮助奠定了现代知识和艺术的基础。
马勒的代表作品是他的九部交响曲(以及《大地之歌》)。马勒可以被看作是德奥交响乐作曲家中的最后一位大师——从海顿、莫扎特到贝多芬,再到舒伯特、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最后到马勒。在这个过程中,交响乐向着更长、更宏大的编制不断发展。马勒继续了这一发展并把它带向了最具特色的顶峰。他的音乐中,一种抒情性特质以更为强烈的程度得以渗透。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一样,他也时常把人声与合唱引入交响曲。
马勒的成熟作品展示了一种矛盾和闪烁不定的性质,这正是现代音乐的独特之处,这种特性最清晰地体现在和声和调性关系上。马勒的和声语言在大多数时候仍然是传统的,现代音乐的高度半音化和不协和并不是马勒音乐的主要特色。然而,马勒音乐中的调性已然接近瓦解的最后边缘:完整的作品,甚至其每个不同乐章,已不再必然地限定在一个单一调性中,而是扩展到了一个更大的相关和相互联系的范围,音乐常常结束在一个不同于乐曲开始时所用的调上。这样的处理方法改变了调性的根本意义,使得调性变成了一个相互关系交织的复杂网络,而不再是一个进行方向单一、确定的封闭系统。
这些调性实践源自马勒关于音乐形式的创新观念,他把音乐形式看作是一个由许多单一片段组成的连续体,这些片段由不同的调性连接以及动机呼应链接在一起。在不同片段之间,马勒常常展现一种“突然对立”的模式。在马勒的作品中,音乐的连续性由一种高度的分离和并置,以及在广泛对比的乐思间高度的快速切换而明显地体现出来。马勒更加开放的观念使得他能够结合极其极端对比的材料,这在较为传统的音乐中是对内在一致性的摧毁。但马勒认为,交响曲意味着运用一切手段去构建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包含一切的,一切流行的、甚至粗俗的音乐成分也应当被包含在内。
马勒音乐的织体常常是复调性质的,这一点受到了他极其敬仰的巴赫音乐的影响。十九世纪后期许多作曲家和声观念中所特有的“伴奏性填充物”被刻意回避,取而代之的是由具有真正旋律意义的多个线条构成的织体化写作,这就产生了一个丰富的包含细腻而多变的动机呼应的声部网络。尽管马勒的乐队编制庞大,但他并不是同时使用所有的乐器,而是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室内乐化的组合,每一种乐器组合都会产生一种独特的音色特性。马勒音乐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质,就是通过处理错综复杂、细腻微妙的音色变化,使得一个扩展的旋律线条的单个动机通过不同乐器组合的变化而相互交织地出现,音色的有规律变化本身成为了一种“旋律”,称为“音色旋律”。
作为传统曲式观念基石之一的“再现”概念也获得了不同的意义。音乐片段确实有再现,但它们通过持续变奏的过程而变形了。马勒发展了一种倾向于持续变奏、倾向于从旧的材料衍生出新的材料的不断发展的创作方法。马勒善于把简单的材料用奇异的方式融合成极其美妙的音乐语言,这些织体不断演进变化,形成篇幅宏大的整体。作曲家本人说:“音乐由不停的演进、不停的发展的原则所控制——正如这个世界,即使在同一地点,总在变化,永远让人耳目一新。”这种不停的音乐流动导致的“稳定性丧失”,极好地体现了马勒音乐对同时代人的革命性影响。
克洛德·德彪西 (Claude Debussy)
法国音乐在二十世纪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其中德彪西(1862-1918)发挥了重大作用。就像半音化的发展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深远意义一样,德彪西对音阶、和声和调性的新的处理方式代表了他对于早期二十世纪音乐最具意义的贡献之一。
德彪西建立调性的方法逐渐摆脱了传统功能体系的制约。他对织体和音色本身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他喜欢用一种更加泛化的对于心情、印象和情景氛围的诗意般的唤起。谈到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时,他说那是“一种对隐藏于大自然中的东西的感性阐释”。在德彪西成熟的第一批作品中显示出对“自然曲线”加以自由装饰的旋律类型,他称之为“阿拉伯风格”的特点(《阿拉伯风》)。 为了创造出更富有色彩的音响,德彪西在音乐中引入古老的中世纪调式,引入遥远的佳美兰音乐,用“外部”观念和技法扩大传统创作资源。德彪西的和声不再作为音乐运动的原动力,而是扮演了一个新的角色:和声成为产生烘托氛围和色彩性音响效果的静态手法——当一个音高中心发生变化时,不代表着传统意义上的转调,而是让音高成为两个不同调式音阶的公共参考点(前奏曲《沉没的教堂》)。他随意地运用各种异国的音节类型纵向组合,使众多音阶融合为一个更大的复合体。德彪西引入了全音阶(把十二平均律分为六等分的音阶),这种音阶在结构上完全对称,因而调性模糊(前奏曲《帆》)。
区别于基于主题或旋律的传统意义上的创作方式,德彪西的音乐通常由短小的动机成分组合而成。这些短小的动机成分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而非出自一个单独的、作为乐曲起始的基本旋律材料。德彪西的作品往往没有一个明确的开始,而是从一个模糊和烘托氛围的背景中逐渐地构成自己的。在体验德彪西音乐时,不能像对待传统西方音乐那样把它当成是向着某个调性目标在运动,我们的注意力不应当集中在音乐从哪来到哪去,而是要关注已经呈现的音乐瞬间的内在特性,这些短小片段本质上往往是静止的和声确定的。德彪西常常使用和弦的平行运动,以致于一个个别的音响只是围绕着旋律的进行连续变化,而一个特殊的和声音响可以控制一个完整的部分甚至整首乐曲。德彪西的调中心不是依赖和声确定的,而是主要依赖于旋律和节奏确定的。通过旋律和节奏的重复,例如连绵不断的持续音或不断重复的短小动机,我们能够被导向一个调性中心。
德彪西音乐的“片段化”和营造色彩氛围的特点,和印象主义绘画中通过大量单个笔触的运用导致表层消解的艺术效果非常类似,因此德彪西常被称为“印象派”作曲家,这是用于区分德国的表现主义的。德彪西的音乐片段之间表面上分离,而又实际上可以看作同一音乐单元的持续细微变奏。这样一个独立而又连续流动的整体很像一种“马赛克”,在表面的连续消解的同时又有着结构完整感。相比于传统音乐,这样的音乐形式更加松散,而更有渗透力——每个部分都能音乐片段的流入和流出。这种把音乐形式当作一种本质上具有“开放”特点的构思,对二十世纪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Sergei Prokofiev)
苏联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拥有着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18岁时他的作品已经被广泛地演奏。他回避浪漫主义的夸大其词与多愁善感,而是选择了之后称为作曲家持续个性化的特性:形式和织体的简练,尖锐的节奏和简洁、严苛犀利的性质(《第一钢琴协奏曲》)。普罗科菲耶夫的性情中一直有一种反浪漫主义和反情感主义的倾向,“古典主义”似乎是他的第二天性。他追求更简单更旋律化的表达,认为奏鸣曲式就可以容纳他所有结构意图的需要(《第一交响曲“古典”》)。他常常使用古典主义的平衡结构,使用朴素的单线条旋律和朴素的三和弦伴奏等形式,却赋予它们非传统的运作方式——和声与节奏的出其不意的变化。这是他对高度传统化风格的惯用手法所开的亲切玩笑(《瞬间幻影》)。
1918年由于政治局势原因,普罗科菲耶夫移居美国,并于1922年移居巴黎。与西方的接触对他的风格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使得他的音乐呈现出更不协和与更复杂的特点(《第三钢琴协奏曲》《第二交响曲》)。1936年他再次回到苏联定居,但面对政府施压,他必须创作旋律清晰简洁、面向大众的作品(《基日中尉》)。他也并没有完全放弃他的音乐良心,因此他晚期的作品都走在官方接受和自己艺术倾向意愿之间危险的狭窄路线上。这些音乐包含了一种更为开放、随和的抒情主义,一种新的表现热情(《罗密欧与朱丽叶》)。他本身就是一位具有强烈传统倾向性的作曲家,因此这种转变与其说是对早年风格的否定,不如说是他以自身方式所作的重新调整。
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Sergei Rachmaninoff)
与同时代的其它作曲家不同,拉赫玛尼诺夫(1873-1943)是一位几乎完全与旧的传统相联系的作曲家,并试图将诸如柴科夫斯基这些前辈们的那样一种浪漫主义创作推向一个新的时代。拉赫玛尼诺夫从未放弃十九世纪音乐的调性和曲式传统,并因此在其一生中都与二十世纪音乐发展主流之间保持着的一定距离。
《第二钢琴协奏曲》(1901)和《第三钢琴协奏曲》(1909)是拉赫玛尼诺夫最为著名的作品,两者都显示了这位作曲家风格上的本质特征。织体始终是主调的,旋律线条通常用循环的结构,节奏的规律性通过大的高潮幅度和温暖的表情而获得缓解。从和声上看,音响丰富但仅仅是温和半音化的音乐,稳固地建立在传统的根音进行之上。曲式结构非常清楚:充满感情的主题部分与常常用模进写成的连接和展开段落相互交替。拉赫玛尼诺夫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他音乐生活的大部分,都被他那辉煌的键盘写作所占据了。但尽管有这种技术上的辉煌,一种忧伤和悲情的氛围却渗透在这些协奏曲中,这也许反映了这位作曲家对于失去一种旧的和更加稳定的生活方式的惋惜之情。
1917年俄国革命后,拉赫玛尼诺夫选择了流亡的生活方式。1918年定居美国,随后他的创作很少,但继续过着一种活跃的演奏生活。只有一首在美国期间创作的作品获得了公众的欢迎:《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Op.43。拉赫玛尼诺夫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五年中相对消极的创作活动是由于他的流亡生活所导致的文化孤立感。同时,作曲家自己的音乐倾向和当时盛行的音乐发展趋势之间相互沟通的完全缺失,他曾说他认为他“所愿意写的音乐类型在今天已不再被人们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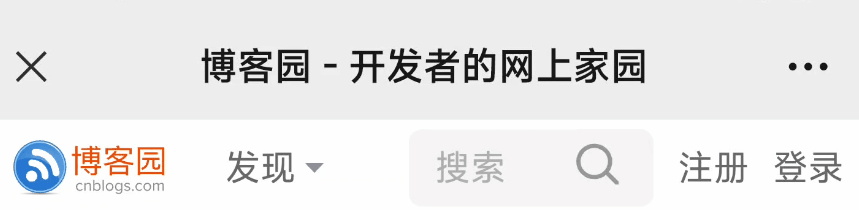
· 分享一个免费、快速、无限量使用的满血 DeepSeek R1 模型,支持深度思考和联网搜索!
· 使用C#创建一个MCP客户端
· ollama系列1:轻松3步本地部署deepseek,普通电脑可用
· 基于 Docker 搭建 FRP 内网穿透开源项目(很简单哒)
· 按钮权限的设计及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