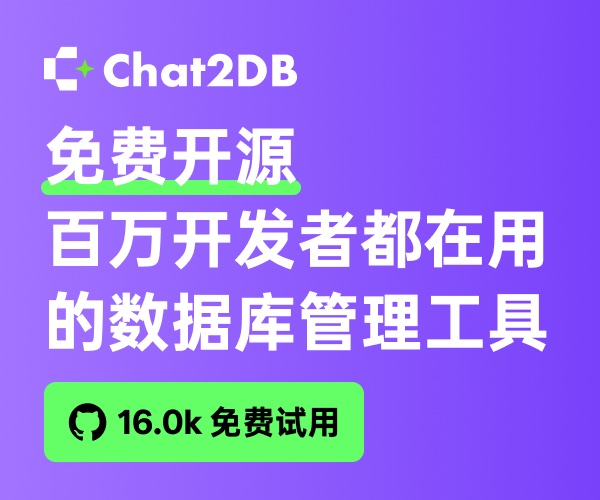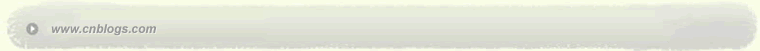一个名叫“辛西娅”(synthia)的人造生命体在美国私立科研机构克雷格·文特尔研究所诞生——上周末传出的这一消息立刻引起全球各方高度关注,并再次引发伦理争议。
有人认为文特尔夸大了人造生命的重要性,但更多科学家倾向于相信合成微生物的应用潜力。中科院生化与细胞研究所研究员郭礼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本质上讲,合成生物学技术与人们熟知的基因工程是一码事,只不过之前更多的是改造一个或两三个基因,而此次是对整个基因组的彻底再造。他强调,“尽管人造生命并非一次划时代的技术突破,却丝毫不妨碍它成为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
实际上,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基因工程技术也曾遭遇生物安全方面的强烈质疑。郭礼和说:“在新技术面前,总有人杞人忧天,相信时间可以最终洗去人们的忧虑。”
为生命“舞台”彻底更换“剧本”
关于“辛西娅”的身世,公众的理解尚有些模糊。按照已有报道的说法,研究人员先是人工合成了一种名为蕈状支原体的细菌的DNA,然后将其植入另一个被掏空的山羊支原体细菌体内。简单地说,就是“移花接木”。至于“花”怎么来,“种花”的过程有多难,则少有描述,而这恰恰是人造生命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生命是一个舞台,那么携带大量遗传密码的基因组就是舞台上演出的剧本,此次美国科学家所做的,是为一种已知细菌彻底更换‘剧本’。”郭礼和说,为生命“重写剧本”不仅工作量大,更需要非凡的创造力。作为“编剧”的科学家,一方面要确保故事的完整性,即生命程序的完整表达;又要设计出众多个性化“演员”,即一个个功能各异的基因,它们有“表情”、有“道白”,知道何时“出场”、何时“退场”。“从理论上说,现有技术已经能够做得到,但要情节合理、环环相扣,难度不小。”
所幸的是,随着多种生命体基因组的破译和生物信息学的发展,“编剧”的过程完全可以在电脑上进行。科学家根据构思,先在计算机上利用A、T、G、C四个字母(构成碱基的基本单位)的不同排列,画出一张基因图谱,然后在实验室中合成出一个个基因片段,最后按事先设计的图纸对基因片段进行适当“剪裁”、“拼接”,一个人造基因组就这样诞生了。
郭礼和告诉记者,人造基因组有三种合成方式:一是完全通过化学合成,二是用天然基因片段“粘贴”而成,三是对已有基因组进行改造。此次,文特尔领导的研究小组先是用“四瓶化学物质”(两种嘌呤和两种嘧啶)重塑了蕈状支原体的基因片段,并将新的基因片段“粘”在一起,植入另一种细菌中。按照他本人的说法,“这是地球上第一个以电脑为父母、可进行自我复制的物种”。
第一笔研究经费来自美国能源部
了解文特尔的人在获悉人造生命诞生的消息后,普遍感觉“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毕竟,这位爱出风头的“科学怪才”向来喜欢特立独行,被同行称为生物学界的“坏小子”。上世纪90年代末,由他创立的塞莱拉基因公司曾公然挑战由六国科学家参与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并发起了一场基因竞赛。
郭礼和认为,人造生命的诞生与文特尔参与人类基因组草图绘制的经历密切相关,因为“要合成基因组,必须先要了解基因组,而他就是在那时打下了基础”。有意思的是,当年由文特尔发明的“鸟枪测序法”先将庞大的基因组打碎成一个个小片段后再进行测序,最后用超级计算机对其排序和拼接,大大提高了“绘图”效率,而此次的设计、合成有异曲同工之妙。
2000年后,文特尔转向了合成生物学研究,希冀从海洋生物中汲取灵感,创造出能缓解能源危机的微藻或细菌。为此,美国能源部向文特尔创立的私人研究机构提供了第一笔4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郭礼和说,此次被制造的虽是最小、最简单的原核生物,可它实现了新陈代谢和遗传分裂两种生命的基本功能,走通这一步相当不容易;下一步,科学家可以为这一基本生命体附加新的功能,比如将纤维素降解成葡萄糖,从海水中分解出氢气,甚至吃掉墨西哥湾的油污。
想“扮演上帝”不那么容易
只要“人造”与“生命”这两个词组合,总会夺人眼球,同时引来“扮演上帝”或是“亵渎生命”的骂名。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学部主任沈铭贤指出,人们有关“人造人”的遐想,在很大程度上也许是受了科幻电影的影响,其实沿着文特尔的技术路线,科学家若想真正扮演上帝,不那么容易。“相对来说,胚胎干细胞技术距离‘人造人’要近得多。”
郭礼和告诉记者,最原始的单细胞生物与最复杂的生命形式——人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前者的基因组只包含108个碱基对,而后者拥有30亿个碱基对,体外合成的工作量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人类基因图谱上的2万多个基因所组成的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三维甚至四维结构,不仅涉及前后排列的顺序,还包含更多的空间信息,而单细胞生物则是简单的环状结构,做起来容易得多。
就目前看来,科学伦理界人士对于人造生命的质疑,更多地是针对技术所具有的“两面性”,比如有人担心“辛西娅”开启了“潘多拉的魔盒”,为未来制造生化武器奠定了基础。对此,沈铭贤表示,与任何一项新技术一样,人造生命技术必须规范,但无法禁止。他认为,“我们需要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作社会管治,而非管制。在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框架下,凭借政府监管、科学家自律和公众参与三股力量,完全有能力避免‘邪恶细菌’或‘超级生命’的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