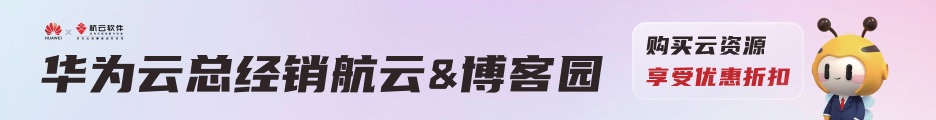文 | 小故事
他一眼便在烟雾缭绕中认出自己,不会有错的——那从不被别人知晓的、独属于自己的微弱特征,像遥远的绿色灯塔在闪光——即使是在油墨绘出的干瘪的报纸上。当他循着标题翻入内页,正文下方偌大的照片赫然映在眼前,而四周一切绞在一起,旋转起来。
恢复知觉后,回忆占领上风。那是他发誓的最后一次赌博,最后一次了,用完当月微薄的薪水。那毅然决然一去不复返的气概赋予这本卑劣的娱乐以崇高,像那些献出生命的人最后找的精神支柱。他要与过去的自己一刀两断了,捏紧那软软糯糯的钱,循着熟悉的潮湿的通道,踏上征途。
“看报纸看过去了?”回忆被冲散,说不明的感受蔓延开来,他察觉到妻子在他身后忙碌。“今天啥头条啊?”她顺着他视线看过去。“哟,赌场被封了?还是我们这的?你瞧瞧,一个个蛆虫被捉出来了。”他不知道妻子口中的“蛆虫”指的是赌场,还是包括他在内的赌客,只是突然莫名其妙恼怒起来。可当他感觉到妻子注视照片时,瞬间冷汗直流。他嗖一下合上报纸。
“哎你合这么快干嘛?照片还没看清呢!” 一声不吭,他带着报纸出门,妻子不满的抱怨远远传来。
楼下茶馆人人都在议论这件事,从小二到摇扇的老头,似乎人人对赌场的存在了如指掌。他先前还以为这是只属于几个人的秘密。“你知道那赌场为啥被封吗?抽老千啦。全国那么多,为啥只办了我们这的,肯定是赌场内部矛盾啦。”老头说得头头是道,听客越喝越觉茶香,小二桌子越擦越亮。他听着听着就只听见自己的耳鸣了。“还放了张照片,一看呐,就知道不是记者拍的,偷拍哪能拍得这么明目张胆,你看,这一个个的看得清清楚楚。”不知是扇子风抑或其他,他仿佛挨了一巴掌,耳鸣持续着,像是深夜的蝉。
一世英名。那些想了很久很久的计划。猫啊,狗啊。妻子年轻时的美丽——一如既往的去了。
他在路上游荡许久,直到傍晚摇扇老头也离开,直到真的听见了哪棵树上的蝉鸣。
回到家,妻子已睡,一张绿色便利贴一如往常粘在桌上。他心惊肉跳走过去。
“饭菜在冰箱里,热着吃。”
第二天他坐在椅子上端着报纸,头条是一名党员被开除党籍。妻子在身后忙碌,好像哼着小曲,油条烧卖飘着清香。
他想去听听那老头对这件事是什么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