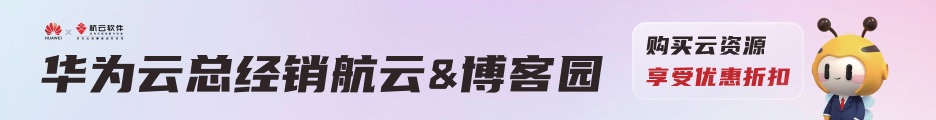《The Gadfly》
突然之间,在阳光烂漫的十七岁,你遭遇到朋友的背叛,深受的女人的误会,并得知自己是一个世人唾弃的私生子。原本打算自杀的你,却突然想到,”抖掉这些毒虫,重新开始生活“。
独自出走到南美后,为了活下去,你抛弃了自己信仰的上帝,放下引以为傲的自尊,“曾经在肮脏的妓院洗过盘子;曾替比他们的畜生还要凶狠的农场主当过马童;曾在走江湖的杂耍班子里当过小丑,戴着帽子,挂着铃铛;曾在斗牛场里为斗牛士们干着干那;曾屈从于任何愿意凌辱我的混蛋;曾忍饥挨饿,被人吐过唾沫,被人踩在脚下;曾乞讨发霉的残羹剩饭,但却遭人拒绝,因为狗要吃在前头”。
三十岁的时候,你冷静睿智,投身将奥地利人赶出意大利的革命。但同时,你也无法抑制的暴躁,对自己生身父亲有着难以言喻的眷恋和仇恨。曾经的初恋情人,此时的波拉夫人,已认不出当年的亚瑟-手虽然如当年一样灵敏好动,但却落下了残疾,眼睛虽然是蓝色,但脸上也留下了一道长长的伤疤。岁月的伤痛和生活的艰辛只留下了一张满是沧桑的脸。
在革命行动中暴露被捕后,经历过两个星期旧病复发生不如死的病痛后,你又见到了自己的父亲-此时的红衣大主教,那个信仰上帝的人。“这个虚伪的受难者,他在十字架上被钉了六个小时,真的,然后就死里复生!padre,我在十字架上被钉了五年,我也是死里复生”。你指责他所信仰的那个加利利人。其实我知道,这一刻你只是十七岁那年的亚瑟。虽然“他曾经用一个谎言欺骗了你”,陷你于万劫不复的痛苦深渊。
后来,听着窗外有人铲掘坟墓的声音。你整夜都躲在黑暗中哭泣。那个加利利人占了上风。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如果一个人必须承担一件事情,他就必须尽量承担。如果他被压垮了下去——那他就是活该”。我知道,那些曾在空荡荡的黑暗之中把你压垮的幽灵般的恐怖,那个阴影世界的幻想和恶梦,只会在此时的黑暗中存在。一旦太阳升起,你就会继续战斗,无所畏惧。
这是你写给自己初恋情人的绝笔信,也是十几年之后你们的第一次相认:
“亲爱的吉姆:
明天日出的时候,我就会被枪决。我答应过要把一切告诉你,所以如果我要遵守我的诺言,我必须现在就动手。但是,话又说回来,你我之间没有多少解释的必要。我们总是相互理解对方,不用太多的语言,甚至在我们还是孩童的时候就是这样。
所以,你瞧,我亲爱的,你不用为了一记耳光这样的旧事而伤心欲绝。当然打得很重,但是我也承受了许多别的打击,我还是挺过来了,我还在这儿,就像我们曾经读过的那本幼儿读物中的那条鲤鱼一样,“活得又蹦又跳,嗬!”
我们将会感谢诸神,至少他们已经给我们这么多的慈悲。虽然并不太多,但是还算是有点。为了这个以及所有其他的恩惠,我们衷心表示感谢。
关于明天早晨的事,我想让你我马尔蒂尼清楚的明白,我非常快乐,非常知足,再也不能奢求命运作出更好的安排。告诉马尔蒂尼,说我捎话给他,他是一个好人,一位好同志。他会明白的。你瞧,亲爱的,我就知道那些不可自拔的人们替我们做了一件好事,替他们自己做了一件坏事。他们这么快就重新动用审讯和处决的手段,我就知道如果你们这些留下的人团结起来,给他们予猛烈的反击,你们将会见到宏业之实现。至于我嘛,我将走进院子,怀着轻松的心情,就像是一个放假回家的学童。我已经完成了我这一份工作,死刑就是我已经彻底完成了这份工作的证明。他们杀了我,因为他们害怕我,我心何求?
可是我心里还有一个愿望,一个行将死去的人有权憧憬他的一个幻想,我的幻想就是你应该明白我为什么对你总是那么粗暴,为何久久忘却不掉旧日的仇恨。你当然明白是为什么,我告诉你只是因为我乐意写信给你。
在你还是一个难看的小姑娘时,琼玛,我就爱你。那时你穿着方格花布连衣裙,系着一块皱巴巴的围脖,扎着一根辫子拖在身后。我仍旧爱你。你还记得那天我亲吻你的手吗?当时你可怜兮兮地求我“再也不要这样做”。
我知道那是恶作剧,但是你必须原谅这种举动。现在我又吻了这张写有你名字的信纸。所以我吻了你两次,两次都没有得到你的同意。
就这样吧,再见,我亲爱的。”
曾经也有那么一个美丽的姑娘,和我出生在同一个山村,上着同一所小学。常常见她穿着天蓝色的外套,扎着和琼玛同样不羁的马尾,早晨上课的时候总是睡眼惺忪地迟到。许多年以后我对你说,那个时候我就爱着你呢。之后四年最宝贵的青春,成都和乌鲁木齐之间,多少3000多公里的来回,我牵着你走过最美好的时光,跑过那些轰隆作响的记忆。你我之间的开始,有关命运,而如今的你我,与命运无关。你不是琼玛,我也不是牛虻。我们都败给了黑暗,输给了时间。
时光就这样走下去,平静而残忍。有一天我们睁开眼睛,模糊的目光再次显露出来,打量四周,却发现自己孑然一身。
晚安,亚瑟。晚安,费利安.里瓦雷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