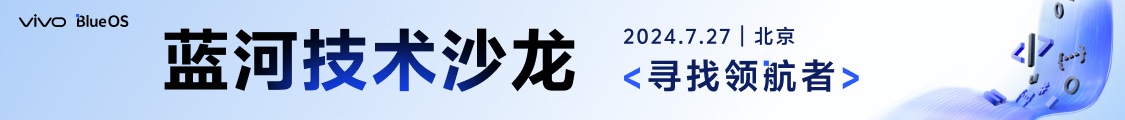[转载]长篇连载:《三国演义》的“性之病”(之四)
长篇连载:《三国演义》的“性之病”(之四)
七 权谋与伪善的二重奏
〇 诸葛亮不出山,呆在隆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吗?
证据是“三顾茅庐”。
三顾茅庐确有其事吗?有,不过具体过程史无记载。《三国演义》作为小说,当然可以虚构。但把诸葛亮说成不想出山,恐怕就很荒唐。众所周知,诸葛亮是以“贤相”(管仲)和“名将”(乐毅)自许的。他怎么会不出山,又怎么会不想出山?他不出山,呆在隆中干什么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吗?
显然,这里有一个价值观和道德观的问题。也许,在某些人看来,想出山,就是想当官;而想当官,是可耻的。这可真是“陋儒之见”!第一,出山不等于做官。在刘备帐下,以朋友身份帮帮忙,不可以吗?实际上,诸葛亮出山之后,并无职务。他的“军师中郎将”一职,是赤壁之战后才担任的。第二,当官也未必就可耻,要看你为什么。如果是为了做事,何耻之有呢?第三,在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时代,一个有能力平治天下的人,是出山可耻呢,还是不出山可耻?至少在刘备看来,是后者。据《三国志·陈登传》,刘备在荆州时,曾经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因为此人“有国士之名,无国士之实”,只知道“求田问舍”,竟毫无“救世之意”。试想,如果诸葛亮也是个这样的,刘备会欣赏他吗?
所以,陋儒之见,万不可信!相反,在我看来,诸葛亮出山,正说明他心系天下,忧国忧民,挺身而出,勇于担当,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听听《毕业歌》吧: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诸葛亮,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吗?
更混账的是,徐庶明明早就推荐了诸葛亮,诸葛出山以后自己才走,为什么要改成临走之前才说?就算“此人不可屈致”,总不至于推荐不得吧?莫非怕他抢了地位和风头?这就是“陷徐庶于不义”了。还有,明明是诸葛亮“每尝自比管仲、乐毅”,却说徐庶把自己当替罪羊、牺牲品,还要勃然变色。真正的诸葛亮,会这么虚伪吗?
其实,这不是罗贯中一个人的虚伪,是旧时代读书人的集体虚伪。这些人的心理,是又想当官,又要摆谱。因此,他们说的话也好,写的书也好,永远都是酸不溜秋的。他们永远都在做一个梦:自己端个架子在家里坐着,皇帝来请,还请三回。请出来之后,言听计从,恩宠有加;自己则光宗耀祖,大展宏图。这是许多人心里的“黄粱梦”。
这才有了“三顾茅庐”的故事。故事很精彩,罗贯中也说得天衣无缝。但明眼人还是不难看出:刘备在隆中的那些奇遇和巧遇,其实都是“罗贯中笔下之诸葛亮”的刻意安排。什么会唱歌的农民,不懂事的童子,满腹经纶的朋友,道貌岸然的丈人,也都是他的“托儿”。其目的,就是要把买方市场变成卖方市场,让刘备出大价钱把自己买断。这,难道不是“权谋”?看不出这一点,只能说明脑残。
诸如此类伪善加权谋的地方还有许多。比方说,小孩都知道,刘备摔孩子,是“邀买人心”。甚至就连他那个“携民渡江”,真实意图如何,都很可疑。朱苏进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说:“我不承认哪个帝王是忠厚的”,这话我同意!
似乎不必再说什么了!诸葛亮和关羽,是《三国演义》刻意塑造的“正面形象”和“英雄人物”,尚且如此,其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八 可疑的旗帜,有毒的药丸
〇 权谋是因为伪善,伪善是因为忠义。被高举的“道德旗帜”,其实是罪魁祸首。
这就是被罗贯中(也许还要加上毛纶、毛宗岗父子)“整容变性”后的“三国”。显然,它的问题不在“容”(与历史的真实相距多远),而在“性”(主题、思想、倾向性)。或者说,不是“容之丑”,而是“性之病”。“性”的问题,也不在“尊刘贬曹”,而在背后的一整套价值观和道德观。因此,尽管《三国演义》主题既鲜明,人物亦鲜活;罗贯中和毛氏父子,也动机既纯正,手法亦高超;但还是不可避免地要走了“麦城”,甚至走向自己反面:代表 明君梦的刘备“长厚而似伪”,代表清官梦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上引均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代表侠客梦的关羽,则既投降了敌人,又放走了敌人。
显然,这是一个悖谬;而问题,就出在他们要弘扬的“忠义”。
忠义旗帜的高扬,有根本原因,也有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在经济基础,直接原因在人际关系。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什么?不是契约关系,而是依附关系。臣依附于君,子依附于父,妻依附于夫。这种关系是不可解除的。就算解除,那也是被依附者的事。比如夫妻离异,就不能叫“离婚”,只能叫“休妻”。
这就要讲“忠”,即臣忠于君,子忠于父,妻忠于夫。显然,这是一种“不平等关系”。臣子必须忠于君父,君父就不必。君父的义务,是仁慈。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表面上看,似乎都有道德义务。但这只能叫“对等”,不能叫“平等”,因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处于主导甚至主宰地位的,仍然是君、父、夫。
不过,能对等,也不错。因为倘若你“不仁”,我就可以“不义”。义,才是普遍适用的。君要讲“仁义”,臣要讲“忠义”,朋友要讲“情义”,买卖要讲“信义”。看起来皆大欢喜,实际上五花八门。究竟什么是“义”,谁都没有解释,谁都说不清楚,只能根据一个模糊的理解,相机行事。正因为可以灵活处理,所以,关羽的依曹、反曹、降曹、别曹、放曹,便都是“义”。当然,这也就是关羽。换成吕布,就是“不义”。
总之,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忠是不变的,义是多变的。这就不好操作。结果,要么各行其是,要么弄虚作假。因为政治斗争,归根结底是利益之争。争利而言义,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这就是“伪善”。比如“当面叫哥哥,背后摸家伙”,或者口口声声为国为民,处心积虑争权夺利。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就是“权谋”。不搞权谋也不行。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都要指责对方“不义”。这就只能搞阴谋,不能搞阳谋。总之,权谋是因为伪善,伪善是因为忠义。被高高举起的那面“道德的旗帜”,其实是罪魁祸首。
这就是《三国演义》留给我们的遗产:一面可疑的旗帜(忠义),两颗有毒的药丸(伪善与权谋)。这样的药丸,当然不能再吃,哪怕裹着糖衣。这样的旗帜,似也不宜再举,即便绣着龙纹。但拿掉这面旗帜,也就不是《三国演义》。更何况,如果连这“亦真亦幻”的道德感都删掉,那可真是“多谋寡义”了。
不能没有忠义,又不能宣扬忠义。《三国演义》之不可改编,还用再说吗?
(全文完)
刊载于2010年7月22日《南方周末》第23版,责任编辑刘小磊,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