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烟缭绕的岁末
已是岁末年尾,母亲又在吵着把父亲送回老家了。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并不算我的老家,而是我的姥姥的老宅。去年,我们村子已被拆迁,而安置房未开始动土,所以四邻八舍投亲访故地分散到了周围的几个邻近村庄。而姥姥家就在隔壁村,父母并不想跟着我来县城,并顺理成章地搬到姥姥家,而姥姥与姥爷两人则搬到了舅舅家的住宅楼上。相距五里地的样子,因为不远,所以母亲隔三差五地总会去看望一下二老,带上她蒸的馒头,捎些平日里的一些吃食。
腊月二十之后,我们这里有个不成文的习俗,嫁出去的女儿就不能回娘家了,说是会坏了娘家人来年的好运。所以,我也就将他们接到了县城,来跟我一起过年。今天姥姥要回老宅去上钱粮,发天地(我们这边的叫法,就是烧些纸钱,摆上供品,请家里的神仙都来享用),母亲让我昨天下午就送父亲回去,收拾一下家里,烧起煤炉,做些酒菜,我却坚持着今天早晨一大早我陪着开车回去即可,40分钟的车程,我也想帮些忙。母亲少有的有些不高兴,跟我说着姥姥着急,早晨7点来钟就会过去,我和父亲需要六点就起来赶路,我满口答应着。
今天早晨4点来钟,母亲接到了姥姥的电话,说是水饺已经包好了。接着我跟父亲便被急急火火地叫了起来。这次轮到我有意见了,大冬天的早晨,4点天空还是黑乎乎的,这些事情似乎并不需要如此的急迫。母亲却是一直在碎碎念道着,我就知道你姥姥会着急,你应该昨天送你爷(山东称呼父母叫爷娘)回去的。我听在耳朵里有些烦躁,拒绝了母亲吃完面再回去的提议,开车载着父亲便走了。好像自从不再读书之后,早晨摸黑赶路的经历便屈指可数了。
回到老宅时,天也未放亮,借着手机的光开了门,父亲便开始忙活着生炉火做饭。我无事可做,便钻到了炕上,睡个回笼觉。朦胧中,听到有人敲院门,父亲去开门,却是姥姥姥爷两个人到了。八十多岁的人了,摸黑骑着自行车赶了过来。姥姥身体远不如以前硬朗,耳朵背得厉害,平时里上个一楼的台阶都是需要紧紧扶着楼梯的扶手,很难想象,他们两个人在这寒冷而漆黑的早晨,慢慢骑着车走在路上,是怎样一种感受。
这些年日子过得好了,家里的神仙所受的香火也一再升级。姥姥到家之后,开始细细地分摊,这一堆元宝是哪个神仙的,那一叠纸钱又是哪个老君的。看在我的眼中,却仿佛是包工头在给神仙们发放一年的工钱,我也在旁边帮忙计算,有的时候弄混了,还要重新来过。姥爷与父亲在院子里放好桌子,摆上酒菜供口。姥姥来到院子里,手里拿一根棍子,在泥土地上画出一个圈,开始了她今年最后一件最庄重的仪式。也只有在今天,平日里脾气并不太好的姥爷却出奇地听话,叫干啥就干啥,而我如果有啥意见,也会被丢来的一句"听你姥姥的"而镇压。
冬早的寒气随着纸钱红红的火苗而在身边退去,我跪在姥姥的身边,抬眼便可以看到姥姥日渐稀疏的白发与愈显虔诚而苍老的脸。火越来越旺,姥姥嘴里念叨的话我也听着比较清晰了:XXXX神仙,请来吃喝了。你听我好好说,来年还请继续保佑我家大公子,二公子(我大舅二舅,我也很惊奇姥姥从哪里学来的这个文绉绉词语)工作顺利,保佑大闰女二闰女家都健健康康的,日子越过越好,保佑我外甥做买卖发大财。泰山老母,你得继续当好孩子们的神仙干娘,保佑你的干儿子来年健健康康的。。。。话还在一句句地喃喃地重复着,直到火苗渐渐地小了下去,这场与神仙的沟通会便在我们四人郑重地三叩首后结束了。姥姥又变回了那个颤颤巍巍的老太太,不再执著,似乎今天这一场钱粮法会消耗了她太多的精力。也许,她的执念本来就是为儿孙们乞求来更多的福与寿,而在所有的话语中,没有哪一句是单独提及他们自己的。
对于鬼神,我的理念更倾向于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中国人的信仰,是比较务实的,每一个神仙,都是一种愿望的化身,或司钱财,或掌姻缘,或管灾祸。而我们敬鬼神,却是不求来世报的,我们总是在向神仙求一个明天,明年。而鬼神更多地也是承载了我们的最后一点顾虑,让我们可以心无旁骛地奋力搏一个更好地未来,毕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再不成功,神仙也会背锅的。我们还会上坟,还会继续祭拜先人,这是我们的来处,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无关科技与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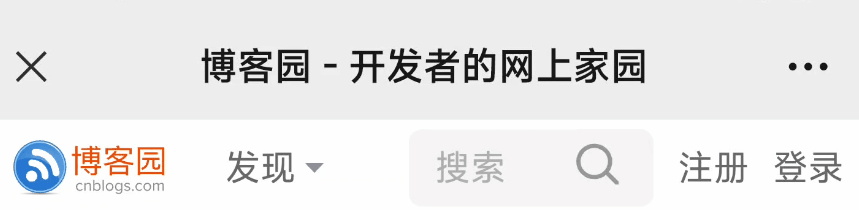
【推荐】国内首个AI IDE,深度理解中文开发场景,立即下载体验Trae
【推荐】编程新体验,更懂你的AI,立即体验豆包MarsCode编程助手
【推荐】抖音旗下AI助手豆包,你的智能百科全书,全免费不限次数
【推荐】轻量又高性能的 SSH 工具 IShell:AI 加持,快人一步
· go语言实现终端里的倒计时
· 如何编写易于单元测试的代码
· 10年+ .NET Coder 心语,封装的思维:从隐藏、稳定开始理解其本质意义
· .NET Core 中如何实现缓存的预热?
· 从 HTTP 原因短语缺失研究 HTTP/2 和 HTTP/3 的设计差异
· 分享一个免费、快速、无限量使用的满血 DeepSeek R1 模型,支持深度思考和联网搜索!
· 基于 Docker 搭建 FRP 内网穿透开源项目(很简单哒)
· ollama系列01:轻松3步本地部署deepseek,普通电脑可用
· 按钮权限的设计及实现
· 25岁的心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