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尔年科:最后的布尔什维克0
标题:CHERNENKO The Last Bolshevik
副标题:The Soviet Union on the Eve of Perestroika
作者:Ilya Zemtsov
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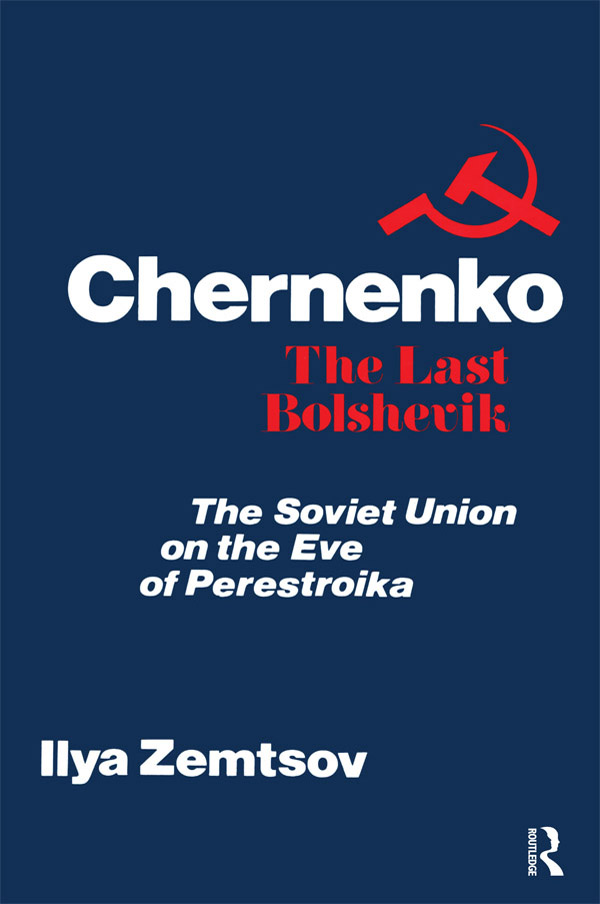
目录
PrefacePrologue: In Retrospect
1. Rising over the Abyss 从深渊升起
2. In Moscow: “Ever Ready” 在莫斯科“时刻准备着”
3. Lessons of Political Maneuvering 政治操纵的教训
4. The Party Boss 党首
5. The Struggle for Succession 为成功而挣扎
6. Leader for the Meanwhile 影子领袖
7. The Brezhnev Era Replayed 勃列日列夫时代的重现
8. The Future Can Be Known from the Past 以史为鉴
Bibliography 传记
Glossary 词汇表
Annotated Index 加注索引

前言
历史的怪癖和反复无常常常令人惊讶。他们经常把平庸的人变成著名的政治家,或者相反,把杰出的、有独创性的人物变成不应该被遗忘的人。
机遇和环境共同塑造了契尔年科平庸甚至可怜的形象。事实上,这个形象只是一个伪装,使他能够在不被注意的情况下爬上权力的陡峭斜坡,到达苏联金字塔的顶端。他的执政时间很短,仅仅一年多一点。然而,如果不了解他的人格特质和他的职业生涯,现代苏联历史将是不完整的,他的继任者戈尔巴乔夫敦促苏联进行的政治变革的性质也将难以理解。
要消除围绕契尔年科这个人形成的半真半假和误解,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陈词滥调和肤浅通常是真理的绊脚石。我必须承认,在试图纠正这些错误时,我经常依靠非公开的证据。首先,我所依赖的是我自己对这个人的印象,这些印象来自我与他的几次会面。第二,我充分利用了道听途说,以及认识契尔年科并与他共事过的人的回忆和印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只是重复我从这些来源得到的信息,一点也不。我很清楚,我听到的很多关于契尔年科的事情不可能都是真的,我把它当作间接推论的起点,而不是可以直接依赖的证据。在得出这样的推论时,我对苏联历史的熟悉,尤其是对苏联权力精英的亚文化特性的熟悉,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然而,更重要的是我掌握的公开证据:主要是契尔年科自己的作品。我发现契尔年科的政治观点和原则在这些书中比在他的政治生活史中表现得更为充分,这在一开始就不无惊奇。
总的来说,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找一种相当虚假的确定性而固执地坚持证据,而是要从中提取最大限度的知识,即使是假设的性质。为了解释从相对贫乏的证据中提取相对丰富的知识的过程,让我考虑一下任何封闭的机构——无论是监狱、军营、轮船还是寄宿学校——作为情境模型。监狱的制度越严格,违反规定的可能性就越小,这意味着一旦我们知道了规定,我们就可以预测任何一个“囚犯”在任何特定时间的位置和行为。没错,出错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让职业经理人和行政管理人员感到悲哀的是,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规则执行。但是,在一个非常严格的制度下,偏离规则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小,以至于出于实际目的可以忽略它。在封闭的机构中,正是行为的标准化和对冲突的压制为个人行为的预测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微观系统(如封闭的机构)是如此,宏观系统(如极权社会)也是如此。苏联是一片由各种因素造成的千篇一律的土地:灌输、管制、警察的恐怖和由此产生的恐吓、缺乏展示个人主动性的机会,甚至是不可估量的、但非常切实的、无处不在的生活灰暗和无聊情绪。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消除了个人差异,无论是在态度或行为上,在日常安排上,在追求的兴趣上,甚至在人的性格和个性上。唯一的主要区别因素是社会角色的不同:例如,规范苏共高级成员和普通苏联公民行为的禁令和规定是完全不同的。但无论哪种情况,这些规定无论多么不同,都是高度标准化的,涵盖了最细微的细节。
要达到统一的效果,成文法、法规和规章并不是唯一的办法。有许多不成文的规则,其内容和执行方式无需言语,人人都能理解。此外,苏联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文化差距导致了高度的文化统一性。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意义,虽然是心照不宣的,但在全国范围内是普遍存在的。同样地,每一个苏联公民从小就受到持续的、咄咄逼人的、刺耳的灌输。这种灌输的内容可能因政治“启蒙”的不同层次而有所不同,但在每一个层次上,从政治局开始,到西伯利亚广阔的某个被遗弃的村庄结束,它培养出的个人在态度和行为上彼此惊人地相似。
最后,还有警察恐怖的恐吓,即使在苏联历史的不同时期强度不同,也总是存在。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也就是契尔年科政治生涯的早期,警察的恐怖行为达到了可怕的顶峰,这一点对本书不无意义。契尔年科的政治生涯将在第一章中详述。尽管与契尔年科这段生活有关的直接证据最为贫乏,但最可靠的假设是,在那些日子里,契尔年科的行为方式与他政治等级的所有其他人完全相同。
读者可能会惊讶于我对契尔年科的频繁使用,也就是说,我谈论契尔年科的想法、感受、经历、理解、渴望、希望或恐惧。当然,这些话不能被理解为我的读心术,而只是表达了我的一种几乎肯定的看法,即在特定的环境下,契尔年科的精神生活与他的社会地位的其他人很难区分。不用说,我在书中对其他人物的描述,以及契尔年科和他的同僚行为的一些琐碎细节,都是如此,我可能没有直接的证据。
我的方法是基于普遍的统一性知识、它们的因果关系和执行力来重建个体的心理特征或行为,其中有一个方面是奇怪的,甚至是矛盾的。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方法程序是由实质性考虑决定的。如果我的故事发生在其他国家,而不是像苏联那样彻底统一,那么选择这种特殊的程序就不成立了。正是苏联社会各界统一化的经验事实,才可以变成一种启发式的手段,成为一种比较丰富而坚定的知识来源。与丘吉尔相反,无论这个国家的政府保密多么偏执,苏联都远不是“一个包裹在谜团中的谜”。苏共的领导层,一方面用其所有的权力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秘密,不让外国检查,同时,也向好奇的外部研究人员揭示了同样的秘密,因为它迫切希望把苏联的一切都置于自己的控制、监管和可预测之下。一个悖论?也许吧,但这也激励着我们,通过艰苦的工作,进一步深入了解苏联的官方秘密,剥去一层又一层保护这些秘密不被曝光的谎言和伪造。
序言:回顾
权力是一种戏剧性的奇观,取决于舞台布景。
时间抹去记忆。岁月会消逝,情感会消逝,印象会黯然失色,但人们的形象通常会留在一个人的记忆中,拒绝消失。当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一个遥远的过去的相遇的记忆重新出现在一个人的脑海中,这一形象最初可能是苍白的,但突然它可能变得清晰,就好像相遇只是最近发生的一样。
那是1984年2月。在红场鹅卵石上方的寒冷中,灰色的雾笼罩着列宁的陵墓,契尔年科冻得佝偻着,瘦弱无力,有点心不在焉。这位苏联领导人吸着冰冷的空气,吃力地喘着粗气,为安德罗波夫致了悼词。
1982年11月7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最后一次检阅革命周年阅兵式时,也站在这个主席台上。就在几天后,安德罗波夫登上了同样的台阶,悼念已经去世的勃列日涅夫。现在,契尔年科站在陵墓上,站在所有灰色的、一动不动的政治局委员的身旁,冒着严寒。他那张胖胖的、朴素的脸上没有一丝喜悦的表情,下巴很沉。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看起来是一个心烦意乱、精神崩溃、精神崩溃的人。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仿佛耗尽了他一生的野心和对权力的贪婪暂时消退了。他受到安德罗波夫的种种羞辱之后,他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胜利。他虽然没有打败安德罗波夫,却比他活得更久。现在,无论他的统治会带来什么,是长是短,是繁荣还是灾难,他都将作为苏联第六任领导人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然而,契尔年科非但没有感到胜利,反而感到痛苦和悲伤,这不是因为安德罗波夫,他曾经害怕他,现在他只能鄙视他。他可怜自己,承认自己年老体弱。他很害怕,因为他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他会被埋在地下,被一块沉重的大理石板覆盖着。他从麦克风前的那张纸上抬头看了一眼,旁边的同事们穿着相同的深色大衣,戴着鹿皮帽子,仿佛在摆姿势拍照留念,他不禁想知道谁会是致悼词的人。看着电视屏幕上的葬礼,看着切尔年科的手在颤抖,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不同的契尔年科,那个我13年前遇到的契尔年科:威严而自信。
我以前见过契尔年科两次,这足以让我对他有个印象。然而,当我计划第三次见他时,我很担心。在非正式场合见到他是一回事——在伊万·哈利波夫将军的生日宴会上,在费多尔·康斯坦丁诺夫的别墅里呆了几分钟。而按照根纳季·奥西波夫的建议,在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室里与他会面则完全是另一回事。[1]
这时,奥西波夫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突然停了下来,向窗外望去,窗外莫斯科的早晨笼罩在一层银白色的薄雾中,他接着说:“明天上午11点,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将接见您……”他的声音和他那弯曲的瘦小的身躯都流露出紧张的神情。他直起身子,搓搓冻僵的手,接着说:“契尔年科。”他那精致、轮廓分明的嘴唇绽开,露出微笑。
“但记住条件:不许对我只字不提。他必须被说服,社会学太重要了,不能交给哲学家——无论是科瓦尔奇克、鲁特科维奇还是其他任何人。社会学研究所应该由社会学家来领导,我是最合适的人选。”
就这样,命运让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遇到了那个注定要成为苏联国家元首的人。但是,在1971年春天,契尔年科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未来的苏共ZSJ。他似乎不具备当领袖的特质。
那时候我对ZSJ的理解还很不完善。当时我对ZSJ的印象是我对我个人认识的各种GCD领导人的总结,或从别人那里听到的,以及在较小程度上从书面资料中读到的。在这个基础上,我相信一个ZSJ必须是傲慢的,他的决定是武断的,对别人是粗鲁的。这些特点——后来我把它们解释为对ZSJ风格的有意识模仿——我在我见过的几乎每一位地方党委书记身上都观察到了。我能看出他们对陈词滥调和简单公式的依赖,这让我相信,ZSJ代表了我在省委官员中观察到的心胸狭窄和智力贫乏。
契尔年科丝毫没有证实我的这些想法。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正坐在他那把很深的扶手椅上,看上去像是一个集体农庄的会计。他那张红红的、一动不动的脸毫无表情,既没有流露出感情,也没有流露出思想,甚至对他将要谈话的人也没有丝毫兴趣。他说话时,下唇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而没有血色的上唇几乎不动。他那双水汪汪的眼睛没有睫毛,一生气就会变成深蓝色。他整洁的双手静静地放在一张擦得锃亮的桌子上,桌子上没有任何文件、笔记或书籍。切尔年科的穿着完全不像通常的党的风格。虽然他不是个赶时髦的人,但他还是很体面的。他穿了一套朴素的棕色西装,配了一条配套的领带和一件灰色衬衫。这条领带的结又粗又笨,破坏了这种效果。
“请允许我,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我开始说,“以苏联社会学协会主席团的名义向您颁发协会荣誉会员证书。”这句话我排练过很多次,在和党的其他人物见面时也用过。
契尔年科假装没听见,平静地问:“您要喝茶吗?”他的声音里有一点讽刺。他很享受这个打量我的机会。
“谢谢你,乐意之至,”我说,把目光移开,望着那扇盖着衬垫和深色皮革的沉重的门,好让自己恢复镇静,然后我继续说,“党的工作本质上也是社会学的工作。”我停住脚步,望了望契尔年科,希望他能像其他党的干部那样赞同这个方案。契尔年科的反应截然不同。“
但是社会学工作不是党的工作,”他尖锐地说。然后他突然问道:“你是党员吗?”语气流露出他的不快。把学术活动和党的活动等同起来是错误的。一个不能容许的错误!”
契尔年科小心翼翼地(当时我觉得有些不安)从我手中接过我递给他的协会会员证书。他打开那本印着金色浮雕的皮革小册子。“你是想拿你的证书和中央颁发的证书做比较吗?”为什么是红色的?只有党证可以是红色的。你想在党的权威下保护自己吗?”
我感到局促不安。这次谈话毫无进展,同时也没有取得契尔年科支持把社会学研究与党的工作等同起来的希望。人们曾希望契尔年科的支持能使首都的社会学家免于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而中央委员会不久前还捣毁了具体社会研究所。[2]
我绝望地喃喃自语,相当愚蠢地说:“当然,你毫无疑问是对的。”如果他是对的,如果社会学家们真的把他们自己和党等同起来,那么我除了道歉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当然不是为了寻求他对任命奥西波夫为研究所所长的支持。我不应该表达我的同意,而应该委婉地指出他的误解。
为了把谈话转移到一个不那么危险的话题上,也为了避免为自己说话,我说:“我们相信党的工作”(我疯狂地寻找合适的说法)“具有与学术研究非常相似的性质。同样的志向,同样的精神。”
“胡说八道!”契尔年科更生气地喊道。“我们不需要无用的社会学调查。没有他们,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党有一支数目可观的志愿告密者队伍。我们对每个人都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你试图通过扭曲社会现象使之符合你想象的范畴来胜过我们。人们必须以一种政党式的方式面对现实,以区分事实与真实的生活真相。你们这些社会学家一次又一次地忘记了目标,无视理想,诽谤我们的人民。
“但是客观的信息可以帮助党做出正确的决定,”我大胆地说。
“什么?正确的决定!”契尔年科在扶手椅上直起身子,提高嗓门说:“党所需要的唯一信息就是证明它的决定是正确的信息。”
契尔年科是对的:自列宁之后,党的领导人一直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的教育(和文化)缺陷由于缺乏与现实生活的接触而变得更加复杂,因为他们没有接触到巨大的办公室和豪华的政府别墅之外的世界。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顾问和专家提交报告,但他们倾向于选择不比自己强多少的助手。党的干部的这种选拔,保证了对命令的顺从态度和对命令的盲目执行。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因为从较低的行政级别到达当局的信息符合他们想要听到的,而不是他们需要知道的。因此,反馈必然是扭曲的。一方面,传递给较低行政级别的信息充满了虚假;另一方面,向上级报告也不符合现实。于是出现了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局面:人民不知道统治者的心理状态,统治者与民众的关切隔绝了。
我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契尔年科。渐渐地,我找到了让自己高兴起来的理由。我知道有关重大社会问题的决定不是在他的行政结构层面上做出的。
不出所料,奥西波夫紧张不安地听着我的报告。他总结说:“永远不要和党的小官僚说话。他们有主人的自负,却没有主人的力量。”
奥西波夫和我都丝毫没有想到,有一天契尔年科会成为苏联的主人。
[1]1970年,最近成立的隶属于苏联科学院的具体社会研究所(konkretnykh Social 'nykh issledovaniansssr)面临着关闭的威胁。一个检查委员会(由苏共中央委员会某部门负责人尼古拉·皮利潘科担任主席)断言,该研究所的研究缺乏党性。社会学研究对舆论、犯罪原因、工人动机等的某些结论和概括,似乎与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和立场并不完全一致。结果,该研究所的四名成员被捕;他们被指控犯有各种罪行,例如散布谣言诋毁苏联政府和政治制度,以及从事反苏活动。有20名党员受到党的处分或被撤职。研究所所长阿列克谢·鲁缅采夫(Aleksey Rumyantsev)院士和苏联国家社会学协会(SSA)主席根纳迪·奥西波夫(Gennadiy Osipov)教授试图安抚党的官僚机构。在他们的倡议下,安排并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与会者包括有影响力的党的官员,即中央委员会主要部门的负责人、一些共和国和省级党委的第一书记以及国防部和国家安全部的政治官员。参加这些会议的是SSA主席团和执行人员,包括本书的作者。
[2]20世纪70年代,克宾是爱沙尼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领导着新西伯利亚的党组织;分别是克麦罗沃和雅罗斯拉夫尔的埃什托金和罗申科夫。
本文来自博客园,作者:昂纳克,转载请注明原文链接:https://www.cnblogs.com/honecker-ddr/p/17474904.html


 基本信息介绍,前言与序言(机翻+校对)
图片为契尔年科的油画
基本信息介绍,前言与序言(机翻+校对)
图片为契尔年科的油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