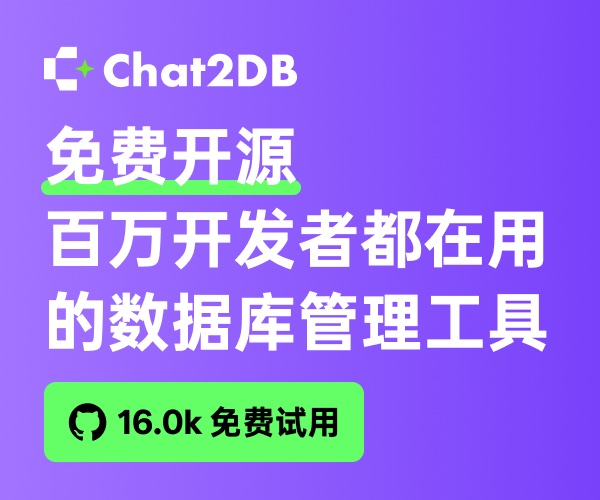html文档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个人博客</title>
<link rel="stylesheet" href="生死场样式.css">
</head>
<body>
<!--左边栏设置-->
<div class="blog-left">
<!--设置头像-->
<div class="blog_tx"><img src="https://ss0.bdstatic.com/70cFuHSh_Q1YnxGkpoWK1HF6hhy/it/u=2729724150,2476510592&fm=26&gp=0.jpg" alt=""></div>
<!--https://timgsa.baidu.com/timg?image&quality=80&size=b9999_10000&sec=1573910977810&di=b720f6369ede5d20d121b486e4867bd6&imgtype=0&src=http%3A%2F%2Fi1.hdslb.com%2Fbfs%2Farchive%2F9ff071d9d35d3c0e2a219b68ec4de42d5b694161.jpg-->
<!--标题1-->
<div>
<p id="title">人和动物一样</p>
</div>
<!--连接标签-->
<div id="info">
<ul>
<li><a href="https://s.weibo.com/weibo?q=%E4%BD%90%E4%BD%90%E6%9C%A8%E5%B8%8C&Refer=SWeibo_box" target="_blank">微博</a></li>
</ul>
<ul>
<li><a href="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6603599/answer/312816479" target="_blank">知乎</a></li>
</ul>
<ul>
<li><a href="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317899/" target="_blank">豆瓣</a></li>
</ul>
</div>
</div>
<!--导航栏设置-->
<!--<div class="blog-top">-->
<!--<a href="" style="margin-right: 110px">新垣结衣</a>-->
<!--<a href="" style="margin-right: 110px">石原里美</a>-->
<!--<a href="" style="margin-right: 110px">佐佐木希</a>-->
<!--<a href="" style="margin-right: 110px">北川景子</a>-->
<!--<a href="" style="margin-right: 110px">长泽雅美</a>-->
<!--<hr>-->
<!--</div>-->
<!--文本阅读层设置-->
<div class="text-page">
<h1 id="over" style="text-align: center">超越阶级的政治的人性之书</h1>
<p id="text">
萧红写《生死场》时才23岁,但已经历了母亡、挚爱的祖父去世、抗婚求学、被软禁、出逃、流浪、与汪恩甲同居怀孕、被遗弃、官司败诉、被扣人质、向报社求救、与萧军相爱、产女送人、出版与萧军的合集《跋涉》、从哈尔滨到青岛——《生死场》的初稿,便创作于1934年在青岛期间。之所以开列她《生死场》之前这些人生传奇,当然是想给一个23岁的女子竟然能写出这么了不起的作品找寻些原因。可是我罗列的这些,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因为不同寻常的经验并不能直接打开通往智慧之路。“那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王安忆探访萧红故居时一直在想这个问题,“那个时代很奇怪,似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受过教育的人,突然睁开眼睛,……人的命运忽然之间就都有一种觉醒,对现实的生活很不满意,就产生了一种‘厌乡症’,直至出走。”王安忆的那个问题,正是我读萧红作品时心里最为挥之不去的,疑问也好,惊奇、惊叹也罢,总之是不解她那些清醒和洞察力、才华和深刻劲儿,从何而来。
</p>
<p>
《生死场》作为她和萧军、叶紫“奴隶社”的“奴隶丛书”之三(“奴隶丛书”的另两部是叶紫的《丰收》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1935年在鲁迅帮助下,假托“荣光书局”之名自费印行。“萧红”,便由这部作品的作者署名而来。“生死场”,是胡风从书中一章节名取定的,本名“麦场”。鲁迅为《生死场》作序,胡风则撰读后记。据许广平《追忆萧红》中说,鲁迅总是向朋友推荐《生死场》,并且认为就写作前途论,萧红比萧军更有希望。
</p>
<p>
《生死场》的帷幕由一头在大道边啃榆树皮的山羊挑起,接下去的一句是:“城外一条长长的大道,被榆树打成荫片。走在大道中,像是走进一个荡动遮天的大伞。”读了,心里就小小一惊:好别致灵动的文字。
</p>
<p>
跛脚农夫二里半和儿子罗圈腿在找羊。二里半的老婆麻脸,人傻,名“麻面婆”。萧红在她身上用了大量的比喻。麻面婆脏水洗脏衣,再脏手抹眼睛,留下脏污的大黑眼圈儿,“若远看一点,那正合乎戏台上的丑角”。抱柴草进屋,“麻面婆是一个母熊了!母熊带着草类进洞。”二里半找不到羊,骂骂咧咧地回家,麻面婆招呼他吃饭,“让麻面婆说话,就像让猪说话一样”。听说羊丢了,去柴堆里翻找,“六月天气,只有和她一样傻的羊才要钻柴堆取暖。”可傻妇并不自知傻,翻得很带劲,最后“像狗在柴堆上耍得疲乏了!”扒拉着头发里的草。又置灶上的饭锅于不顾,尾随丈夫出门找羊。二里半一转身,发现老婆“一捆稻草似的跟在后面。”麻面婆午后再接再厉闷头往高粱地里去找羊,“经过留着根的麦地时,她像微点的爬虫在那里。”
</p>
<p>
发现没?萧红所用以比喻麻面婆的,尽是极贱的。丑角、母熊、猪、羊、狗、稻草。爬虫已经够渺小了,还要加上“微点的”。《生死场》中大量使用比喻,基本如此。一开始,可能会被这种强烈的“轻贱”吓着,可是读下去就明白了。萧红要呈现的正是故乡百姓的卑微、困苦、悲惨和愚昧。写出人类的愚昧,是她认定的作家的责任。1938年4月在由胡风召集的“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文艺座谈会”上,她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创作观:“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 从《生死场》中不难看出,她在文学创作之初,便忠实于自己的创作观。
</p>
<p>
“麻面婆的性情不会抱怨。”萧红往人物内里挖,“她一遇到不快时,或是丈夫骂了她,或是邻人与她拌嘴,就连小孩子们扰烦她时,她都是像一摊蜡消融下来。她的性情不好反抗,不好争斗,她的心像永远贮藏着悲哀似的,她的心永远像一块衰弱的白棉。”这带有强烈批判意味的议论,当然含着作者的观点:只有反抗才有出路。萧红短暂的一生一直在抗争,以逃离、漂泊的方式。她从呼兰到哈尔滨,之后北平、青岛、上海、东京、武汉、西安、重庆、香港,固然有战乱年代迫不得已的颠沛流离,但更有主观意识下一次次清醒的出走,或者说追求。为逃婚、为求学、为自由、为独立、为疗伤、为写作、为温暖和爱……虽然一路伤痕累累,战乱的局势也给不了她一个“安静的写作空间”。可她仍在极有限的创作时间、极动荡艰难的生存条件、极痛苦挣扎的情感纠葛中写下了百万字左右的作品。
在题为《祖父死了的时候》的散文中,她写道:“过去的十年我是和父亲打斗着生活。在这期间我觉得人是残酷的东西。父亲对我是没有好面孔的,对于仆人也是没有好面孔的,他对于祖父也是没有好面孔的。因为仆人是穷人,祖父是老人,我是个小孩子,所以我们这些完全没有保障的人就落到他的手里,后来我看到新娶来的母亲也落到他的手里,他喜欢她的时候,便同她说笑,他恼怒时便骂她,母亲渐渐也怕起父亲来。母亲也不是穷人,也不是老人,也不是孩子,怎么也怕起父亲来呢?我到邻家去看看,邻家的女人也是怕男人。我到舅家去,舅母也是怕舅父。”不得不惊异她女性意识出现之早,她由小女孩的双眼看出去,竟然就看清了男女不平等,看清了男权制下女人所受的压迫;同时,那样小的年龄,就深晓了人世间层层的压迫和不平等。
金枝担心肚里的孩子,恍惚中错摘了没长熟的柿子,妈妈扑上去就是一通厮打。“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什么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这讽刺可真狠!金枝妈妈夜里每翻一回身,就冲金枝骂一句:“该死的!”痰不往地上吐,往金枝脸上吐。“乡村的母亲们对于孩子们永远和敌人一般。当孩子把爹爹的棉帽偷戴起跑出去的时候,妈妈追在后面打骂着夺回来,妈妈们摧残孩子永久疯狂着。”平儿穿了爸爸的靴子,王婆追着强脱下来,平儿只能赤脚在雪地里走回家,冻伤了脚,许久好不了。
月英曾是打鱼村最美丽温和的女人,“生就的一对多情的眼睛,每个人接触她的眼光,好比落到绵绒中那样愉快和温暖。”后来瘫痪,起初丈夫也为她请神、烧香,不见效后,便骂,便打,后来打骂都省了,把她靠在一堆砖头上,被子也夺了,让她一日日淹在自己生了蛆虫的排泄物里等死。“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变绿,整齐的一排前齿也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她像一头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死了,乱坟岗上一埋。
《生死场》中的女人全以血肉之躯出现,她们的血肉之躯被侮辱、被践踏、被撕裂、被损毁、被牺牲。
在《刑罚的日子》的章节里,赤裸呈现的是“妇人们的刑罚”——生育。原来萧红将生育看作上天对女人的刑罚。从《生死场》中女人们的故事看,从生到死,从身体(性和生育)到命运,女人都对自己做不了主。她们的身体是由男人摆布的,怀孕和生育之苦,不仅全由女人承受,甚至在男人眼里,还成了女人的罪过。五姑姑的姐姐快生产了,光着身子爬在土炕上的尘土中挣扎。丈夫醉酒归家,差唤她拿靴子,未应,嘴里骂着“装死”,拿起长烟袋就打了过去。“每年是这样,一看见妻子生产他便反对。”这是何其尖锐的讽刺和批判。产妇一夜苦挣苦扎仍然生不下来,丈夫又进来了,兜头浇下一大盆冷水。“大肚子的女人,仍涨着肚皮,带着满身冷水无言地坐在那里,她几乎一动不敢动,她仿佛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在这里,她将男权制下女人和父权制下的孩子刻意混写,将女性所承受的痛苦揭露个彻底。孩子终于生下来了,死婴。“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这当然是刑罚,如果这还不是刑罚,什么是刑罚?当个体之痛被书写到极致,便带有了最普适的意义。萧红的《生死场》是对整个乡土中国的控诉。
金枝未嫁先有了孩子,“等她确信肚子有了孩子的时候,她的心立刻发呕一般颤索起来,她被恐怖把握着了。”她对自己鼓出的肚子满是厌恶。婚嫁尚未落实,占有她的男人只管对性的索取。金枝一面给他看肚子,一面叫不行。“男人完全不关心,他小声响起:‘管他妈的,活该愿意不愿意,反正是干啦。’”婚后四个月,金枝生产。生产前夜丈夫还在“干”。女儿出生仅几天,就令父亲生了厌,说摔死就摔死了。
读《生死场》,是很需要一点心理承受力的,否则那样苦难深重的画面会刺痛到心肝颤索,不敢直视。
牛和马在交配,萧红称它们“在不知不觉中裁培着自己的痛苦”。她不仅将女人的生育定义为“刑罚”,也将动物的繁衍视作“痛苦”。她有意混淆人与动物的界线,将人与动物的生死并列书写。让人卑微到尘土里去,猪、狗、马、牛里去。“暖和的季节,全村忙着生产。”小狗出生,伴随着麻面婆的生产,母猪也产下了小猪。“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生死场》的笔端,是直接贴伏到地面去的。在文字与现实间,作者不留一丝缝隙,不让幻想、假想、美梦、欺骗有生存的空间。我想,因为那就是她看到的乡土,那就是她熟悉的乡民。她视角的诚实、书写的朴素,正是来自她的悲悯和赤诚,对家国,对故土,对人民。
王婆是刚烈的,丈夫赵三要搞“镰刀会”,密谋铲除恶棍刘二爷,她直接递给丈夫一杆枪,还传授用法。可她的人生一样苦痛。她一嫁二嫁三嫁,讲起三岁的女儿如何跌在铁犁上摔死了,“孩子死,不算一回事” 一个秋天她不哭不嚎,闷头干活,可到了冬天,看到别人的孩子长大了,想起自己死去的女儿来。多年后述说这段往事,却说“要小孩子我会成了个废物。”我一哆嗦,那孩子原来是被她摔死的。围绕着对萧红的非议,除了男女关系,最狠的莫过于说她把跟汪恩甲的女儿送人,而跟萧军白白胖胖的儿子“夭折”得如何蹊跷。“那时我才二十几岁。”王婆跟邻妇讲,我心里又是一凛。虽然在萧红和萧军儿子之迷上,我更倾向于季红真的观点,那就是孩子未必真的像萧红所说抽风死了,而可能是为了彻底了断和萧军的关系,把孩子送了人。但人的心理就是这么怪,有时候哪怕仅是风过,都会留下痕迹。
王婆还是绕不过儿女事,听说儿子被抢毙,她服了毒。丈夫赵三跑去乱坟岗挖好了坑,进城买好了棺材,衣服也给她换好了,可她就是不咽气。男人们一再催促着“抬呀!该抬了。”赵三也像是等得不耐烦了。人们吃饭喝酒,并不恐惧。王婆却突然活动着想要起来,男人们叫着不能让她死尸还魂,赵三一扁担狠砸在她腰间。王婆的肚子和胸膛霎时高鼓,鱼泡似的,双目大睁,嘴角牵动,喷出血来。终于,王婆气息全无了。人们把她放进棺材。全村女人借机放声一哭,因为她们的一生可哭的机会并不多,心里再苦,平白哭起来,是要被骂挨打的,而她们可哭的痛苦又那么多。终于要钉棺材盖子了,王婆要喝水。她活了过来。
小说一共十七章,从第十一章起,转入对日本侵略和东北人民觉醒、反抗的叙述。日本人来了,女人的苦难更加深重,她们却不再怨恨丈夫,而是把所有苦难的帐都算到日本鬼子头上去了。“村中的寡妇多了起来”,金枝也是其一。日本人抓女人,剖孕妇的肚子,女人在乡下呆不住了。金枝勇敢地进了城,却在城里被中国人强奸,被中国人盘剥欺凌。她羞恨地返回乡村,妈妈接过她挣的钱,急催着她返城。无望的金枝决定出家为尼,可是庙庵早已空了。“‘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 最后她转到伤心的路上去。‘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
男人们一下子爱起国来,赵三从前不知道什么叫国家,甚至可能根本不记得自己是哪国的国民,更不明白他在中国人中属于什么阶级。但这不妨碍“他可以代表整个的村人在进步着”。他也闪过这样的念头:“这下子东家也不东家了!有日本子,东家也不好干什么!”萧红对赵三这一丝“快意”的揭露,一下子刨到了国人阴狭的心底。进步的赵三热情地宣传抗日,“他逢人便讲亡国、救国、义勇军、革命军,……这一些出奇的字眼,”他得意地告诉儿子,听了他的宣传,寡妇怎样送儿子去投义勇军;小伙子们又怎样准备集合。“老头子好像已在衙门里作了官员一样,摇摇摆摆着他讲话时的姿式,摇摇摆摆着他自己的心情,他整个的灵魂在阔步!”
乡民分不清各支抗日队伍,弄不明白这军那军怎么回事;这军那军也说不明白他们的队伍是怎样的队伍,王婆寻问她女儿是不是在队伍里死了,如何死的?一堆空言虚语连唬带吓:”老太太你怎么还不明白?不是老早就对你讲么?死了就死了吧!革命就不怕死,那是露脸的死啊……比当日本狗的奴隶活着强得多哪!“萧红说那说话人,“弄得骗术一般”。
反正一切都变了样了,日子不像日子,节更没法像节。有队伍经过,“人们有的跟着去了!他们不知道怎样爱国,爱国又有什么用处,只是他们没有饭吃啊!”
村民们要搞个宣誓仪式,无鸡可献祭,抬来了二里半的老山羊。二里半在羊快被杀时,找来了一只公鸡替下他的羊。“对于亡国,他似乎没什么伤心,他领着山羊,就回家去。”小说最后,二里半的老婆孩子死了,这个曾经被老赵三骂做“老跛脚的物”,也追着去抗日了。
如果将《生死场》的叙述切分为苦难和反抗,前者的分量远远超过后者。可这,不正是这部作品最为了不起的地方吗?她超越了阶级、政治,甚至超越了国家。她是一部关于人类苦难和愚昧的人性之书。胡风在《读后记》中指出《生死场》存在着三条“短处或弱点”:题材组织力不够;人物性格不突出;语言修辞锤炼不够——他先是说“语法句法太特别了”。我仅对“语法句法太特别了”稍有同感,却不认为是修辞锤炼的问题。因为一读之下略微费解的句子,再读,不仅释然,而且惊奇。鲁迅在《序》中用“越轨的笔致”——我理解这五个字的意思是:超越规范的用笔风格——形容《生死场》的文字,我十分钟意这种说法。“越轨的笔致”加上“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鲁讯认为它们为《生死场》“增加了不少的明丽和新鲜”。至于胡风批评的前两个问题,说全篇尽是散漫的素描,没有向心力,读者感受不到紧迫感;人物描写综合想象加工非常不够,人物性格不突出,不大普遍,不能明确地跳跃于读者面前……我则不仅完全不敢认同,还与之南辕北辙。的确,《生死场》是散漫的,没有主要人物,也没有主题。但一个个悲苦、麻木、屈辱的个体,特别是一个个女人赤裸裸的惨痛人生,其本身不就构成了强大的“向心力”吗?那便是对男权制度、对一切强权施加的不公不义、对一切非人性的揭露和批判,以及对未来深重的担忧。由这样的个体构成的乡村、社会、国家,能期望什么样的未来?这是萧红没有说出口的担忧吗?《生死场》对困苦、对挣扎的书写都是力透纸背的。也有光亮。在我看来,光亮仍然发自个体。金枝勇敢地出走,虽然被迫返回乡村,但她的见解,令王婆感到学识”有点不如金枝了。”觉醒,一定是一件个体的、自我的事,而不是集体齐刷刷地被唤醒。说到《生死场》中的人物,他们岂止“明确地跳跃”于读者面前?他们于我,简直是一头撞来,直撞进心里,撞得胸口生痛不说,一下子就生了根,想拔出来都困难。这样一群人物,哪里还需要“综合的想象的加工”?
</p>
<a id="back" href="#over">回到顶部</a>
</div>
</body>
</html>
css样式设置
/*生死场博客样式表*/
/*通用样式*/
body {
margin: 0;
/*背景图片样式*/
z-index: -10;
background-image: url("https://timgsa.baidu.com/timg?image&quality=80&size=b9999_10000&sec=1573910977810&di=b720f6369ede5d20d121b486e4867bd6&imgtype=0&src=http%3A%2F%2Fi1.hdslb.com%2Fbfs%2Farchive%2F9ff071d9d35d3c0e2a219b68ec4de42d5b694161.jpg");
/*https://ss0.bdstatic.com/70cFuHSh_Q1YnxGkpoWK1HF6hhy/it/u=2729724150,2476510592&fm=26&gp=0.jpg*/
background-position: 46% 40%;
background-attachment: fixed;
}
/*设置a标签*/
a {
text-decoration: none;
color: #f0f8fb;
}
/*悬浮态变化*/
a:hover {
color: #113355;
}
.clearfix:after {
content: "";
display: block;
clear: both;
}
/*左侧样式*/
.blog-left {
float: left;
background-color: rgba(128,128,128,1);
height: 100%;
width: 20%;
left: 0;
top: 0;
position: fixed;
clear-after: left;
/*!*右侧加边框*!*/
/*border-right:1px solid white;*/
}
/*画头像的圆*/
.blog_tx {
border: 3px solid white;
border-radius: 50%;
height: 150px;
width: 150px;
overflow: hidden;
margin: 15px auto;
}
/*设置图片的尺寸*/
.blog_tx img {
width: 100%;
}
/*设置标题属性*/
#title {
font-size: 20px;
text-align: center;
margin-top: 40px ;
margin-bottom: 140px;
}
/*去除列表的圆点*/
ul {
list-style-type: none;
font-size: 16px;
margin-top: 30px ;
margin-left: 30px;
}
/*上侧样式*/
.blog-top {
float: left ;
width: 80%;
height: 5%;
left: 24%;
right: 20px;
position: fixed;
background-color: rgba(128,128,128,1);
}
/*文本层样式*/
.text-page {
float: left;
height: 100%;
width: 80%;
background-color: rgba(128,128,128,0.5);
top: 20px;
left: 23%;
position: relative;
/*段落格式*/
line-height: 40px;
letter-spacing: 3px;
}
/*文本样式*/
.text-page p {
color: rgba(255,255,255,0.9);
text-indent: 32px;
margin: 20px 20px;
word-break: keep-all;
}
#back {
/*float: right;*/
color: black;
position: fixed;
border: #9bd4ff 3px solid;
top: 90%;
left:90%;
z-index: 100;
margin: 1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