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王夺嫡案是怎么收场的?
韩安国的劝谏之下,梁王刘武做出让步,逼羊胜、公孙诡自杀,以两个所谓凶案主谋者的尸体向朝廷使者交差。这样一来,案子虽然可以告一段落,但真正的幕后元凶也就不言自明了。
其实事情也可以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梁王刘武不妨早一点负荆请罪,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说自己和袁盎结有私怨,咽不下这口气,一时之间情绪失控,这才做了傻事。这样的话,不管刘武被怎么处置,只要兄弟之情不受影响,一切都好说。但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晚了。随着羊胜、公孙诡的死,案情进入了一个很敏感的阶段——要查的话,可以彻查到底,非要搞个水落石出不可;不查的话,也可以蒙混过关,大家心照不宣。
邹阳斡旋
这个时候,汉景帝的态度就变得至关重要了,而梁王刘武并不傻,察觉到了哥哥的恨意,于是派邹阳到长安,找王信想办法。
邹阳在前文有过出场,他是当时的辞赋名家,在文学史上很有一席之地,先前投靠吴王刘濞,见势不对就转投了梁王刘武,成为梁园雅集当中的活跃分子。王信在前文也有出场,他是奇女子臧儿和前夫王仲生的儿子,如今大妹妹做了皇后,王信就是国舅的身份了。
邹阳说动王信,抓住的要点是皇亲国戚同气连枝,一旦袁盎遇刺案被追究到底,梁王死了,窦太后的怒火没处倾泻,一定会找王信这帮人的麻烦,怨恨他们没有及时援救。王信没少违法乱纪,浑身上下到处是破绽,到时候窦太后要想找茬收拾王信,肯定一找一个准。所以呢,王信就应该赶紧替梁王求情去,只要保住了梁王,那还不被窦太后另眼相看么。
邹阳的这套逻辑,确实入情入理,而且就算退一万步说,无论皇亲国戚还是平民百姓,亲戚之间劝和不劝分,这是赚好感的经典操作,大概率上当和事佬总是最能给自己加分的。而那些袖手旁观和煽风点火的亲戚,即使一时得了好处,也难免将来倒霉。即便王信很认同袁盎曾经说的那套“君子大居正”的道理,但也同样应该明白自己是皇亲国戚,袁盎是外姓人,两者谋求幸福生活的策略一定不一样。
就这样,王信找机会开导汉景帝,稍稍缓和了汉景帝的愤怒情绪。
那么,窦太后现在怎么样呢?并不好。窦太后知道小儿子闯下了滔天大祸,整日里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就让汉景帝特别为难。
我们读这段历史,还是会很明显地感觉到在皇帝的家庭生活里,亲情依然占据着很高的位置。无论景帝也好,梁王也好,不论再怎么利欲熏心,到底还是一家人,有着很自然的血缘感情。景帝后来疏远梁王,也属于很自然的情感表现。窦太后说起来贵为太后,其实也就像一个农村老太太,眼睁睁看着老大和老幺闹矛盾,手心也是肉,手背也是肉,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熟人社会
就在这个时候,田叔、吕季主一行人办完公差,从梁国回来了。快要走到长安的时候,他们把所有案件卷宗烧个精光,空着手来向皇帝交差。接下来的这段对话相当经典。
景帝问道:“梁王参与了吗?”
回答是:“参与了,梁王有死罪。”
景帝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答是:“陛下您就别问了吧。”
景帝很费解:“为什么呀?”
回答是:“如果梁王不伏诛,那么朝廷法律就是一纸空文;而如果依法办事,太后她老人家吃得消吗,陛下您又该怎样面对太后呢?”
先前之所以要找田叔、吕季主侦办袁盎遇刺案,为的正是这样一种办案精神。田叔他们在梁国,办案办得急如星火,板子高高举起,震慑力必须有,还必须大。但结案结得轻描淡写,高高举起的板子必须轻轻落下。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者处置犯错的员工,往往也是这种风格,背后的道理很简单:真正处罚一个人,甚至裁掉一个人,在当时难于登天,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不处罚的话,一来犯错的员工会得寸进尺,二来无数双眼睛盯着,队伍从此就没法带。
儒家伦理是从熟人社会里边诞生出来的,也特别适用于熟人社会。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其实也是熟人社会,同事之间要处一辈子。
汉帝国虽然在一路推进中央集权,打破熟人社会,但像汉景帝这样,皇族的核心成员依然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里。那么案子到底该怎么侦办,就算田叔他们不是儒家出身,只要看得懂这一层基本的人情世故,自然就会心里有数。
药到病除
汉景帝于是让田叔一行人去窦太后那里做汇报,屎盆子全扣在羊胜、公孙诡两个死鬼头上,梁王刘武仍然是一朵纯洁无瑕的白莲花,是老太太最疼爱的小幺儿。
这可真是药到病除,窦太后马上就有胃口了。
当然,窦太后也不傻,她对案情的真相肯定会有自己的判断,只不过在她而言,重要的并不是梁王刘武到底是不是无辜,而是汉景帝能不能法外开恩,放过这个兄弟。
而值得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假如窦太后前些年就已经死了,那么汉景帝这一次会不会放过梁王刘武呢?
估计并不会。
这才是梁王刘武必须直面的严峻问题,可不能因为案子结了,羊胜、公孙诡当自己的替死鬼了,就能相信“风穿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所以呢,案子虽然结了,但事情并没有完。
如果梁王刘武因为自己被判无罪,就真的拿出白莲花的姿态如常生活的话,那么灭顶之灾就离他不远了。也就是说,在国家大事的层面上,梁王虽然洗清了嫌疑,可以挺直腰板做王爷了,或者说,他可以不认错,而在家庭关系的层面上,他必须拿出十足的知错悔改的姿态,去软化哥哥的心。
这种事情,分寸感很难拿捏,既要伏低做小,又不能直接认错请求宽恕。
疏远梁王
刘武的做法,简直就是一场行为艺术。他先是给朝廷上书,请求进京朝见,然后在到达函谷关的时候,把大部队留在关外,只乘坐一辆很不起眼的小车,带着两名骑马的随从,无声无息地前往长安——但不是直接入宫,而是躲进了自己的亲姐姐馆陶长公主刘嫖家里。于是,当朝廷使者迎接梁王的时候,却发现梁王神秘失踪了,只有随行的人马留在函谷关外。
窦太后当即就哭了,说梁王一定是被汉景帝杀了。
汉景帝又是担心,又是焦躁,不知道如何是好。
而就在这个时候,梁王突然现身,不再是以前那种车马如云、光鲜靓丽的样子了,而是孤零零的,摆出一种类似于负荆请罪,但并没有真的负荆请罪的姿态。这就像一个犯了错,受不得爸爸妈妈的批评而愤然离家出走的小孩子,在出走了一整夜之后突然出现在家门口一样,紧张、害怕、想家,似乎心里知道错了,但紧紧抿着嘴唇,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泪珠马上就要掉下来的样子。
好吧,回来了就好。窦太后和汉景帝如释重负,一家三口顿时哭在一起。
家人嘛,没有隔夜仇,关系恢复如初。
擢为鲁相
当然,只是貌似恢复如初,扎在汉景帝心里的那根尖刺早已经生根发芽了。等这一时的亲情下了头,从此他就疏远了梁王,不再像以前那样两兄弟同乘一辆车了。至于田叔,因为办案表现出色,有大局观,因此很受汉景帝赏识,出任鲁国国相。
这位田叔,前文已经有过出场了。那还是刘邦时代,赵王张敖被控谋反,案子搞得血雨腥风。逮捕张敖的时候,刘邦下过严令,张敖的官僚、宾客如果有谁胆敢追随张敖,一律灭族,但田叔、孟舒等人自己剃掉头发,套上枷锁,自称是张敖的奴仆,追随张敖到了长安。《史记》的记载比较详细,说追随者一共有十几个人。后来案情水落石出,刘邦将这十几个人尽数授予要职,要么是郡守,要么是诸侯相。在这些人物当中,田叔是最耀眼的一个。(S3-155)
交代几句后话。田叔的儿子田仁颇有乃父之风,在汉武帝时代名扬天下。后来发生了巫蛊事件,汉武帝疑心太子刘据造反,当太子兵败,逃到城门,想要逃出长安的时候,负责把守城门的正是这位田仁。一个两难的局面就这样摆在田仁面前:忠于职守的话,就必须严守城门,甚至捉拿太子。但人家只是父子之间闹矛盾,不管现在的阵仗看上去有多大,毕竟打断骨头连着筋。怎么办呢?田仁故意卖个破绽,由着太子出城逃走了。(《史记·田叔列传》)
那么问题来了:田叔放过了梁王刘武,因此被汉景帝提拔;田仁放过了太子刘据,因此被汉武帝批捕处死,到底谁做对了,谁做错了?
景帝中二年(前148年)的大事件到此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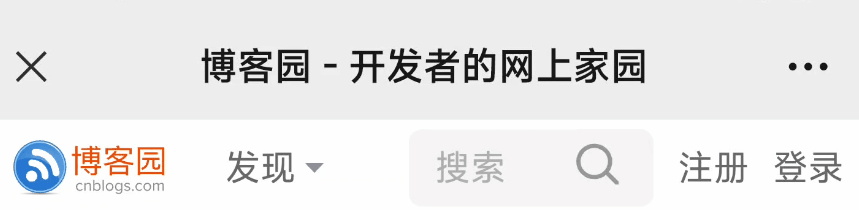
【推荐】国内首个AI IDE,深度理解中文开发场景,立即下载体验Trae
【推荐】编程新体验,更懂你的AI,立即体验豆包MarsCode编程助手
【推荐】抖音旗下AI助手豆包,你的智能百科全书,全免费不限次数
【推荐】轻量又高性能的 SSH 工具 IShell:AI 加持,快人一步
· 无需6万激活码!GitHub神秘组织3小时极速复刻Manus,手把手教你使用OpenManus搭建本
· C#/.NET/.NET Core优秀项目和框架2025年2月简报
· 什么是nginx的强缓存和协商缓存
· 一文读懂知识蒸馏
· Manus爆火,是硬核还是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