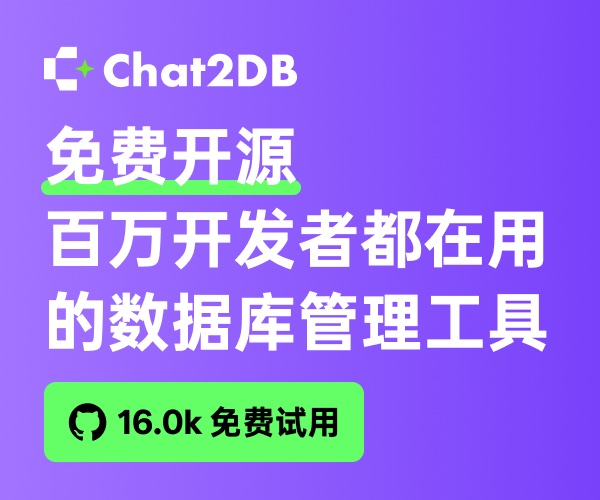寂寞凌迟(转)
手中做着某件事时,寂寞来袭。它像是某种隐痛,不为人知,不可言说,亦难以抵抗。有时可以享受它,可是在人们最为脆弱的一刻,寂寞作为灭顶之灾,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人的意志。
寂寞是凌晨惊醒时的一杯冰水。是繁华地段中各自奔忙的人。是日本料理店中独自面对的一碟精致昂贵的生鱼寿司。是表情僵硬的女子眼边的一颗泪痣。它是这样含蓄的暗涌,除了寂寞的人本身,我们无法预知当寂寞来袭,内心有怎样的压抑深楚。
都市里的人似乎大都有一种天生的疏离感,因此更需要制造些热闹的声色。即使一群陌生人,亦可以勾肩搭背。那些无关痛痒的玩笑话,纵使无趣,也大抵百听不厌。而我在这些场合中,向来是扰人兴致的一个。有时沉默得尴尬,或者笑得突兀。既然这样,不如一个人去百无聊赖罢。
城市里的邂逅大都平地起风无始无终。所有人都可能在某一刻互相紧挨着取暖,然后彼此离散,最终各自溺毙在人群洪流里。无处告别。这开始及结束,大抵都是因为寂寞。开始的时候,是觉着一个人寂寞,而结束,是发现两人比一人寂寞。
张国荣在他最后一部电影里说,人的脑袋是个比宇宙还大的东西,每天接收不同的信息,不知不觉中就会收集一些垃圾,不及时清理,就会沉淀下来,然后让人产生幻觉。这部电影的名字,是《异度空间》。抛开它的心理学主题不说,便能归为惊悚片,午夜看来,足够寒心。“人的脑袋”和心永远是我们无力测量的深渊,我们对于自己的了解,如同汪洋中的一滴水,且不说多少,是清或浊,我们都无法确知。原来寂寞可以被植入
寂寞总是挑在一些冬天的凌晨偷袭我。比如现在。面对这种任人宰割的滋味无所适从,放着音乐和电影神经质地紧张兮兮。有时穿上我玛格丽格的低跟白凉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侧耳听着鞋跟轻轻叩在地板上的声音。像一个疯子。我似乎始终是一个与人交往有障碍的人,因为长久的寂寞,身上散发着腐朽的气味。当我坐在窗台蜷起腿吹风时,这种气味尤为强烈。然后我开始对着纸张喋喋不休,像一个间歇性狂躁病人的喃喃自语。
张国荣在《异度空间》里对着幻觉,对着早已跳楼自杀的女友说话。他说,我不快乐。你走了以后,我一直不快乐。
镜头可以表现寂寞,但不能形容。文字亦如是。当一个镜头以缓慢沉着的姿态向前推进,掠过路人光影,掠过《the wall》中Pink毫无生机的双眼,掠过《东邪西毒》里黄药师的醉生梦死。真正的寂寞不是声色犬马场合里和平共处的人群,这样高声喧哗的寂寞无法接受深究。真正的寂寞是一个女人独自去市场买菜,做饭给自己吃,然后对着镜子发现脸上的第一道皱纹。喝着水突然落下泪来,无力挽回自己迅速苍老的容颜,眼睁睁看着自己奔向市井妇人的邋遢形象。寂寞就是这样琐碎,贫乏,平庸,乃至虚无。任何华美修饰都微不足道。每个人都会在某刻感到无法抵御的寂寞。即使有时,我们自己都无法获知这样的无助及沮丧就是寂寞。
我在小说《药》里写到一个老男人轻唤冬喜:little girl.是那样温暖宠爱的口吻。亦是笃定的,坚信她应该得到安定的美好牌生活。也许是我本不相信,于是这样详尽地写它,藉此来填补自己心里的空缺。这样包容的感情,不必爱,只要完美的温情。它是否可以得到救赎,抵挡寂寞。
每天凌晨将睡前,翻遍手机里所有电话,确认没有人可以在这样的时间听我絮叨的倾诉。倚在墙边发呆半晌,息灯躺在床上,辗转一小时后做一个悠长混乱的梦。不到四小时迷糊着爬起床,努力睁着渴睡的眼刷牙洗脸。穿上厚衣服裹住我一夜都未能回暖的皮肤,开始劳顿于身外事。寂寞就是在这时候现形的,是沉闷盲目的生活带来的怅惘。
左耳幻听,繁复钝重的杂音缭绕不散。右眼发炎,瞳孔周围散出一圈漂亮的暗红阴影。
我们给自己裹上标签,是害怕不小心暴露出可耻的寂寞,从别人的眼里探询到悲悯。是,我不够美丽,我知道。但我自有淡定和沉静,即使不能绝代,亦自有风华。
寂寞非常,一刀一刀割进皮肉,反复摩擦在骨头上。这时候,我们多么怜惜自己,以致我们的每一寸皮肤都伸出手,紧紧地拥抱了自己。
寂寞已经被人说滥了,我在这里仆仆前人的后尘,大抵也无伤大雅。滥一点,再滥一点,它仍然无可避免。
张国荣那天到了酒店,对服务生说,你帮我拿纸和笔;他又说,你再去帮我拿一点饮料,好吗?——据说,这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他从高楼一跃而出,寂寞么?
后记
写完这些文字,我坐在书桌前看书到凌晨五点。握着手机打扰了一个男子。我再次确知,寂寞以及眼泪,都是可耻的,被禁忌的。如同在地铁上众目睽睽之下一个女子突然掩面而泣。那些目光中的好奇和揣度。它们如果仅仅在我们独自一人时发生倒也无伤大雅,一旦曝露在日光下,大抵只会让看到的人尴尬。
然后手机在凌晨五点半被限制呼出。感觉像是突然被隔离。独自在桃花源生存。我坐在地上把头埋进膝间,身体慢慢开始了一场漫长的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