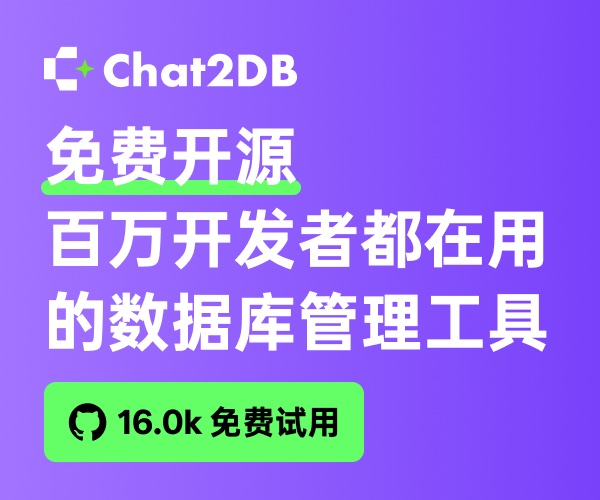你为什么成不了比尔·盖茨?
不必沮丧,不必恼怒,毕竟,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比尔·盖茨,准确地说应该是:我们为什么成不了比尔·盖茨?
“开什么国际玩笑,我一个连住房按揭都还不过来的'月光族',还比尔·盖茨呢!”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只能说明你在思维上与比尔·盖茨相差一光年,比财富上的距离还远—是的,正如巴拉昂秘诀所揭示的,你缺乏野心!
比尔·盖茨的偶像、世界上第一个亿万富翁洛克菲勒曾豪言:“如果把我剥得一文不名丢在沙漠的中央,只要一行驼队经过—我就可以重建整个王朝.”世界旅馆业大王康拉德·希尔顿则表示,当他潦倒困顿到必须睡在公园的长板凳上时,他已经知道自己以后将会成功.这就是野心的力量!
比尔·盖茨自然是幸运的:他自己亦坦承,如果王安能完成他的第二次战略转折,世界上可能就没有今日的微软,“我可能就在某个地方成了一位数学家,或一位律师”,此乃天时;微软公司创办25周年之际,《今日美国报》记者问他对美国政府决定分割微软的看法,他回答说:“撇开这宗诉讼不谈,这仍是一个利于创业的伟大国度.我对这个国家的感激,远胜于这宗针对我们的官司.”比尔·盖茨本人无疑是“美国梦”的最佳诠释.此乃地利;更关键的是,他在选择学校、专业乃至选择退学上最终都得到了父母的理解和支持,他担任IBM董事的母亲“以自己的成就和人格为我的爱子作最好的担保”帮助初创的微软获得了至关重要的第一份商业合约,而其身为知名律师的父亲亦在商务处理方面颇多助力,此乃人和.
除了天时、地利、人和,最重要的,当然仍是天才企业家的个人禀赋.《影响历史的商业七巨头》一书的作者、哈佛商学院教授理查德 ·泰德罗就认为:“这本书里的主人公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教育的”.甲骨文CEO拉里·埃里森甚至声称:“一顶帽子一套学位服必然要让你沦落……”伟大的企业家没有一个是读出来的,他们总是创造或改写商学院案例,而非学习案例.“有能力把自己写进艺术史的人,不会做一个评论家”,尽管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 这一论断在某种意义上同样适用于企业家.德鲁克就说过:“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在于成果.”
1975年,就在比尔·盖茨创立微软的同时,同年出生的史蒂夫·乔布斯也在车库里创立了苹果电脑.随着公司的成功上市,25岁的亿万富豪乔布斯亦成了全美年轻人的偶像.然而,今天盖茨的个人财富(约600亿美元)却整整超出乔布斯几十倍.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就在电脑还是摄影棚似的“巨无霸”时,盖茨已认定基于小型个人电脑的软件才是未来趋势.这样的洞察力只能源于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商业本能.商人同样怕入错行,无论如何卓尔不凡,我们都无法想象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会成为今天的全球首富,这是其传统媒体的行业属性决定的,与企业家个人的才华与努力无关.
仅有远见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行动.“于尚未开始的领土,不可能有一副可靠的地图”,仅从《大众电子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比尔 ·盖茨就敏锐地意识到这将是一片“流淌着奶和蜜”的商业新大陆.他没有迷恋于哈佛的光环,而是当机立断选择辍学创业,这是一个近乎赌注的商业决断,也许是商业史上“最伟大的放弃”之一.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混沌理论”同样适用于商业领域.事实上,当年比尔·盖茨曾与一位叫科莱特的哈佛同学商议一起退学去开发 32Bit财务软件,科莱特却委婉地拒绝了.1995年,已拿到博士后学位的科莱特认为开发32Bit财务软件的条件已成熟,比尔·盖茨却绕过Bit系统,开发出比它快1500倍的Eip财务软件,在两周内占领了全球市场,并在这一年成了全球首富.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关键处却只有几步.”想想格雷的教训吧:这位与贝尔几乎同时发明电话的技术天才,只因申请专利晚了两小时而黯然出局,而贝尔则成了商业巨子.是的,短短120分钟,就决定了命运的巨大分野!这是商业残酷的一面,也是其魅力所在. “我花了整个上午校对一首诗,把一个逗号删掉了;到了下午,我又把逗号放了回去”(王尔德),与追求不朽经典的文学相比,强调行动哲学的商业更像“遗憾的艺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你如果非得坚持将商业计划书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推敲无误后再去实施,机会女神可能早已溜走.从MS-DOS到Windows Vista,微软从不奢求完美,有的只是“我们一直在努力”.
无独有偶.当年与丁磊同时进宁波市电信局的大学生有52个,但走出来的,至今只有他一人.后来他这样回忆道:“这是我第一次开除自己.人的一生总会面临很多机遇,但机遇是有代价的.有没有勇气迈出第一步,往往是人生的分水岭.”当年陈天桥从一家企业跳槽,公司挽留他“等分了房子再走吧”,他却不为所动: “难道我这辈子自己还挣不了一栋房子?”后来他曾自我评价道:“我的心理从小就愿意承受风险,我是一个大赌、大输、大赢的个性.”曾以杨振宁、陈景润为偶像,“理想是关在只有一盏小煤油灯的屋子里解数学题,一整天只吃一个冷馒头”的张朝阳则表示,“在决定经商之前,早已放弃了诺贝尔物理学家的梦想”.“不要问现在加入商战是否太晚,按照现在信息经济的发展速度,谁又能够承担不参战的责任呢?”1999年,李彦宏毅然启程回国创业.
放弃是困难的,无论是一个金饭碗、一套即将到手的房子还是曾经的理想…….“对于无产者来说,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一个已有清晰人生图景的中产者,为何还要投身于巨大的不确定性中?于是,太多的人在患得患失中坐失良机,太多的人满足于饭桌上的高谈阔论却从未想过付诸实施.这也许就是许多巨富都出身赤贫的原因所在.在某种程度上,埃里森的“蛊惑”不无道理:“离开这里.收拾好你的东西,带着你的点子,别再回来.退学吧,开始行动.”除了行动,你别无选择!
仅有天才的idea是不够的,你还得有执行力:资源整合的能力、团队合作的能力、危机处理的能力…….有时候,起得早不如赶得巧,栽苹果树的未必能吃上苹果.生产出第一台电脑的苹果公司,最终却被挤出计算机主流企业之列,乔布斯自己也一度被炒了鱿鱼.陈春先,这位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营科技机构的“中关村第一人”一生始终难以跨越技术与商业的鸿沟.
运气的因素永远不可忽略.人生有太多的偶然性,智力从来就不是商业成功的充分条件.事实上,真正的“DOS之父”很早就在一场酒吧斗殴中丧生.一位著名风险投资人曾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他们所投资的一家公司,创业者各方面都很优秀,就是喜欢飙车,结果死于一次车祸.在孙宏斌看来,无论是丘吉尔、罗斯福还是杨致远,他们的成功其实都源于某种风云际会的因素,“一下子,偶然的一下子……”,对于那场深刻改变了自己人生轨迹的牢狱之灾,他亦有独特理解:“没有那样的经历也许你没有今天这样的成长或者成就,你就是联想的一个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就是中关村一个小公司.”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即使你身上已具备几乎所有成功因子,一个关键性意外就足以让你功败垂成.即使你拥有比尔·盖茨式的天才,由于“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你仍无法复制他的成功.
“伟大是熬出来的”.事实上,即使是那些今天看来堪称伟大的公司,也并非一贯高瞻远瞩,在其成长史上同样不乏试错、机会主义、太多的踉踉跄跄和“差点死掉”.最富戏剧性的也许当数美国联邦快递公司的创始人弗雷德·史密斯,一次他靠在拉斯维加斯玩二十一点纸牌赢得的27000美元支付了员工工资…….虽然 “成功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难”,但也绝非地摊励志书说的那么简单.张朝阳曾以“惊弓之鸟般的等待”形容筹措第一笔风险投资的艰辛,陈天桥则坦承“一年里承担了别人十年的风险”、“半夜醒来一身冷汗”,腾讯CEO马化腾在最艰难时甚至曾计划以100万元将QQ转让,却被认为“开价过高”谈不拢而告吹……
在这个十倍速时代,你得时刻谨记“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在这个天才辈出、声称“35岁就退休”的“挨踢”业,你得时刻“保持饥饿,保持愚蠢”; 你得面对埃里森这样的“硅谷坏小子”发出的成吉思汗式的“咆哮”:“仅仅成功是不够的,其他人必须失败.”你得面对旷日持久的可能法律诉讼…….与杰克· 韦尔奇宣称的“商业就是生活,是每天我们都想打赢的一场游戏”的洒脱相比,现实也许更接近泰德罗对柯达公司创始人乔治·伊士曼的评论:“我不愿意说他爱的是生意本身,生意意味着战争.生意意味着冷酷无情,生意是伊士曼生活中黑暗的一面.”或是泰德罗在《IBM王朝》中向你揭示的:伟大的“Think”背后伟大的不择手段.
现在,问题变了:你还愿意成为比尔·盖茨吗?
什么都有代价.商业价值与文化理想间永远都有矛盾.与西装革履的比尔·盖茨相比,更富反叛色彩的乔布斯被视为全球最酷的企业家,他是IT界的时尚先生、商业领域的艺术家,甚至,硅谷的精神领袖.当然,对应的是,他永远也无法成为全球首富.莫非这就是商业领域的“政教分离”?
哈耶克认为,一个“伟大社会”应鼓励一切个体在一切可能的方向探索.正如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独一无二的你,DIY自己的人生吧.即使在比尔·盖茨面前,你也无须自惭形秽,只要你心中仍有爱、诗意与梦想.想想莫利(C.Morley)的话吧:“只有一种成功,那就是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好了,现在,让我们回到正题—
中国的比尔·盖茨,
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2006年美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约26.7%的被调查者认为下一个比尔·盖茨最可能出自中国.2007年4月比尔·盖茨第十次访华时亦预言:下一个伟大的成功将会来自亚洲.英国卡斯商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全球45岁以下最年轻有为的前10名CEO中,有8名来自中国.“下注中国”,这是2006年美国《巴伦周刊》给出的口号.2007年初的《时代》周刊以《中国世纪》为封面故事.高盛的一份报告指出,35年后中国将成全球第一经济体,而美国则仅列第三…….正如比尔·盖茨所指出的:“一个人拥有的机会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在哪个国家所决定的.”无论这些分析充满多少溢美之辞,至少在宏观上预示了下一个比尔·盖茨的可能.
德鲁克认为,一个时代、一个区域的社会类型可以从其“首富”的特征中直观地获知.放眼全球,与GOOGLE财富神话相映成辉,印度的钢铁大王、墨西哥的电信巨头及中国的地产大亨,这些新一代的洛克菲勒们正试图利用全球资本市场完成整合传统行业的“炼金术”.对于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并存、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复合”转型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来说,“饲料首富”、“钢铁首富”、“房地产首富”、“软件及互联网首富”等完全可能同时涌现. 由于后发优势,互联网正是中国少数完全与国际接轨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这无疑为中国的比尔·盖茨的出现奠定了产业基础.
资金并不是真正的问题.盛大网络崛起后,一家国际风险投资机构的中国区负责人批评其下属:你身在上海,为什么没有发现盛大?在资源与市场都日益全球化、流动性泛滥的今天,“世界是平的”,真正稀缺的并不是资本,而是创新.
创新对于企业家来说永远是第一位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有“一俊遮百丑”之效.正是创新,让当年的乔布斯一不小心成了“暴发户”,美国航天工业巨子休斯公司的副总裁艾登·科林斯慨叹道:“我们就像小杂货店的店主,一年到头拼命干,才攒那么一点钱,而他几乎是一夜之间就赶上了.”
也正是创新,才是我们的最大软肋:无论是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还是管理创新…….除了缺乏核心技术,我们亦从未出现类似福特流水线、通用事业制度、丰田生产方式、连锁店这种级别的组织创新.即使是互联网领域,成熟的商业模式也大多拷贝自美国.英特尔董事长安德鲁·葛鲁夫曾断言:华人对财富几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创造力,但对组织的运作似乎缺乏足够的热情与关注.WTO前总干事穆尔甚至认为:中国企业的管理相当于30年前的日本,相当于100年前的英国.
当中国的IT精英们在很大程度上因受惠于NASDAQ的“中国溢价”因素而获得个人财富的“爆米花效应”时,也许有必要重温一下戴尔在总结自己“如何管理 30亿美元的公司”时说的话:“大多数公司的发展和成熟的脚步都比我们慢许多,但他们在规模尚小的时候所学到的基本程序,我们这时候必须回头认识.”
对于巨额财富,黄光裕直言“没感觉,假如你在不停地发展自己的事业,那么它就不是财富;如果停下来了,它或许是.但最大的可能是,今天你一无所有,但明天你什么都有了,而后天你又回到了起点.”作为“剩者为王”的马拉松而非百米冲刺,商业更需要“韧的战斗”.中国从来就不乏“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明星企业, 不乏“增长速度回落到400%”式的狂飙突进,惟独缺乏基业长青的百年老店!“涨潮的时候,看起来所有的人似乎都在游泳,一旦退潮,谁没穿衣服便一目了然.”与GE这样的百年老店相比,还没有哪家中国企业经受了完整经济周期的洗礼.正如任正非在考察了连续十年经济衰退的日本之后写下的那篇著名的《北国之春》所说的:“什么叫成功?像日本企业那样,经九死一生还能好好地活着,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华为没有成功,只是在成长.”与比尔 ·盖茨连续12年蝉联全球首富的记录相比,不断刷新的“中国首富”既是活力的象征,也寓示着脆弱和不确定性.
谁扼杀了我们的创造力?
曾任美国总统的艾尔文·柯立芝有句名言:“美国的事业是企业”.今天的中国却出现了公务员热.即使是在以个人创业精神著称的温州,那句“再不好好学习长大了就当干部”也早已变成了“好好读书长大了好当干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一个事实是:1999年至2004年6年间全国个体户净 “缩水”810万户.除了结构升级因素外,创业环境不尽理想应是主因.
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世界银行的教授对85个国家和地区所作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从申请注册公司到开业,加拿大只需2天,中国内地需111天;再来看注册资本(以股份有限公司为例),中国内地为1000万元人民币,日本约为82万元人民币,美国则为零.另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07全球商业环境报告》,在全球商业运营活动的便利性排名中,中国位居175个经济体中的第93位.
“春江水暖鸭先知”,对于创业环境,一线的企业家们最有发言权.柳传志曾以“孵小鸡”为比喻形象地诠释“市场温度”的变化.史玉柱曾对媒体叹苦:“我随便写了民营企业的15个死法,随便一条就能把你搞死……我觉得我们比下岗工人更苦.”更有甚者,据说亚都公司CEO何鲁敏的办公桌边放着一个小包,毛巾、牙刷都准备好了,“如果来抓我,我随时都可以跟着走.”让何颇为感慨的是,他在美国时发现:在一些大家聚会的会所,或者咖啡馆里,有人吃饭、喝咖啡是不花钱的.仔细一打听,才知道那就是失败的企业家.在中国,企业家一旦失败,面临的更可能是“以落井下石的火力一夜间摧毁被它们吹捧了几年的企业”的舆论环境.
不妨进一步设想一下:我们未来的比尔·盖茨的街头小贩创业实践会不会被城管扼杀在摇篮中?与硅谷的车库创业文化相比,在一刀切式的“民宅禁商”政策下,北京、上海那些刚起步的小公司,会不会因寸土寸金的高昂房租而倒下?公司稍有规模,面对形形色色的“赞助”电话,你如何说 “不”?面对工商联副主席或政协副主席的可能邀请,会选择“商而优则仕”吗?……
鲁迅先生早就强调过“做土”的重要性:“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正是由于创业环境的差异,硅谷的创新型公司在风险资本的“催肥”下迅速成长为参天大树,而中国一些颇有潜质的中小企业却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成了“小老树”.
《基业长青》和《从优秀到卓越》的作者吉姆·柯林斯认为:“人类历史上,一些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发明其实并不是技术或产品,而是社会发明.试想一下美国宪法、货币或者市场机制等概念的诞生.它们永远都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创造.”就此意义而言,在期待中国的微软之前,我们也需要中国的摩根斯坦利、中国的华尔街日报、中国的麦肯锡、中国的奥美等商业支撑体系,同时更需要自由市场、法治等社会支撑体系!
“创意创造生意,想象力创造利润率”,在一个内心荒芜的时代,曾经的诗人江南春转而向商业世界寻求诗意.可是,我们的头脑早就被格式化了,还能有什么想象力与创造力?
“《易经》里没有强大的秘诀,《庄子》里没有自由的路径,《资治通鉴》中找不到民主人权的旗帜,《论语》里也没有宪政的痕迹,要去《尚书》中发现共和同样只会是无益的徒劳,而秦皇汉武们留下的只有奴役和专制.”在学者黎明看来,自2000多年前的秦政,中国人就已失去想象力了.
杨振宁教授曾提出一个观点:创新可分为爱因斯坦、杜甫、比尔·盖茨和任天堂四种体系,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盖茨和任天堂,暂时拿一两个诺贝尔奖并没有什么用处.其实,科学、人文、商业之间本就相通并互为促进,对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来说,比尔·盖茨、任天堂与爱因斯坦、杜甫或可并存.美国学者波特的一个观点早已被广泛认同: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最难替代和模仿、最持久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很难想象,一个在文化上未有丰富创造的国家,能实现真正的“崛起” 和“复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认为: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正如知名青年评论家许知远所言:我们期待一个真正的社会精英群体的出现……按照20 世纪50年代那个充满激情的个人主义者爱因·兰德的说法,“他们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是文艺复兴之父,是工业革命之父,是科学之父,是个人主义之父,是资本主义之父……”
教育部部长周济曾坦承,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不足是中国教育的致命缺点.张朝阳回忆起当年水木清华的校园生活时仍不胜感慨:“被伤着了”,“不停地比,比谁的作业先完成,谁学习的时间最长……整个小社会只提供给你一种可能性……”自认“(大学时代)不是个好学生,上课总拣'偏远地区'坐下”的丁磊曾表示,当下大学生的知识结构还不具备一毕业就创业的条件,这是我们的教育体制所造成的.在《中国企业家》采访的10多位“80后”创业者中,许多人都从未在传统教育体制内获得肯定.《南方周末》曾报道当年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神童”宁铂出家的新闻,他这样抱怨:“'神童'剥夺了我许多应该享有的生活和娱乐的权利”……
作为“80后”的PCPOP网CEO李想来自一个环境宽松的家庭,“我小学时父母给的是命令,初中时给的是建议,高中时是从朋友的角度提出参考,到了高中以后就是信任了.”比他年长一些的创业者则没有那么幸运:丁磊当年从宁波市电信局辞职,就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我父亲总是打击我”,江南春的父亲是一位审计师,推崇稳健、平淡的生活,至今他对儿子的人生观念还是不大认同;曾梦想成为“中国的微软”的科利华公司的总裁宋朝弟 600元的创业资金是向家里要的,“我不敢说生意,他要让你当教授,走正道.做生意那不是白培养你了吗?”……
在一些家长眼里,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孩子成了没有生命的石头,在自己并不高明甚至拙劣的手艺下,天才的棱角被“打磨”殆尽.鲁迅先生曾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呼吁解放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 “伤仲永”式的“捧杀”与“耳光教育”式的“棒杀”仍时有所闻.
谁妨碍了我们长大?
“在中国,社会对企业家的期许,以及这个财富群体的自我膨胀即将达到顶点.”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他《被夸大的使命》一书中说.在并不漫长的中国当代商业史上,许多声称要做“中国的微软”、“中国的IBM”、“中国的GE”、“中国的松下”、“中国的索尼”、“中国的麦当劳”、“中国的可口可乐”、“中国的八佰伴”、“中国的巴菲特”、“中国的索罗斯”……乃至“真正的世界级企业家”的人都纷纷倒下了.为什么比尔·盖茨和他的微软帝国能在30年的跨度里 “每一次我们都经受住了考验”?
商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场与人性间的战争.正如一位企业家所言:“在任何时候,人,都是输给自己的.”张树新,这位“可以把读哲学当作休息”的企业家,曾这样反思道:“每个人都有误区,总是认为自己不可以被别人替代.”在有“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传统、“一年合伙,二年红火,三年散伙”的中国商界,你能找到一位像保罗·艾伦那样甘当“绿叶”、几十年默契如初的绝佳拍档吗?大多数成年人都能顺利爬上香山,但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成功登顶珠峰.不少温州商人在资产过亿后欲再攀高峰,却纷纷遭遇“高原反应”.在温州有这样一个说法:“即使你做了微软的CEO、IBM的总裁,都不如做一个小卖部的老板'值钱'”.如果并购重组意味着自我退出,对于视企业为“己出”的企业家来说,这不啻为自我宣战!“万科不是我的儿子,他是我的作品.”像王石这样有着清醒认知的企业家毕竟太少.阿里巴巴CEO马云无疑是有大梦想的人,对他来讲,成为一个“伟大的公司”远比“一个人的帝国”更有意义,因而才有阿里巴巴与雅虎的合并.在马云看来,生意人是做买卖,商人有所为有所不为,企业家是影响一代人的生活,在中国80%是生意人.
迪斯尼无疑是“影响一代人的生活”的企业家的典范.是他以爱灌注了那些卡通精灵,“使千千万万的人们享受到了一种更光明、更快乐的生活.他所创造的真、美和欢乐是永世不朽的.”(美国前总统约翰逊语)柯林斯则将现代公司的意义提升到“社会发明”的新高度:“决不仅仅因为它是技术革新的源泉,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是连接市场机制与民主政治的桥梁.”在这个意义上,商业与公民社会间的价值链得以打通,也因此才可能出现德鲁克所说的“企业家社会”.
美国作家罗伯特·索贝尔认为:在每一个关键历史时刻,企业家既影响社会和经济变化的严酷无情的进展,同时又受这种进展的影响.段永基曾坦承:“中国的现代企业很难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建成—我们都是过渡性人物.”王石则曾不无悲观地认为:“我们儒家文化背景、小农经济操作方式,已经决定了我们的性格,包括我本人,是不适合搞全球大企业的.”“我们中国企业由盛至衰的周期也就是20年、25年吧.”著名学者秦晖认为:“就中国没有 Citizen而言,实际上我们都是农民”.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则认为:中国“入世心态”的超越方式仅仅是此世的“立德、立功、立言”,这使得中国企业家大凡有了些成就的总要去追求“济世”的功业,所谓“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他并表示,就我们尚未获得西方自启蒙时代开启出来的个体理性这个意义而言,我们都是难以自立的儿童.
心理学大师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决定着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这条无意识的河流.什么样的市场,造就什么样的企业家.“转轨+新兴”市场的独特成长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部分中国企业家“原罪”性的世界观和机会主义的方法论.盛田昭夫曾说过,“我们日本商人必须是两栖动物,必须在水中和陆地上生存.”反映了那一代日本企业家在日本与西方价值观之间的挣扎.在今天的中国企业界,你同样可以轻易发现前现代思维与后现代技术的碎片.杰克·韦尔奇自传与《曾国藩家书》、《胡雪岩》同步流行—“历史叙事”与“科学叙事”的分殊同样反映在畅销书领域.“振兴民族产业”的口号与具体经营中“冷酷打击,坚决消灭”的对手观可以并行不悖而不会有丝毫心理上的不安…….致力于中国企业史研究的吴晓波以极富传神的笔法描绘了一幅过去30年活跃于中国商界的族群的图像:“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博取.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捷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得他们能够拨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的不畏天命使得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的规则与准绳.他们的贪婪使得他们敢于采用一切的手法和编造最美丽的谎言.”尼采认为,人生必经“由骆驼至狮子而至婴儿”三阶段.在一些中国企业家试图像洛克菲勒一样成为市场上的“狮子王”时(其实更多的时候只能像土狼一样在全球产业链上吃点残羹冷炙,而狼性也已成为早期某些企业家的基因),他们却没有后者的清教传统,而曾经的 “骆驼”精神也早已不再,当然他们也没有像晚年的洛克菲勒那样进入“婴儿”般纯真状态的可能.
一代人的迷惘与凯恩斯的忧虑
2002年,麦克斯·拉夫琴(Max Levchin)这位硅谷最年轻的“王子”在将自己开发的电子支付系统Paypal卖给eBay之后,陷入了一生中最灰暗的日子:他花340万美元买了一幢山顶豪宅,却从未搬进去住过一晚;他百无聊赖地骑车逛街,与女友厮混…….是的,退休太年轻了一些,当慈善家又坐不住.内心告诉他,必须重新找回创业的激情.于是,2005年他成立了自己的新公司Slide.曾有人问他干嘛这么拼命,他的回答是,“因为我觉得好玩.好玩,所以不想停下来”.在接受中国《财经》杂志记者采访时,他说:“定义一个大公司的成功,可以是'非常成功',但也可以是'比较成功',或'今年不成功明年成功',这只是程度的问题—不是那么关键性的成功.但是,创业很特别—不成则败.它就像赌博,让人兴奋.”
28岁的李嘉诚、30岁的陈天桥同样曾经历相似的迷惘.“就好像爬山,我已经爬到了顶峰,然后还有什么奔头呢?”而立之年即荣膺“中国首富”的陈天桥曾这样袒露心声.在搬到位于香港半山的新家的第一个夜晚,李嘉诚怎么也睡不着,整个晚上都在“痛苦和快乐的回忆中度过”.伴随“像火箭上升一样积攒财富”,一直忧心忡忡的日子终于彻底结束了,自己平生第一次可以放慢脚步思考人生的意义.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晚上,他常来到宝珊道上靠着路边的石头发呆.“财富能令一个人内心拥有安全感,但超过某个程度,安全感的需要就不那么强烈了.”他后来这样回忆道.
多年后,李嘉诚依然保持了早年的那种“饥饿”感.1999年,在完成“卖橙”(欧洲Orange电信公司)这一“世纪交易”的记者会后,他拿起一块饼干以充腹饥并奖励自己.就在前一天夜里,临睡前他特意将手机放在枕边,并将铃声调到最大,惟恐在睡梦中错失交易落实的喜讯.虽已富可敌国,却还这么“搏命”, 有谁能读懂这位华人首富的内心?
“如果看着比尔·盖茨的财富和你自己的距离那么大,那么你永远不会快乐.”说这话的人是李嘉诚,“我知足,但不表示没有上进心.”在他70岁大寿那天,有宾客问他:“你平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李小声说:“开一间小饭店,忙碌一整天,到晚上打烊后与老婆躲在被窝里数钱.”宾客大笑,李亦大笑.
就像一个“正午的小孩”,比尔·盖茨似乎从未背负人类的精神包袱,“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变得富有,这根本不是我的梦想,时刻激励着我向上的是一种创造与众不同的愿望.”“也许,人生就是一场正在熊熊燃烧的火灾,一个人所能做也必须去做的就是竭尽全力从这场火灾中抢救出一点什么.”
事实上,我们同样可以在中国的IT精英身上发现这种自由精神.丁磊就曾表示,“'网络首富'的称号,那只是创业过程中的副产品,包括其它名利等等.”“网易如果不成功,自己完全可以去搞唱片制作.”在陈天桥看来,“'爸爸'这个头衔,就比'首富'重要得多.”张朝阳不仅追求 Hip-Hop青春形象,甚至还要“把20岁再重新过一遍”,自由意味着工作与生活的合二为一,“我去酒吧蹦迪和我做商业决策之间是有关联的”……
纪伯伦有诗云,“生活的确是黑暗的,除非有了渴望;所有渴望都是盲目的,除非有了知识;一切知识都是徒然的,除非有了工作;所有工作都是空虚的,除非有了爱;当你们带着爱工作时,你们就与自己、与他人、与上帝合为一体.”然而,对于大多数疲于奔命、“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中国商人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种饥饿感驱使下的幸存者哲学代替了对于商业意义的真正思考.今天的中国,既没有共同的情感,甚至也没有共同的时尚.就像托马斯·卡莱尔所说的,金钱是这个社会唯一的连接点.在创造了一个日益丰沛的物质世界之后,我们却未能创造相应的精神世界.类似的贫困同样体现在素有“经济动物”之称的日本人身上.管理专家汪中求在日本考察时就听到一位日本朋友说:“日本人不做梦,哪有时间做梦!”如果说在“美国梦”的语境中,人生被定义成“为了梦想和兴趣而展开的表演”,那么,从未有一个“日本梦”像“美国梦”那样具有灵魂性的感召力.
“假定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没有大规模的人口增长,那么'经济问题'将可能在100年内获得解决,或者至少是可望获得解决.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展望未来, 经济问题并不是'人类的永恒问题'.……因此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是凭我们的天性—包括我们所有的冲动和最深层的本能—都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而进化发展起来的.如果经济问题得以解决,那么人们就将失去他们传统的生存目的……”(《预言与劝说》)凯恩斯的忧虑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也许仍显超前,但总有一天它将成为人们绕不过去的问题.
“每一代人都需要新的革命”
台湾作家龙应台早年留学美国,看到美国的年轻人昂首阔步、轻轻松松地面对每天升起的太阳,不胜感慨:“这样没有历史负担的人类,我不曾见过,我,还有我这一代人,心灵里的沉重与激越,是否有一个来处.”今天,30年“改革下的蛋”已经孵化,“中国的青春痘”们正在出场.在他们的脸上,你看不到历史的沧桑、悲情与重负.作为这个古老国度的异质性“增量”,假以时日,在引领21世纪中国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新生活风尚的同时,他们可能在根本上重塑这个国家的性格,创造一个名副其实的“新新中国”!
有人不无形象地将今天的中国社会比作一台电视节目:1960年代以前生人做总制片和审片人,1960年代生人做编导,1970 年代生人做主持人,1980年代生人做嘉宾,而观众席上坐着的是没有及时“出人头地”的各个年代生人.“80后”们的崛起,颇似《大未来》作者托夫勒所告诫的:“有些趋势汹涌而来,在你还没看清楚之前,就已让你灭顶.”这是深具“DIY精神”的“我一代”:他们信奉 “我的地盘我做主”、“做最好的自己”、“大狗小狗都要叫”,他们相信“每一代人都需要新的革命”(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语),发誓要让“前浪死在沙滩上”,他们熟稔“成名要趁早”,试图“打破一切常规”、“重估一切价值”,希望“2年内取得20年的经验”,并略带“不屑”地回应那些自称“我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认为他们“还太嫩”的人:不少号称拥有20年经验的人,其实不过是一年经验的20年简单重复.他们相信“一切皆有可能”,这个正进入“后喻”时代的世界归根结底是他们的,历史将按他们的方式改写,光荣自然“属于我们八十年代(出生)的新一辈”.
与王石们的社会大学、张朝阳们的“常春藤”相比,在他们眼里没有比互联网更好的大学—足不出户,即“读天下书、行万里路”.与前辈们动辄十万百万的“第一桶金”相比,他们几乎是零成本创业:一台电脑、一根网线、一个脑袋,就是全部.他们不知“红帽子企业”为何物,亦无需再像前辈那样“忍耐了很多很多常人无法忍耐的东西,隐藏过按常例不应隐藏的黑暗,为他人背过的黑锅也历历可数”,同时也面临更纯粹、更严酷的市场考验.与所谓“不落空”阶层相比,他们没赶上下海热、房地产热、股票热、MBO热、新经济热,一位自认是“最吃亏的一代”的80后创业者抱怨道:“他们指责80代想一夜成名,但是除了'一夜成名'还有什么其他机会?”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他们不热衷于宏大叙事,对自己“处于何种历史地位”这样的问题毫不敏感,他们也不复有“产业报国”的宏愿,甚至也没有 “留下一串对后人富有建设意义的脚印”(王石语)式的使命感.他们试图“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与前辈“怪杰” 们相比,这些中国版的“极客”们似乎更倾心于美国领导学泰斗沃伦·本尼斯所描述的那种生活,“创业就像远足、泛舟、骑登山脚踏车及滑雪一样,成为年轻人的消遣,让他们相信自己无所不能,并了解到自己生活在无前例可循的世界.”他们试图证明:商业原来是可以更美的!
不过,在叛逆的外表下,他们尚有待证明自己拥有真正的颠覆性力量.在将“年轻,就是一切”的宣言挂在嘴边的同时,也不妨听听 “老邦菜”王朔的“风凉话”:“有人没年轻过,没人没老过”,“基本不构成力量,基本是泡沫,基本上没有形成战斗力”(尽管这本是针对文学而言的).在梦想“飞得更高”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历史没有飞跃”(马歇尔语),“奇迹”的光芒背后往往是琐碎的商业细节,“在一个管理好的企业内部没有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张瑞敏语).前辈王石在对(“80后”创业者)这些“超级男生”寄予厚望的同时也不失理性地指出:“要现在就定义为'未来中国商业的脊梁'显然为时尚早”.“老是那几个人在说话,他们说完了好像行业的大事就定了.他们代表了昨天,能代表明天吗?”在他们之前,孙宏斌,一条地产界的“鲇鱼”,一个发誓要“让世界重新走出旧规”的咄咄逼人的挑战者,最终却因自己凌空蹈虚的躁动成了“昨天的代表”.当然,他其实并未失败,而且也的确给这个圈子带来了震撼,并仍有机会再起.(余华曾经说过,“在一个作家没有到达80岁之前,不要轻易给他下判断”,其实这同样适用于企业家.老骥伏枥,尚志在千里,想想和田一夫吧.)
他们不再“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平庸和无聊”(余华语)式的“活着”,却可能陷入另一种 “一心要过别人的生活”的不自信与“单向度”消费主义的贫困.“未来之路”依然迷茫,他们却已找不到“回家的路”,因而注定将是无根的“漂一代”!印度诗哲泰戈尔有诗云:“黄昏时的树影拖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你无论走得多么远也不会走出我的心.”如果将比尔·盖茨的创富神话比作“盛夏的果实”,那么美国精神无疑就是树根!可口可乐公司总裁曾表示,即使公司的物质资产毁于一旦,仍可借品牌迅速崛起.“资源是会枯竭的,唯有文化才会生生不息”,如果说任何商业都基于一定的生活方式,那么如何在传统的废墟上建立现代商业大厦?伴随这一代人中国意识的觉醒,中国的崛起和复兴背后又孕育着什么样的文化信息?
1998年6月,中国互联网的启蒙者张树新黯然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瀛海威公司:“现在回过头看,瀛海威不幸生得太早.”正如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前言中所言:“每一代人都学会了他们要扮演的最后角色,无非是当下一代人进门前用脚踩踏一下的垫子;这也是值得和应尽的义务.”
预测未来是困难的.1978年,中国的改革刚刚拉开序幕,而在大洋彼岸,比尔·盖茨首次见到葛鲁夫,当时微软只有11个人,而英特尔已是万人大公司,他们不知道未来“Wintel”联盟将主宰一个时代.1984年,正是中国的企业元年,当柳传志信誓旦旦地表示“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时,肯定想不到这家曾卖过电子表、旱冰鞋,“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的名叫“联想”的小公司,20年后竟收购了IBM 的PC业务,成为年营收千亿的跨国公司.而当年声名显赫的“两通两海”中名实尚存的四通,却成了一家“谁都知道但谁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公司”.
中国的比尔·盖茨将在现有企业家群体中产生还是尚在摇篮中?谁也给不出答案.不过我们也许能从全球风险投资界“国王”迈克尔· 莫瑞茨的一番话中得到些许启发:“虽然我们在中国已经看到了很多成功的企业,但如果过50年、100年以后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会觉得现在的企业只是微型的,很有可能,很多伟大企业的创始人现在还没有出生呢.”
是的,“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Let's begin now!
不必沮丧,不必恼怒,毕竟,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比尔·盖茨,准确地说应该是:我们为什么成不了比尔·盖茨?
“开什么国际玩笑,我一个连住房按揭都还不过来的'月光族',还比尔·盖茨呢!”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只能说明你在思维上与比尔·盖茨相差一光年,比财富上的距离还远—是的,正如巴拉昂秘诀所揭示的,你缺乏野心!
比尔·盖茨的偶像、世界上第一个亿万富翁洛克菲勒曾豪言:“如果把我剥得一文不名丢在沙漠的中央,只要一行驼队经过—我就可以重建整个王朝.”世界旅馆业大王康拉德·希尔顿则表示,当他潦倒困顿到必须睡在公园的长板凳上时,他已经知道自己以后将会成功.这就是野心的力量!
比尔·盖茨自然是幸运的:他自己亦坦承,如果王安能完成他的第二次战略转折,世界上可能就没有今日的微软,“我可能就在某个地方成了一位数学家,或一位律师”,此乃天时;微软公司创办25周年之际,《今日美国报》记者问他对美国政府决定分割微软的看法,他回答说:“撇开这宗诉讼不谈,这仍是一个利于创业的伟大国度.我对这个国家的感激,远胜于这宗针对我们的官司.”比尔·盖茨本人无疑是“美国梦”的最佳诠释.此乃地利;更关键的是,他在选择学校、专业乃至选择退学上最终都得到了父母的理解和支持,他担任IBM董事的母亲“以自己的成就和人格为我的爱子作最好的担保”帮助初创的微软获得了至关重要的第一份商业合约,而其身为知名律师的父亲亦在商务处理方面颇多助力,此乃人和.
除了天时、地利、人和,最重要的,当然仍是天才企业家的个人禀赋.《影响历史的商业七巨头》一书的作者、哈佛商学院教授理查德 ·泰德罗就认为:“这本书里的主人公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教育的”.甲骨文CEO拉里·埃里森甚至声称:“一顶帽子一套学位服必然要让你沦落……”伟大的企业家没有一个是读出来的,他们总是创造或改写商学院案例,而非学习案例.“有能力把自己写进艺术史的人,不会做一个评论家”,尽管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 这一论断在某种意义上同样适用于企业家.德鲁克就说过:“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在于成果.”
1975年,就在比尔·盖茨创立微软的同时,同年出生的史蒂夫·乔布斯也在车库里创立了苹果电脑.随着公司的成功上市,25岁的亿万富豪乔布斯亦成了全美年轻人的偶像.然而,今天盖茨的个人财富(约600亿美元)却整整超出乔布斯几十倍.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就在电脑还是摄影棚似的“巨无霸”时,盖茨已认定基于小型个人电脑的软件才是未来趋势.这样的洞察力只能源于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商业本能.商人同样怕入错行,无论如何卓尔不凡,我们都无法想象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会成为今天的全球首富,这是其传统媒体的行业属性决定的,与企业家个人的才华与努力无关.
仅有远见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行动.“于尚未开始的领土,不可能有一副可靠的地图”,仅从《大众电子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比尔 ·盖茨就敏锐地意识到这将是一片“流淌着奶和蜜”的商业新大陆.他没有迷恋于哈佛的光环,而是当机立断选择辍学创业,这是一个近乎赌注的商业决断,也许是商业史上“最伟大的放弃”之一.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混沌理论”同样适用于商业领域.事实上,当年比尔·盖茨曾与一位叫科莱特的哈佛同学商议一起退学去开发 32Bit财务软件,科莱特却委婉地拒绝了.1995年,已拿到博士后学位的科莱特认为开发32Bit财务软件的条件已成熟,比尔·盖茨却绕过Bit系统,开发出比它快1500倍的Eip财务软件,在两周内占领了全球市场,并在这一年成了全球首富.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关键处却只有几步.”想想格雷的教训吧:这位与贝尔几乎同时发明电话的技术天才,只因申请专利晚了两小时而黯然出局,而贝尔则成了商业巨子.是的,短短120分钟,就决定了命运的巨大分野!这是商业残酷的一面,也是其魅力所在. “我花了整个上午校对一首诗,把一个逗号删掉了;到了下午,我又把逗号放了回去”(王尔德),与追求不朽经典的文学相比,强调行动哲学的商业更像“遗憾的艺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你如果非得坚持将商业计划书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推敲无误后再去实施,机会女神可能早已溜走.从MS-DOS到Windows Vista,微软从不奢求完美,有的只是“我们一直在努力”.
无独有偶.当年与丁磊同时进宁波市电信局的大学生有52个,但走出来的,至今只有他一人.后来他这样回忆道:“这是我第一次开除自己.人的一生总会面临很多机遇,但机遇是有代价的.有没有勇气迈出第一步,往往是人生的分水岭.”当年陈天桥从一家企业跳槽,公司挽留他“等分了房子再走吧”,他却不为所动: “难道我这辈子自己还挣不了一栋房子?”后来他曾自我评价道:“我的心理从小就愿意承受风险,我是一个大赌、大输、大赢的个性.”曾以杨振宁、陈景润为偶像,“理想是关在只有一盏小煤油灯的屋子里解数学题,一整天只吃一个冷馒头”的张朝阳则表示,“在决定经商之前,早已放弃了诺贝尔物理学家的梦想”.“不要问现在加入商战是否太晚,按照现在信息经济的发展速度,谁又能够承担不参战的责任呢?”1999年,李彦宏毅然启程回国创业.
放弃是困难的,无论是一个金饭碗、一套即将到手的房子还是曾经的理想…….“对于无产者来说,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一个已有清晰人生图景的中产者,为何还要投身于巨大的不确定性中?于是,太多的人在患得患失中坐失良机,太多的人满足于饭桌上的高谈阔论却从未想过付诸实施.这也许就是许多巨富都出身赤贫的原因所在.在某种程度上,埃里森的“蛊惑”不无道理:“离开这里.收拾好你的东西,带着你的点子,别再回来.退学吧,开始行动.”除了行动,你别无选择!
仅有天才的idea是不够的,你还得有执行力:资源整合的能力、团队合作的能力、危机处理的能力…….有时候,起得早不如赶得巧,栽苹果树的未必能吃上苹果.生产出第一台电脑的苹果公司,最终却被挤出计算机主流企业之列,乔布斯自己也一度被炒了鱿鱼.陈春先,这位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营科技机构的“中关村第一人”一生始终难以跨越技术与商业的鸿沟.
运气的因素永远不可忽略.人生有太多的偶然性,智力从来就不是商业成功的充分条件.事实上,真正的“DOS之父”很早就在一场酒吧斗殴中丧生.一位著名风险投资人曾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他们所投资的一家公司,创业者各方面都很优秀,就是喜欢飙车,结果死于一次车祸.在孙宏斌看来,无论是丘吉尔、罗斯福还是杨致远,他们的成功其实都源于某种风云际会的因素,“一下子,偶然的一下子……”,对于那场深刻改变了自己人生轨迹的牢狱之灾,他亦有独特理解:“没有那样的经历也许你没有今天这样的成长或者成就,你就是联想的一个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就是中关村一个小公司.”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即使你身上已具备几乎所有成功因子,一个关键性意外就足以让你功败垂成.即使你拥有比尔·盖茨式的天才,由于“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你仍无法复制他的成功.
“伟大是熬出来的”.事实上,即使是那些今天看来堪称伟大的公司,也并非一贯高瞻远瞩,在其成长史上同样不乏试错、机会主义、太多的踉踉跄跄和“差点死掉”.最富戏剧性的也许当数美国联邦快递公司的创始人弗雷德·史密斯,一次他靠在拉斯维加斯玩二十一点纸牌赢得的27000美元支付了员工工资…….虽然 “成功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难”,但也绝非地摊励志书说的那么简单.张朝阳曾以“惊弓之鸟般的等待”形容筹措第一笔风险投资的艰辛,陈天桥则坦承“一年里承担了别人十年的风险”、“半夜醒来一身冷汗”,腾讯CEO马化腾在最艰难时甚至曾计划以100万元将QQ转让,却被认为“开价过高”谈不拢而告吹……
在这个十倍速时代,你得时刻谨记“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在这个天才辈出、声称“35岁就退休”的“挨踢”业,你得时刻“保持饥饿,保持愚蠢”; 你得面对埃里森这样的“硅谷坏小子”发出的成吉思汗式的“咆哮”:“仅仅成功是不够的,其他人必须失败.”你得面对旷日持久的可能法律诉讼…….与杰克· 韦尔奇宣称的“商业就是生活,是每天我们都想打赢的一场游戏”的洒脱相比,现实也许更接近泰德罗对柯达公司创始人乔治·伊士曼的评论:“我不愿意说他爱的是生意本身,生意意味着战争.生意意味着冷酷无情,生意是伊士曼生活中黑暗的一面.”或是泰德罗在《IBM王朝》中向你揭示的:伟大的“Think”背后伟大的不择手段.
现在,问题变了:你还愿意成为比尔·盖茨吗?
什么都有代价.商业价值与文化理想间永远都有矛盾.与西装革履的比尔·盖茨相比,更富反叛色彩的乔布斯被视为全球最酷的企业家,他是IT界的时尚先生、商业领域的艺术家,甚至,硅谷的精神领袖.当然,对应的是,他永远也无法成为全球首富.莫非这就是商业领域的“政教分离”?
哈耶克认为,一个“伟大社会”应鼓励一切个体在一切可能的方向探索.正如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独一无二的你,DIY自己的人生吧.即使在比尔·盖茨面前,你也无须自惭形秽,只要你心中仍有爱、诗意与梦想.想想莫利(C.Morley)的话吧:“只有一种成功,那就是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好了,现在,让我们回到正题—
中国的比尔·盖茨,
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2006年美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约26.7%的被调查者认为下一个比尔·盖茨最可能出自中国.2007年4月比尔·盖茨第十次访华时亦预言:下一个伟大的成功将会来自亚洲.英国卡斯商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全球45岁以下最年轻有为的前10名CEO中,有8名来自中国.“下注中国”,这是2006年美国《巴伦周刊》给出的口号.2007年初的《时代》周刊以《中国世纪》为封面故事.高盛的一份报告指出,35年后中国将成全球第一经济体,而美国则仅列第三…….正如比尔·盖茨所指出的:“一个人拥有的机会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在哪个国家所决定的.”无论这些分析充满多少溢美之辞,至少在宏观上预示了下一个比尔·盖茨的可能.
德鲁克认为,一个时代、一个区域的社会类型可以从其“首富”的特征中直观地获知.放眼全球,与GOOGLE财富神话相映成辉,印度的钢铁大王、墨西哥的电信巨头及中国的地产大亨,这些新一代的洛克菲勒们正试图利用全球资本市场完成整合传统行业的“炼金术”.对于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并存、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复合”转型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来说,“饲料首富”、“钢铁首富”、“房地产首富”、“软件及互联网首富”等完全可能同时涌现. 由于后发优势,互联网正是中国少数完全与国际接轨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这无疑为中国的比尔·盖茨的出现奠定了产业基础.
资金并不是真正的问题.盛大网络崛起后,一家国际风险投资机构的中国区负责人批评其下属:你身在上海,为什么没有发现盛大?在资源与市场都日益全球化、流动性泛滥的今天,“世界是平的”,真正稀缺的并不是资本,而是创新.
创新对于企业家来说永远是第一位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有“一俊遮百丑”之效.正是创新,让当年的乔布斯一不小心成了“暴发户”,美国航天工业巨子休斯公司的副总裁艾登·科林斯慨叹道:“我们就像小杂货店的店主,一年到头拼命干,才攒那么一点钱,而他几乎是一夜之间就赶上了.”
也正是创新,才是我们的最大软肋:无论是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还是管理创新…….除了缺乏核心技术,我们亦从未出现类似福特流水线、通用事业制度、丰田生产方式、连锁店这种级别的组织创新.即使是互联网领域,成熟的商业模式也大多拷贝自美国.英特尔董事长安德鲁·葛鲁夫曾断言:华人对财富几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创造力,但对组织的运作似乎缺乏足够的热情与关注.WTO前总干事穆尔甚至认为:中国企业的管理相当于30年前的日本,相当于100年前的英国.
当中国的IT精英们在很大程度上因受惠于NASDAQ的“中国溢价”因素而获得个人财富的“爆米花效应”时,也许有必要重温一下戴尔在总结自己“如何管理 30亿美元的公司”时说的话:“大多数公司的发展和成熟的脚步都比我们慢许多,但他们在规模尚小的时候所学到的基本程序,我们这时候必须回头认识.”
对于巨额财富,黄光裕直言“没感觉,假如你在不停地发展自己的事业,那么它就不是财富;如果停下来了,它或许是.但最大的可能是,今天你一无所有,但明天你什么都有了,而后天你又回到了起点.”作为“剩者为王”的马拉松而非百米冲刺,商业更需要“韧的战斗”.中国从来就不乏“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明星企业, 不乏“增长速度回落到400%”式的狂飙突进,惟独缺乏基业长青的百年老店!“涨潮的时候,看起来所有的人似乎都在游泳,一旦退潮,谁没穿衣服便一目了然.”与GE这样的百年老店相比,还没有哪家中国企业经受了完整经济周期的洗礼.正如任正非在考察了连续十年经济衰退的日本之后写下的那篇著名的《北国之春》所说的:“什么叫成功?像日本企业那样,经九死一生还能好好地活着,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华为没有成功,只是在成长.”与比尔 ·盖茨连续12年蝉联全球首富的记录相比,不断刷新的“中国首富”既是活力的象征,也寓示着脆弱和不确定性.
谁扼杀了我们的创造力?
曾任美国总统的艾尔文·柯立芝有句名言:“美国的事业是企业”.今天的中国却出现了公务员热.即使是在以个人创业精神著称的温州,那句“再不好好学习长大了就当干部”也早已变成了“好好读书长大了好当干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一个事实是:1999年至2004年6年间全国个体户净 “缩水”810万户.除了结构升级因素外,创业环境不尽理想应是主因.
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世界银行的教授对85个国家和地区所作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从申请注册公司到开业,加拿大只需2天,中国内地需111天;再来看注册资本(以股份有限公司为例),中国内地为1000万元人民币,日本约为82万元人民币,美国则为零.另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07全球商业环境报告》,在全球商业运营活动的便利性排名中,中国位居175个经济体中的第93位.
“春江水暖鸭先知”,对于创业环境,一线的企业家们最有发言权.柳传志曾以“孵小鸡”为比喻形象地诠释“市场温度”的变化.史玉柱曾对媒体叹苦:“我随便写了民营企业的15个死法,随便一条就能把你搞死……我觉得我们比下岗工人更苦.”更有甚者,据说亚都公司CEO何鲁敏的办公桌边放着一个小包,毛巾、牙刷都准备好了,“如果来抓我,我随时都可以跟着走.”让何颇为感慨的是,他在美国时发现:在一些大家聚会的会所,或者咖啡馆里,有人吃饭、喝咖啡是不花钱的.仔细一打听,才知道那就是失败的企业家.在中国,企业家一旦失败,面临的更可能是“以落井下石的火力一夜间摧毁被它们吹捧了几年的企业”的舆论环境.
不妨进一步设想一下:我们未来的比尔·盖茨的街头小贩创业实践会不会被城管扼杀在摇篮中?与硅谷的车库创业文化相比,在一刀切式的“民宅禁商”政策下,北京、上海那些刚起步的小公司,会不会因寸土寸金的高昂房租而倒下?公司稍有规模,面对形形色色的“赞助”电话,你如何说 “不”?面对工商联副主席或政协副主席的可能邀请,会选择“商而优则仕”吗?……
鲁迅先生早就强调过“做土”的重要性:“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正是由于创业环境的差异,硅谷的创新型公司在风险资本的“催肥”下迅速成长为参天大树,而中国一些颇有潜质的中小企业却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成了“小老树”.
《基业长青》和《从优秀到卓越》的作者吉姆·柯林斯认为:“人类历史上,一些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发明其实并不是技术或产品,而是社会发明.试想一下美国宪法、货币或者市场机制等概念的诞生.它们永远都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创造.”就此意义而言,在期待中国的微软之前,我们也需要中国的摩根斯坦利、中国的华尔街日报、中国的麦肯锡、中国的奥美等商业支撑体系,同时更需要自由市场、法治等社会支撑体系!
“创意创造生意,想象力创造利润率”,在一个内心荒芜的时代,曾经的诗人江南春转而向商业世界寻求诗意.可是,我们的头脑早就被格式化了,还能有什么想象力与创造力?
“《易经》里没有强大的秘诀,《庄子》里没有自由的路径,《资治通鉴》中找不到民主人权的旗帜,《论语》里也没有宪政的痕迹,要去《尚书》中发现共和同样只会是无益的徒劳,而秦皇汉武们留下的只有奴役和专制.”在学者黎明看来,自2000多年前的秦政,中国人就已失去想象力了.
杨振宁教授曾提出一个观点:创新可分为爱因斯坦、杜甫、比尔·盖茨和任天堂四种体系,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盖茨和任天堂,暂时拿一两个诺贝尔奖并没有什么用处.其实,科学、人文、商业之间本就相通并互为促进,对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来说,比尔·盖茨、任天堂与爱因斯坦、杜甫或可并存.美国学者波特的一个观点早已被广泛认同: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最难替代和模仿、最持久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很难想象,一个在文化上未有丰富创造的国家,能实现真正的“崛起” 和“复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认为: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正如知名青年评论家许知远所言:我们期待一个真正的社会精英群体的出现……按照20 世纪50年代那个充满激情的个人主义者爱因·兰德的说法,“他们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是文艺复兴之父,是工业革命之父,是科学之父,是个人主义之父,是资本主义之父……”
教育部部长周济曾坦承,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不足是中国教育的致命缺点.张朝阳回忆起当年水木清华的校园生活时仍不胜感慨:“被伤着了”,“不停地比,比谁的作业先完成,谁学习的时间最长……整个小社会只提供给你一种可能性……”自认“(大学时代)不是个好学生,上课总拣'偏远地区'坐下”的丁磊曾表示,当下大学生的知识结构还不具备一毕业就创业的条件,这是我们的教育体制所造成的.在《中国企业家》采访的10多位“80后”创业者中,许多人都从未在传统教育体制内获得肯定.《南方周末》曾报道当年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神童”宁铂出家的新闻,他这样抱怨:“'神童'剥夺了我许多应该享有的生活和娱乐的权利”……
作为“80后”的PCPOP网CEO李想来自一个环境宽松的家庭,“我小学时父母给的是命令,初中时给的是建议,高中时是从朋友的角度提出参考,到了高中以后就是信任了.”比他年长一些的创业者则没有那么幸运:丁磊当年从宁波市电信局辞职,就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我父亲总是打击我”,江南春的父亲是一位审计师,推崇稳健、平淡的生活,至今他对儿子的人生观念还是不大认同;曾梦想成为“中国的微软”的科利华公司的总裁宋朝弟 600元的创业资金是向家里要的,“我不敢说生意,他要让你当教授,走正道.做生意那不是白培养你了吗?”……
在一些家长眼里,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孩子成了没有生命的石头,在自己并不高明甚至拙劣的手艺下,天才的棱角被“打磨”殆尽.鲁迅先生曾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呼吁解放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 “伤仲永”式的“捧杀”与“耳光教育”式的“棒杀”仍时有所闻.
谁妨碍了我们长大?
“在中国,社会对企业家的期许,以及这个财富群体的自我膨胀即将达到顶点.”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他《被夸大的使命》一书中说.在并不漫长的中国当代商业史上,许多声称要做“中国的微软”、“中国的IBM”、“中国的GE”、“中国的松下”、“中国的索尼”、“中国的麦当劳”、“中国的可口可乐”、“中国的八佰伴”、“中国的巴菲特”、“中国的索罗斯”……乃至“真正的世界级企业家”的人都纷纷倒下了.为什么比尔·盖茨和他的微软帝国能在30年的跨度里 “每一次我们都经受住了考验”?
商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场与人性间的战争.正如一位企业家所言:“在任何时候,人,都是输给自己的.”张树新,这位“可以把读哲学当作休息”的企业家,曾这样反思道:“每个人都有误区,总是认为自己不可以被别人替代.”在有“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传统、“一年合伙,二年红火,三年散伙”的中国商界,你能找到一位像保罗·艾伦那样甘当“绿叶”、几十年默契如初的绝佳拍档吗?大多数成年人都能顺利爬上香山,但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成功登顶珠峰.不少温州商人在资产过亿后欲再攀高峰,却纷纷遭遇“高原反应”.在温州有这样一个说法:“即使你做了微软的CEO、IBM的总裁,都不如做一个小卖部的老板'值钱'”.如果并购重组意味着自我退出,对于视企业为“己出”的企业家来说,这不啻为自我宣战!“万科不是我的儿子,他是我的作品.”像王石这样有着清醒认知的企业家毕竟太少.阿里巴巴CEO马云无疑是有大梦想的人,对他来讲,成为一个“伟大的公司”远比“一个人的帝国”更有意义,因而才有阿里巴巴与雅虎的合并.在马云看来,生意人是做买卖,商人有所为有所不为,企业家是影响一代人的生活,在中国80%是生意人.
迪斯尼无疑是“影响一代人的生活”的企业家的典范.是他以爱灌注了那些卡通精灵,“使千千万万的人们享受到了一种更光明、更快乐的生活.他所创造的真、美和欢乐是永世不朽的.”(美国前总统约翰逊语)柯林斯则将现代公司的意义提升到“社会发明”的新高度:“决不仅仅因为它是技术革新的源泉,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是连接市场机制与民主政治的桥梁.”在这个意义上,商业与公民社会间的价值链得以打通,也因此才可能出现德鲁克所说的“企业家社会”.
美国作家罗伯特·索贝尔认为:在每一个关键历史时刻,企业家既影响社会和经济变化的严酷无情的进展,同时又受这种进展的影响.段永基曾坦承:“中国的现代企业很难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建成—我们都是过渡性人物.”王石则曾不无悲观地认为:“我们儒家文化背景、小农经济操作方式,已经决定了我们的性格,包括我本人,是不适合搞全球大企业的.”“我们中国企业由盛至衰的周期也就是20年、25年吧.”著名学者秦晖认为:“就中国没有 Citizen而言,实际上我们都是农民”.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则认为:中国“入世心态”的超越方式仅仅是此世的“立德、立功、立言”,这使得中国企业家大凡有了些成就的总要去追求“济世”的功业,所谓“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他并表示,就我们尚未获得西方自启蒙时代开启出来的个体理性这个意义而言,我们都是难以自立的儿童.
心理学大师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决定着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这条无意识的河流.什么样的市场,造就什么样的企业家.“转轨+新兴”市场的独特成长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部分中国企业家“原罪”性的世界观和机会主义的方法论.盛田昭夫曾说过,“我们日本商人必须是两栖动物,必须在水中和陆地上生存.”反映了那一代日本企业家在日本与西方价值观之间的挣扎.在今天的中国企业界,你同样可以轻易发现前现代思维与后现代技术的碎片.杰克·韦尔奇自传与《曾国藩家书》、《胡雪岩》同步流行—“历史叙事”与“科学叙事”的分殊同样反映在畅销书领域.“振兴民族产业”的口号与具体经营中“冷酷打击,坚决消灭”的对手观可以并行不悖而不会有丝毫心理上的不安…….致力于中国企业史研究的吴晓波以极富传神的笔法描绘了一幅过去30年活跃于中国商界的族群的图像:“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博取.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捷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得他们能够拨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的不畏天命使得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的规则与准绳.他们的贪婪使得他们敢于采用一切的手法和编造最美丽的谎言.”尼采认为,人生必经“由骆驼至狮子而至婴儿”三阶段.在一些中国企业家试图像洛克菲勒一样成为市场上的“狮子王”时(其实更多的时候只能像土狼一样在全球产业链上吃点残羹冷炙,而狼性也已成为早期某些企业家的基因),他们却没有后者的清教传统,而曾经的 “骆驼”精神也早已不再,当然他们也没有像晚年的洛克菲勒那样进入“婴儿”般纯真状态的可能.
一代人的迷惘与凯恩斯的忧虑
2002年,麦克斯·拉夫琴(Max Levchin)这位硅谷最年轻的“王子”在将自己开发的电子支付系统Paypal卖给eBay之后,陷入了一生中最灰暗的日子:他花340万美元买了一幢山顶豪宅,却从未搬进去住过一晚;他百无聊赖地骑车逛街,与女友厮混…….是的,退休太年轻了一些,当慈善家又坐不住.内心告诉他,必须重新找回创业的激情.于是,2005年他成立了自己的新公司Slide.曾有人问他干嘛这么拼命,他的回答是,“因为我觉得好玩.好玩,所以不想停下来”.在接受中国《财经》杂志记者采访时,他说:“定义一个大公司的成功,可以是'非常成功',但也可以是'比较成功',或'今年不成功明年成功',这只是程度的问题—不是那么关键性的成功.但是,创业很特别—不成则败.它就像赌博,让人兴奋.”
28岁的李嘉诚、30岁的陈天桥同样曾经历相似的迷惘.“就好像爬山,我已经爬到了顶峰,然后还有什么奔头呢?”而立之年即荣膺“中国首富”的陈天桥曾这样袒露心声.在搬到位于香港半山的新家的第一个夜晚,李嘉诚怎么也睡不着,整个晚上都在“痛苦和快乐的回忆中度过”.伴随“像火箭上升一样积攒财富”,一直忧心忡忡的日子终于彻底结束了,自己平生第一次可以放慢脚步思考人生的意义.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晚上,他常来到宝珊道上靠着路边的石头发呆.“财富能令一个人内心拥有安全感,但超过某个程度,安全感的需要就不那么强烈了.”他后来这样回忆道.
多年后,李嘉诚依然保持了早年的那种“饥饿”感.1999年,在完成“卖橙”(欧洲Orange电信公司)这一“世纪交易”的记者会后,他拿起一块饼干以充腹饥并奖励自己.就在前一天夜里,临睡前他特意将手机放在枕边,并将铃声调到最大,惟恐在睡梦中错失交易落实的喜讯.虽已富可敌国,却还这么“搏命”, 有谁能读懂这位华人首富的内心?
“如果看着比尔·盖茨的财富和你自己的距离那么大,那么你永远不会快乐.”说这话的人是李嘉诚,“我知足,但不表示没有上进心.”在他70岁大寿那天,有宾客问他:“你平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李小声说:“开一间小饭店,忙碌一整天,到晚上打烊后与老婆躲在被窝里数钱.”宾客大笑,李亦大笑.
就像一个“正午的小孩”,比尔·盖茨似乎从未背负人类的精神包袱,“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变得富有,这根本不是我的梦想,时刻激励着我向上的是一种创造与众不同的愿望.”“也许,人生就是一场正在熊熊燃烧的火灾,一个人所能做也必须去做的就是竭尽全力从这场火灾中抢救出一点什么.”
事实上,我们同样可以在中国的IT精英身上发现这种自由精神.丁磊就曾表示,“'网络首富'的称号,那只是创业过程中的副产品,包括其它名利等等.”“网易如果不成功,自己完全可以去搞唱片制作.”在陈天桥看来,“'爸爸'这个头衔,就比'首富'重要得多.”张朝阳不仅追求 Hip-Hop青春形象,甚至还要“把20岁再重新过一遍”,自由意味着工作与生活的合二为一,“我去酒吧蹦迪和我做商业决策之间是有关联的”……
纪伯伦有诗云,“生活的确是黑暗的,除非有了渴望;所有渴望都是盲目的,除非有了知识;一切知识都是徒然的,除非有了工作;所有工作都是空虚的,除非有了爱;当你们带着爱工作时,你们就与自己、与他人、与上帝合为一体.”然而,对于大多数疲于奔命、“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中国商人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种饥饿感驱使下的幸存者哲学代替了对于商业意义的真正思考.今天的中国,既没有共同的情感,甚至也没有共同的时尚.就像托马斯·卡莱尔所说的,金钱是这个社会唯一的连接点.在创造了一个日益丰沛的物质世界之后,我们却未能创造相应的精神世界.类似的贫困同样体现在素有“经济动物”之称的日本人身上.管理专家汪中求在日本考察时就听到一位日本朋友说:“日本人不做梦,哪有时间做梦!”如果说在“美国梦”的语境中,人生被定义成“为了梦想和兴趣而展开的表演”,那么,从未有一个“日本梦”像“美国梦”那样具有灵魂性的感召力.
“假定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没有大规模的人口增长,那么'经济问题'将可能在100年内获得解决,或者至少是可望获得解决.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展望未来, 经济问题并不是'人类的永恒问题'.……因此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是凭我们的天性—包括我们所有的冲动和最深层的本能—都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而进化发展起来的.如果经济问题得以解决,那么人们就将失去他们传统的生存目的……”(《预言与劝说》)凯恩斯的忧虑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也许仍显超前,但总有一天它将成为人们绕不过去的问题.
“每一代人都需要新的革命”
台湾作家龙应台早年留学美国,看到美国的年轻人昂首阔步、轻轻松松地面对每天升起的太阳,不胜感慨:“这样没有历史负担的人类,我不曾见过,我,还有我这一代人,心灵里的沉重与激越,是否有一个来处.”今天,30年“改革下的蛋”已经孵化,“中国的青春痘”们正在出场.在他们的脸上,你看不到历史的沧桑、悲情与重负.作为这个古老国度的异质性“增量”,假以时日,在引领21世纪中国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新生活风尚的同时,他们可能在根本上重塑这个国家的性格,创造一个名副其实的“新新中国”!
有人不无形象地将今天的中国社会比作一台电视节目:1960年代以前生人做总制片和审片人,1960年代生人做编导,1970 年代生人做主持人,1980年代生人做嘉宾,而观众席上坐着的是没有及时“出人头地”的各个年代生人.“80后”们的崛起,颇似《大未来》作者托夫勒所告诫的:“有些趋势汹涌而来,在你还没看清楚之前,就已让你灭顶.”这是深具“DIY精神”的“我一代”:他们信奉 “我的地盘我做主”、“做最好的自己”、“大狗小狗都要叫”,他们相信“每一代人都需要新的革命”(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语),发誓要让“前浪死在沙滩上”,他们熟稔“成名要趁早”,试图“打破一切常规”、“重估一切价值”,希望“2年内取得20年的经验”,并略带“不屑”地回应那些自称“我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认为他们“还太嫩”的人:不少号称拥有20年经验的人,其实不过是一年经验的20年简单重复.他们相信“一切皆有可能”,这个正进入“后喻”时代的世界归根结底是他们的,历史将按他们的方式改写,光荣自然“属于我们八十年代(出生)的新一辈”.
与王石们的社会大学、张朝阳们的“常春藤”相比,在他们眼里没有比互联网更好的大学—足不出户,即“读天下书、行万里路”.与前辈们动辄十万百万的“第一桶金”相比,他们几乎是零成本创业:一台电脑、一根网线、一个脑袋,就是全部.他们不知“红帽子企业”为何物,亦无需再像前辈那样“忍耐了很多很多常人无法忍耐的东西,隐藏过按常例不应隐藏的黑暗,为他人背过的黑锅也历历可数”,同时也面临更纯粹、更严酷的市场考验.与所谓“不落空”阶层相比,他们没赶上下海热、房地产热、股票热、MBO热、新经济热,一位自认是“最吃亏的一代”的80后创业者抱怨道:“他们指责80代想一夜成名,但是除了'一夜成名'还有什么其他机会?”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他们不热衷于宏大叙事,对自己“处于何种历史地位”这样的问题毫不敏感,他们也不复有“产业报国”的宏愿,甚至也没有 “留下一串对后人富有建设意义的脚印”(王石语)式的使命感.他们试图“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与前辈“怪杰” 们相比,这些中国版的“极客”们似乎更倾心于美国领导学泰斗沃伦·本尼斯所描述的那种生活,“创业就像远足、泛舟、骑登山脚踏车及滑雪一样,成为年轻人的消遣,让他们相信自己无所不能,并了解到自己生活在无前例可循的世界.”他们试图证明:商业原来是可以更美的!
不过,在叛逆的外表下,他们尚有待证明自己拥有真正的颠覆性力量.在将“年轻,就是一切”的宣言挂在嘴边的同时,也不妨听听 “老邦菜”王朔的“风凉话”:“有人没年轻过,没人没老过”,“基本不构成力量,基本是泡沫,基本上没有形成战斗力”(尽管这本是针对文学而言的).在梦想“飞得更高”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历史没有飞跃”(马歇尔语),“奇迹”的光芒背后往往是琐碎的商业细节,“在一个管理好的企业内部没有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张瑞敏语).前辈王石在对(“80后”创业者)这些“超级男生”寄予厚望的同时也不失理性地指出:“要现在就定义为'未来中国商业的脊梁'显然为时尚早”.“老是那几个人在说话,他们说完了好像行业的大事就定了.他们代表了昨天,能代表明天吗?”在他们之前,孙宏斌,一条地产界的“鲇鱼”,一个发誓要“让世界重新走出旧规”的咄咄逼人的挑战者,最终却因自己凌空蹈虚的躁动成了“昨天的代表”.当然,他其实并未失败,而且也的确给这个圈子带来了震撼,并仍有机会再起.(余华曾经说过,“在一个作家没有到达80岁之前,不要轻易给他下判断”,其实这同样适用于企业家.老骥伏枥,尚志在千里,想想和田一夫吧.)
他们不再“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平庸和无聊”(余华语)式的“活着”,却可能陷入另一种 “一心要过别人的生活”的不自信与“单向度”消费主义的贫困.“未来之路”依然迷茫,他们却已找不到“回家的路”,因而注定将是无根的“漂一代”!印度诗哲泰戈尔有诗云:“黄昏时的树影拖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你无论走得多么远也不会走出我的心.”如果将比尔·盖茨的创富神话比作“盛夏的果实”,那么美国精神无疑就是树根!可口可乐公司总裁曾表示,即使公司的物质资产毁于一旦,仍可借品牌迅速崛起.“资源是会枯竭的,唯有文化才会生生不息”,如果说任何商业都基于一定的生活方式,那么如何在传统的废墟上建立现代商业大厦?伴随这一代人中国意识的觉醒,中国的崛起和复兴背后又孕育着什么样的文化信息?
1998年6月,中国互联网的启蒙者张树新黯然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瀛海威公司:“现在回过头看,瀛海威不幸生得太早.”正如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前言中所言:“每一代人都学会了他们要扮演的最后角色,无非是当下一代人进门前用脚踩踏一下的垫子;这也是值得和应尽的义务.”
预测未来是困难的.1978年,中国的改革刚刚拉开序幕,而在大洋彼岸,比尔·盖茨首次见到葛鲁夫,当时微软只有11个人,而英特尔已是万人大公司,他们不知道未来“Wintel”联盟将主宰一个时代.1984年,正是中国的企业元年,当柳传志信誓旦旦地表示“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时,肯定想不到这家曾卖过电子表、旱冰鞋,“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的名叫“联想”的小公司,20年后竟收购了IBM 的PC业务,成为年营收千亿的跨国公司.而当年声名显赫的“两通两海”中名实尚存的四通,却成了一家“谁都知道但谁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公司”.
中国的比尔·盖茨将在现有企业家群体中产生还是尚在摇篮中?谁也给不出答案.不过我们也许能从全球风险投资界“国王”迈克尔· 莫瑞茨的一番话中得到些许启发:“虽然我们在中国已经看到了很多成功的企业,但如果过50年、100年以后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会觉得现在的企业只是微型的,很有可能,很多伟大企业的创始人现在还没有出生呢.”
是的,“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Let's begin 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