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北教室的风筝 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上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篇文章,没想到,自己也成了当事人。。。。过了1年感觉像是过了3年
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我已经很老了吗?大人指着我,会对他的孩子说:“叫阿姨!”我难为情得不敢出声,因为我只是一个高中生。爸爸说,这是因为你的目光里有忧郁。我说,爸爸你知道这忧郁是从哪里来的吗?爸爸说,是因为数学。爸爸真知道我。我相信世界上比我爸爸更爱他女儿的不会有几个。可是我相信像他那样因为数学让女儿增添忧郁的也不会有几个。这写满我从小到大的记忆。他昨天晚上又这样了。我那张不及格的卷子被他扔得飞舞了起来。 正好那时黄晓俊打电话来。她是我音乐幼儿园的同学。她拉小提琴,我弹钢琴,在广元路那幢白颜色洋房里一起度过了音乐的三年。她说,她读到了我写的《音乐同学》,激动地给他们上音附中的同学这看,说:“这是我的同学写的!”我说:“是吗?”那时我在哭。她说:“你怎么啦?”“我数学不好。”“咦,你数学不是一直不好吗,有什么稀奇!”但是她不知道现在我的卷子正被扔得像风筝一样飞舞起来。她从来不哭的。小时候,她爸爸为了让她拉琴时手不瘪下去,做了个钢套戴在她手上,她也不哭。她爸爸还把电视机锁起来,钥匙藏在钢精锅里,她就四处找,在她爸爸还没下班时看动画片。上大班的时候她告诉我:“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干什么了吗?我把琴弦扔到窗口外面去了,我对我爸爸说,我不拉了!”我从那时候就佩服黄晓俊,她敢把琴弦扔到窗口外面去。可是她后来还是拉得很好,考进上音附中。 爸爸激愤了以后就出去散步了。他其实不是去散步,而是以这种方式来克制。他知道他如果不出去的话,激愤一定会更掀高潮。他出门的时候说:“对不起,我又态度不好了,出去走一走。”妈妈坐在那儿发呆。妈妈是个美丽又懦弱的人,遇到事情没有主见,她少女时丧父,青年失母,像一只孤独的鸟飞到爸爸身边,只要家里开开心心,她就异常异常满足,仿佛有了飞翔的树林。可是我偏偏数学不好。 我坐到妈妈的身边,靠着她。我不是一个善于把爱摆在脸上的女孩。心里是那么依恋父母,但是一句也不会说出来。这是不是就是长大的表现?但是同样是长大,别的女孩却照旧像童年一样甜蜜。爸爸妈妈生日的时候,我会精心挑选一张卡,但是我却要把那张卡放进楼下的信箱,觉得当着面让爸爸妈妈读到我那女儿语气的亲热祝福真不好意思。 妈妈轻轻地说:“繁繁,你数学怎么又不及格?”
“我想放弃。”
“放弃了那么考大学怎么办?”
是啊,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虽然我无数次想放弃,可是直到如今仍旧没有。我甚至星期天还到教育学院去补习数学。毛毛也去补。毛毛是一个属于天才型的女孩,会画画,数理化成绩年级总分第一,可是她也要去补。她报名迟了,位子在很后面,她就苦苦哀求老师让她坐在前在,说,“我个子矮,坐在后面怎么看得见呀。”老师见她着实可爱,就“灵活机动”帮她解决了。她甜蜜异常地说:“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其实都没有什么明显提高。但是让星期天这样度过会让人放心不少,爸爸妈妈的脸上也有笑容。听老师在上面讲的仍是些诸如此类的题目:某市商检局对35种商品进行抽样检查,鉴定结果有25种假货,现从这35种商品中任取3种,至少有两种假货的取法有几种?5名男生和两名女生站成一列,其中某男生必须排在中间,两名女生必须排在男生的后面,求不同的排法种数……这都是些我做过了一百道两百道的题目,明明觉得已经搞懂,但一面对卷子,就又完全没了记性,没了思路,没了逻辑,只有47分。
可我真不觉得自己是个木瓜脑袋,我的脑袋是在别的方面的。比如在文学方面。我不是仅仅可以和你聊聊《长袜子》、《马列耶夫》什么的,也可以聊《情人》和君特·格拉斯。数理化好的人都能顺畅地把《情人》读下来吗?可是我早就顺畅地读了。我还能背诵里面的段落。比如女孩和男人在湄公河渡船上的相遇。女孩乘了邮船的离去,那越离越远的岸和黑色长长的利穆新汽车。这时叙述变成了第三人称。她知道他在看她。她也在看他;她是再也看不到他了,但是她看着那黑色汽车急速驶去。最后汽车也看不见了。港口消失了,接着,陆地也消失了。还有很多年后他带着他的女人到巴黎给她打的电话。读着这些的时候我会流泪。我喜欢杜拉斯就是因为这些。也可以聊电影和戏剧。我甚至在班级里导演过《等待戈多》。只不过我做了一点改编,把戈多解释为不考试。可是怎么可能不考试?所以戈多怎么等得来?结果爱斯特拉冈和费拉季米尔只好用裤带上吊。爱斯特拉冈上吊的时候大喊一声:“我死得冤啊!”我把何中大骂一顿:“谁让你喊的!”爱斯特拉冈是何中演的……所以我难道也一定要把那么难的3件商品中至少弄两件假的出来之类的事情搞得那么熟练?它们完全可以让毛毛来弄,而让我兴致勃勃地来分析分析新浪潮的《最后一班地铁》。我把《最后一班地铁》借给毛毛看,毛毛说她看得想把自己掐死。我说,那么《罗生门》不借给你了,要不你更要把自己掐死。何中在边上叫起来:“千万别看,千万别看,什么玩意儿!”我说:“你才什么玩意儿!”
但是老师不同意。考大学的明文规定不同意。所以爸爸会把卷子扔得如同风筝飞舞。
我写了再多的文章登出来也没有用,一些老师总在办公室里说,她数学不好。他们甚至给我的同学的爸爸妈妈打电话也这么说:“她数学不好。”上一周李思哲就这样告诉我。他们的意思就是让李思哲别老跟我在一起。李思哲说,哎,按照这个逻辑,不就是说,教数学的老师不应该理睬教语文的老师吗?我们两个就大笑起来。其实那一刻我很想哭,心里特别感动,感动李思哲这样说。
我喜欢雷博。就是我们的雷校长。他是博士,所以我们都叫他雷博。他从来都是对我只有鼓励。我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我在电台当主持,我甚至在电视刊物上写很短的评论他都读到了。只要看见我,他老远地就会跷起大拇指,说:“真棒!”然后走过来拍拍我,问:“心情愉快吗?发挥自己的特长。”
这一刻我会不愉快吗?得到这样的鼓励。我甚至会愉快整整一天。爸爸说,有雷博这样的人做老师、做父亲真是幸福。
我在心里说,有你这样的爸爸也很幸福。爸爸把卷子扔得飞起来,那一次还打我耳光,这都不能怪他。他如果不爱我就不会这样。所以他听陈升的《风筝》会默默流泪。“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容易担心的小孩子/所以我将线交你手中却也不敢飞得太远/不管我随着风飞翔到云间我希望你能看得见/就算我偶尔会贪玩迷了路也知道你在等着我。”
我的脸肿着。那天我没有去上学,我准备晚上也不回家了。
我背着书包在马路上晃荡。书包里有《数学一课一练》、《数学同步练习》和厚厚的《五星级题库》……我不敢把它们扔掉,只能背着它们慢慢地走。我从小就背着它们走啊走啊,走了那么多路了。我不知道该走到哪里去。身上没有很多钱,不可以乱用,否则接下来怎么办?所以中午在大食代一圈又一圈地逛,最后还是没有坐下来,吃一份上海炒面或者是海鲜通心粉。我忧伤地想,我要流落街头了。在大千美食林门口的Jessica玉米铺买了一个烤玉米,就把中饭打发过去。中午的阳光很好,可是我心里没有一丝的明亮,一丝的快活。我拿着烤得金黄喷香的玉米在街上大啃大嚼。我是从来不在街上边走边吃东西的,觉得那样不好看。可是现在我是流浪汉了。我来到那幢白颜色的洋房前,站在马路对面看着它。那是一个多么小的小姑娘,永远睁着特别大的眼睛。每天总是好早就被妈妈拉着走上43路母婴车,妈妈说,今天好好练琴,不然晚上大灰狼要来找你的。她已经知道大灰狼是假的,所以睁着特别大的眼睛里不会有忧郁。可是现在有了。现在一切都不是假的了。数学不好,那就真的考不取大学,至少是考不取好的大学。爸爸的头发就是为此而白了。美丽的妈妈也憔悴了很多。可是她每天早晨还是要洗一个苹果,用保鲜纸包好,塞进我的包里,说:“别忘记吃。”这个世界有多少大人多少小孩因为数学因为大学而白了头发,憔悴了很多,忧郁起来。前几天,吃午饭的时候,门门优秀的毛毛也哭了起来。说她真不想再念书了,考啊,考啊,一点劲也没有。毛毛居然真的哭得很伤心,我目瞪口呆。李思哲也突然偷偷告诉我,她准备去考联合航空公司,不再拼大学,实在读不下去了。李思哲的英语口语特别特别的好,其实她的数学在文科班也是名列前茅。你说,这是怎么啦?
那一天我还是回了家。外面好冷哦,下雪了。我总是嫌上海的冬天不够冷,看不到灰格子的羊毛围巾,看不到雪,可是在我成了一个流落街头的女孩的时候它却下了起来。我把书包抱在胸口,这样会暖和些。从小爸爸就对我说,胸口别着凉,要不会生病的。我也想就这样漫无目标地走啊走啊走下去,冻死在马路上。明天早晨,很多人看见了这个死去的女孩子,他们会说,快来看啊,这个小姑娘的包里有那么多数学书,还有一张不及格的数学卷子,唉,她是为数学而死的。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半夜。妈妈哭着抱住我。我也哭着抱住妈妈。不念书我又可以干什么?不回家又能去哪儿呢?爸爸摸着我的头:“是爸爸不好……”我靠在爸爸的肩头:“对不起,爸爸,是我数学没有学好。”
那一晚,我和妈妈睡在一起,爸爸在客厅坐到天亮。我告诉妈妈,今天的苹果没有吃掉,我不舍得吃。妈妈泪流满面。
我在电台主持节目的时候讲了这个故事。那是全上海中学生都知道的节目。我们称它是“阳光列车”。可是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只有忧郁和伤感。结束的时候我问负责这个节目的陈洁:“这样可以吗?”她说:“我哭了。”
我们都是些爱学习的孩子,能够考取重点中学多少也是个证明。我们害怕的是那样的方法和考试,可谁知道它们会怎么断送了我们。我们如果被断送了那又怎么办?
高二社会考察是我们整个中学时代所有欢乐的高潮。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玩过,也好像是要把未来所有的轻松提前享受掉。我们在车上打八十分吵得差点打起来。我们坐在西湖边上,捧着三块钱一杯的绿茶,尽享了秋末温暖的阳光。我们在咸亨酒店吃茴香豆,喝黄酒,知道了什么是酩酊大醉,毛毛路也不会走了,何中哇里哇啦地唱“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最后一天的中午,在嘉兴镇上的小饭铺吃饭,李栋吃着吃着嚷了起来:“让我在这儿当农民吧,我再也不想回去了!”汽车往上海开去,白杨树成片飞过。男生们数着窗外路程牌上的公里数,越近大家也就越惊惶,越黯然。明天又要听到期中考试的成绩。高中最后欢乐的帷幕就要落下。毕业的同学前辈个个都说,高三天天是阴天。何中终于说出了他这一辈子最有文采的一句话:“我们的日子到了。”
高三天天是在朝北的教室里拼着。这等于雪上加霜。一个楼面六个教室,四个朝南的都给了理科班,剩下两个朝北的一个给历史班,一个给政治班。到了冬天,小姑娘就带一个小热水袋,到一楼的开水房去冲水。男孩子往二楼的保暖桶冲,去泡雀巢咖啡,喝了又暖和又提神。凭什么朝南的教室都给理科班,文科班只配待在终日没有阳光的北面呢?实在哆嗦得不行,我就只好拿着本书到南面物理班教室去找毛毛。我说:“毛毛,数理化好多好啊!”毛毛就安慰我:“可是我一辈子也写不出好文章来了,哪里像你啊。”也是物理班的何中就趁火打劫:“哈哈,学哲学的马克思,学法律的克林顿,喜欢古典文学的毛主席,如果到我们这儿来上学,也统统是文科班,只能坐在朝北教室里哆嗦啰!”我和毛毛联合骂他:“哆嗦你个头!”然后我会很珍惜地趴在桌子上,在冬日的阳光里昏昏睡去。
那天晚上,下着雪,我在街上漫无目标地走着,结果我真的被冻死了。很多人跑过来说,快来看啊,这个小姑娘的包里有那么多数学书,还有一张不及格的数学卷子,唉,她是为数学而死的。我朝着他们喊,我的苹果呢?我的苹果呢?那是我妈妈早晨放在我包里的!可是我找来找去找不到苹果。我哭了。毛毛推推我:“你怎么啦?”我抹着满脸的泪,很不好意思:“我在找我的苹果。”
以后的一天一天都会这样过去。忧郁地数着日子,但是我也要学会装出潇洒。其实谁不忧郁呢,为什么偏偏我要充满在眼睛里。每天早晨都背着数学还有妈妈洗好的苹果去上学,晚上桌上总有我喜欢吃的青菜炒蘑菇。
“我是一个贪玩又自由的风筝每天都会让你担忧/如果有一天迷失风雨中如何回到你身边/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容易担心的小孩子/所以我在飞翔的时候却也不敢飞得太远。”
我没有办法写出故事的结局。因为我哪里知道最后会是怎样。但是在我小心翼翼的想象中,微笑的日子总会真正来到的吧?我和毛毛他们早就说好了,要是那一天我们都等到了,那么我们一定快快活活地再喝一次黄酒,拼命地唱,“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快活的小行家……”
本文来自博客园,作者:aspirant,转载请注明原文链接:https://www.cnblogs.com/aspirant/p/13820774.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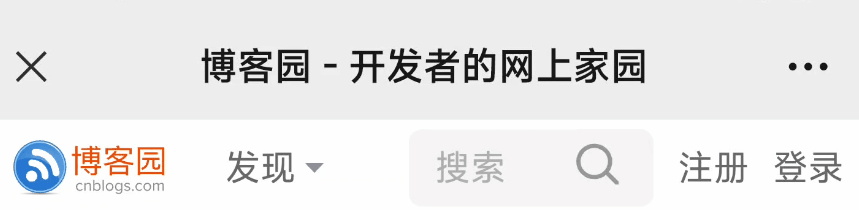
【推荐】国内首个AI IDE,深度理解中文开发场景,立即下载体验Trae
【推荐】编程新体验,更懂你的AI,立即体验豆包MarsCode编程助手
【推荐】抖音旗下AI助手豆包,你的智能百科全书,全免费不限次数
【推荐】轻量又高性能的 SSH 工具 IShell:AI 加持,快人一步
· AI与.NET技术实操系列(二):开始使用ML.NET
· 记一次.NET内存居高不下排查解决与启示
· 探究高空视频全景AR技术的实现原理
· 理解Rust引用及其生命周期标识(上)
· 浏览器原生「磁吸」效果!Anchor Positioning 锚点定位神器解析
· DeepSeek 开源周回顾「GitHub 热点速览」
· 物流快递公司核心技术能力-地址解析分单基础技术分享
· .NET 10首个预览版发布:重大改进与新特性概览!
· AI与.NET技术实操系列(二):开始使用ML.NET
· .NET10 - 预览版1新功能体验(一)
2019-10-15 忽略警告注解@SuppressWarnings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