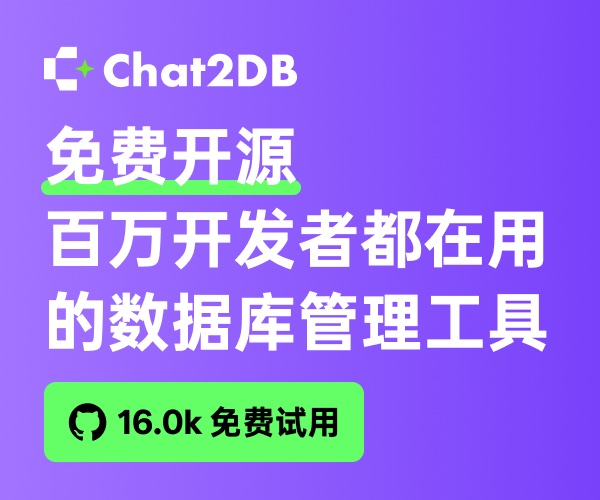我的通讯十年
|
【编者注:于读者建议,我从网络上找到此文并转载于此,希望大家客观评论。我读了2遍。非常不错和优秀的华为骨干。】 大家好,我叫周红,十一年前毕业于复旦大学,到华为公司工作。最初带领一支七人的团队从事CDMA无线接入设备开发,那时候华为无线领域的销售大约一亿元,整个公司约4000人,年产值约20亿。十年来,全球电信产业增加了一倍,华为公司人员发展到约8万人,去年的产值约1000亿,增加了50倍,华为无线领域的产值从当初的1亿增长到今年的700亿左右,我所负责的无线研发团队增加到近万名员工,分布在全球十六个城市。 大家知道,这几年全球经济不景气,十年来的复合增长率每年只有约7.2%,从2000年IT泡沫破灭以来,欧美电信厂家纷纷大合并、大裁员,这次次贷危机使得情况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华为公司,特别是无线领域复合增长率达到182%,还在继续保持高速发展,受到格外关注。 华为之所以发展这么快,要感谢科大以及在座的各位老师,除了与华为公司进行关键领域的研究合作外,学校还向华为公司输送了很多杰出的人才。科大办学精益求精,每一千位学生中就能培养出一名院士,700多名硕士、博士。十年前 我们刚走上CDMA和WCDMA研究道路的时候,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本翻得最烂书,就是朱近康老师写的扩频通信原理;目前华为无线产品线总裁万飚、核心网产品线总裁蔡立群、瑞研所长杨超斌、上海研究所干部部长应陵、基站开发部部长卞红林、以及控制器开发部部长黄学文都是大家的师兄、师姐。 非常羡慕大家!我念大学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还会有今天这样的幸福生活,天天能打电话、能用计算机、能上网,找工作还不用犯愁!现在通信已经进入千家万户,大家能在条件最好、机会最多的时代学习计算机、芯片、电路系统与通信,今年全球电信业务总收入估计将达到2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广阔的事业舞台! 我国通信业发展得非常晚,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电话发明了100年后,我国人均拥有的话机数量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5%!那时候打电话要排长队、要等很长时间,而且可能接不通。 八十年代末,一部电话初装费要差不多5000元,我的父亲在一家上万人的国有大型企业担任副厂长,每个月工资才四十多元。当时在复旦大学只有两个地方可打电话,一个是旦苑餐厅右边小屋,外面经常排上长长的队,另一个是在东区女生宿舍,也就是熊猫楼下的接待室,可以打国际长途。电话费贵的惊人,到美国一分钟电话要我一个月的伙食费。在学校的时候,我从来没打过国际长途,连家里的电话都很少打,主要是靠写信,一张邮票两毛钱。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电话发明后整整一百多年的时间中,我们国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通信产业,没有自己的人才,整个产业被国外企业垄断。大学生活,找不到工作: 87年我考上了复旦大学,读半导体微电子专业,也就是今天的芯片设计。通过半导体参杂、刻蚀等方法,把成千上万的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等集成在一块硅片上,变成大规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这是一个及其精密的活,对环境有很高的要求。复旦大学大操场后面的净化大楼,进去之前要换鞋子换衣服,还要在一段过道中间封闭起来猛吹一通,把身上的灰去掉。尽管如此,当时没有全真空环境,设计出来的东西,做出来往往不合格。净化楼流传着不能吃带鱼的故事,谁吃带鱼谁就做不好芯片,大家想来想去,最后只能怪罪于呼出来的气里纳离子太多。由于整体工业基础弱,如激光、化学、机械等,我们很难做到很高的精度、集成度、速度。一次做实验,我们寝室分成两个小组,另一个小组做出了beta管,放大倍数达到1000倍,而我们组只做到0.1倍──在清洗时少了几秒钟,结果半导体变成绝缘体了! 大三那年学了计算机,手痒痒,特别想编程序,想办法溜到全系各个实验室去侦察了一圈,发现CAT实验室凌教授那里有好几台微机,就毛遂自荐去干活,赖在那里不走,结果就成立CAT实验室最小的师弟,整天跟师兄师姐们混在一起。凌老师对我很好,给我一把实验室钥匙,于是几乎每天我都呆在实验室,疯狂地编写各种程序,除了做各种各样电路设计仿真、信号处理算法外,也做一些好玩的事,有一次我突发奇想,在实验室连续干了三天,接连吃了十几包方便面,终于编程序让计算机演奏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那时候还没有计算机音乐、没有声霸卡更没有MP3,这首歌后来变成了我孩子的催眠曲。周末的时候,我和师兄弟们常常通宵打游戏,我们都是高手,用GAME BLASTER在内存中追查出生命力、火力装备的数据,然后把自己篡改成超级强大、长生不老、战无不胜的英雄。我喜欢通宵干活,半夜了,毛主 席像后面的物理大楼黑黢黢的,只有CAT的427房间亮着灯,空调嗡嗡响。我想,那时我一定是整个学校上万名学生中睡得最晚、用电最多的人。 91年毕业的时候,找来找去,只有四个地方专业对口:北京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无锡华晶、四川永川24所、上海贝岭。几位家里条件好的上海籍同学不约而同地到美国念书去了,有路子的同学分到北京和上海,还有一位同学分到永川24 所山沟沟里。八年后我在深圳碰到他,告诉我们那里的条件其实还不错,特稀罕大学生,每天的衣服换下来放在门口,自会有钟情的小姑娘帮你洗,就像七仙女的故事,他去了第二年结婚、第三年生孩子、第四年就跳槽了。我还记得大四那年的冬天,同学们浩浩荡荡骑着自行车去上海贝岭找工作,那时候漕河泾大部分还是农村,坑坑洼洼的路上来回花了三个小时。我们那一届,一个都没去上海贝岭,或者说上海贝岭一个都没要我们。 我的成绩普普通通,英文和政治很不好,大多数时间只能拿三等奖学金,有一年丰收,拿了二等奖学金,还有一年收成差一些,只拿到鼓励奖。班上学习成绩最优秀的都是女生,她们后来绝大部分都出国去了,其中一位在美国买了农场,开始了养牛生活,一位同学读书回国后做了老师,如今已经是半导体微电子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了。当时我既不是优秀学生,保送不了研究生,家里也没有任何关系,分不到北京和上海,也不愿意到无锡和四川。于是只能拼命补习英语和政治,以我们班的最高分考上了研究生,继续读书。为了将来能有出路,转到无线电专业,做信号处理和通信。 读研的时候手头特别紧张,父亲以前每个月帮我存的5元钱解决不了温饱问题,除了申请贷款外,还在外面找活干。第一次是到军工路上一家炼钢厂,编程序让计算机来自动控制炼钢,从行车抓斗配料到高炉过程控制,一个车间只需要两个人,第一次挣了350元,加上几个月吃馒头咸菜省下来的钱,买了一把红棉吉他和一把萧,后来在上千人的相辉堂大礼堂表演过吉他独奏小罗曼史,萧主要用在女生楼下吹给女朋友听。还有一次接了一个翻版图的活,实验室全体师兄弟、师姐妹几个月干下来挣了5000元,买了一台彩电。 在学校十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读了很多书、做了很多事,通信、软件、硬件、芯片、算法,课内的和课外的,学术的或挣钱的,基本上都行,较广的阅历为之后带队伍、把方向打下了基础;二是在研究生当小课老师时,追到了一位很好的太太,为今后安心工作建好了大后方。 都四千人了,还去华为干什么? 过了五年,博士毕业了,这时候半导体和通信行业都开始火了起来,可以留校,或到国外去做博士后,还可以去外企──贝尔实验室的工资很有诱惑力,一个月 8000元,后来好几位师弟去了。这时候选择太多了也很痛苦!对我来说,在学校憋了十年,摩拳擦掌真想干些大事。一天晚上,一边做实验一边聊天,谈到了我要去华为的打算,我的好朋友,第一届全国芯片设计大赛特等奖获得者周汀很吃惊地问我,“都四千人了,你还去华为干什么?”的确,当时的华为只是一家民营企业,在大多数同学心中,华为在名气和待遇上完全不能与贝尔实验室相比的,在生活安逸上更不可能与学校比。现在回忆起来,我之所以选择到华为,主要在于华为有着梦寐以求的发展平台以及充满激情的文化。 当时听说华为有个博士后流动站,这非常少见。正好有两位师兄在华为工作,就找了个机会去看看。到了华为,在无线业务部一个宽敞明亮的办公区里,看见一组又一组的人聚在各自的小白板前面热烈地讨论着,有人在埋头画电路,有人在专心编程序,有人在调板子——真是非常热闹。 有三件事情打动了我:一是当我把博士期间做的跳频通信研究的情况做了介绍后,研发领导徐总、余总就无比热情地欢迎我到公司做博士后研究,无论做什么方向,都支持我,随便挑,经费不受控制,这比在国外做博士后这样那样的限制条件要好得多,公司对于知识和人才的尊重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这两位领导先后做了公司欧洲地区部的总裁,带领兄弟姐妹们打下了欧洲最高端的电信市场,成为公司巨大的产粮区。第二件事情是我去找彭智平师兄聊天,他是无线电专业蓝老师的学生,只比我高一年级,研究生毕业就工作了。当时他正在筹划申请一个无线集群项目,要争取超过五亿的收入,对我这种在学校呆了近十年、啥也不懂的人来说,这真是天方夜谈,认为他吹牛不要本钱!前几天我特地给他打了个电话,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同意把他的故事奉献给大家。实际上十年前的这个项目,解决了我们国家农村地区有线电话铺设的难题,通过无线基站可以通过无线覆盖超过10公里,首次让20万偏远农村的用户第一次用上了电话。当时业务发展非常火爆,刚安装不久话务量就饱和了,远远超出建网时话务量模型,到现场去调查,才发现农民背着无线固定台去赶集,作为公共电话用!98年特大洪灾时,江主席在湖南抗洪前线使用的无线通话设备,就是华为的ETS。这个 项目实际上创造了好几十亿的利润。彭师兄后来调到光网络产品线,在他的领导下,做出了世界上最长传输能力的光网络解决方案,把华为的DWDM做到了世界第一!另外一位张顺茂师兄是CAD实验室唐老师的学生,也只比我高一年级,他带领固网的兄弟姐妹们,用了近十年的时间,从国内的农村包围城市开始,到后来在全世界到处搬迁其他厂家的交换设备,把华为公司的程控交换机做到了世界第一!现在大家能随便打电话、随便上网,要感谢张师兄。 在华为,绝大部分是年轻的小伙子、小姑娘,一不留神你就会碰到电信领域年轻的世界级专家,几年的功夫他们就把产品做到了世界第一,在二十多岁就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第三件事,是我在人力资源部与肖老师谈博士后的事,这时一位大师傅走了进来,在办公室地上铺了一层报纸,指挥着一群年轻人把一摞子书搬了进来。肖老师马上抓着我到那位大师傅面前说,“任总,这是复旦大学的博士,来做博士后”。当时可把我吓了一大跳——几千人公司的老总竟然这么平易近人。任总把一套介绍我国老一辈科学家“两弹一星”艰苦创业的书送给我。在学校学习和研究了十年,完全不知道实际产品是怎么回事、没有为社会做过一点贡献,急切地希望能多做一些事情。一个公司的老总能这么执著的推崇创新精神、有这么好的大平台,肯定有很多事情可做,于是我就决定了。 移动通信,无知、无畏: 八十年代商用的移动通信系统,采用的是第一代模拟制式,以美国的AMPS和欧洲的NMT为代表,大砖头、大能耗。由于加密很困难,用无线接收机可以收听到电话,同时因为调制方式落后,容量很低,第一代模拟制式的不能支持大规模用户扩展。 九十年代,以欧洲的GSM制式和美国的CDMA制式为代表争夺第二代移动通信的市场,GSM经过欧盟长期研究和试验,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CDMA起源于军用技术,具有优良的抗干扰性能,在军事、宇航通信中广泛应用,美国的高通公司稍后解决了蜂窝应用中的功率控制、软切换等问题,实现了民用。我们国家最初选型采用GSM,中国移动现在的全球通、神州行就是这种制式,随后联通选用了CDMA制式。 97年我一进公司,就挑了一个最难的课题:CDMA无线接入网络开发,那时候CDMA制式在全球试商用才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我们项目组8个人,甚至全公司都谁没有真正做过CDMA,我的博士课题搞跳频,与扩频相近,于是就负责关键算法分析和实现。我们与北大无线电系项海格教授合作,他做过卫星通信的 CDMA技术,整个项目组移师北大,在物理系后的铁皮物中干起来,北京的夏天很热,没有空调,我们几个小伙子光着膀子在里面干,挥汗如雨,就像桑拿一样。半年后,项目组回上海继续开发。样机做出来,我们基站的覆盖太远了,市里面测不行,于是驾着小船到海里拉距测试,那天突遇狂风暴雨,上海交大的高才生赵明差点没能回来──他现在已经是CDMA产品线总裁;我们花好几个月,在烈日下抱着终端优化无线算法,从只能支持步行提升到100公里的时速。这期间,因为没有产品开发经验,我们犯了很 多错误,吃尽了苦头,下定决心要向兄弟部门学习,按规范来好好开发: 1. 不懂工程应用。在硬件设计中简单地把器件连起来,不知道在高速应用时每根线和每个接口上可能存在严重的过冲,用久之后“砰”地一声,器件盖子炸飞了,有的还要冒一阵青烟。 2. 粗心。把二极管焊反了、电源跳线冒忘了插,器件居然还能工作,只是性能偶尔不对。本来1个人1分钟就能解决的问题,花了100人天。 3. 逻辑设计不规范,几十万门逻辑的芯片每天偶尔出一次错,花了两周攻关,最后在一天半夜,才在大海捞针中捉到1ns的异步设计毛刺。 4. 软件开发不规范,不懂CMM,每千行的缺陷尽然有近十个之多。98年,因国家频点频点收回,CDMA产品被迫放弃。虽然没有实现产业化,这两年的工作给了我很强的信心,我们团队形成了敢做敢为精神和胆大心细的工作方法。 97年的生活 刚开始在深圳工作,后来到北京,再到上海,太太因此先后换了两个工作。研究所最初在上海西南角漕河泾,我在桂林北路边的一排民房里租了一套房子,两室一厅,空空的没有任何家具,只有两张床,一个月要1500元。四千多元的工资除了孝敬父母、吃饭、房租外,没剩多少。太太在上海东北角复旦大学那边上班,我们各自分头住宿舍。有时周末,我从上海西南角骑自行车到东北角,来回三个多小时去看她(从没想到过要坐TAXI)。因为我下班比较晚,而且常加班,更多的时候则是她乘公交车来看我。有一次,我出差了三个多月刚回来,太太辗转乘车来漕河泾,我在路边等啊、等啊,天都快黑了,才看见瘦瘦的她疲惫地挤下公交车,那一刻我心里又幸福又愧疚。97年的时候,房价高得离奇,感觉只有外国人才买得起房子,偏远的虹许路上,商品房要卖到两三千一平方米,美元、不是人民币。直到99年,我 们从老丈人、丈母娘那里借了钱,才在浦东的农村买了一套房子──空气很好,一开窗就是大棚农田。 大部队大协同,挺进第三代: 98年2月,我们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3G国际会议,3G将通信流量提升了至少十倍,将有可能实现可视电话,实现高速无线数据业务,描绘了一个美好的蓝图。 我开始负责3G关键技术预研。当时最缺的是什么?人才!我到全国各地高校跑,在各个对口专业中物色了100名硕士和博士,最后博士基本都没来,而硕士大部分都来了。 经过两年研究,我们完成了从公式到模型的仿真和关键技术验证,心里有数了,向公司汇报,估计需要投入十倍于CDMA的人力,用大约200人、花三年做出产品来。八年后回头看,仅在WCDMA上,我们就投入了接近2000人。感谢上帝我们那时候真的很天真,否则公司看到要当时全公司一半以上的人投入到这个八年后才能见成效的项目上,不知道能否下得了这个决心。 那时候WCDMA标准还没有定型,没几个月就变一次,为了做快一点,我们到全世界寻求去合作,美国谈一家著名公司,要300人投入、要价三千万美元,欧洲谈一家小公司,两千万欧元。回头和兄弟们商量,太贵了,IPR还是别人的,决定自己做。 01年中,WCDMA网络上的八个全新的设备(终端、基站、控制器、MSC、SGSN、GGSN、HLR、OM),上千人从深圳、北京集中到上海金茂大厦六层大楼中,开展大会战,开始一段时间我负责整个联调工作,八个网元近千万行软件代码和几百万门逻辑中,发现了成千上万的问题,不断成立攻关组,最多的时候有二十多个团队在轮番攻关。花了大半年,整网解决方案打通,WCDMA正式出台。在WCDMA上,我们走出来一条独立自主、大团队阵地战的路。 逆周期成长,活下去: 我们的WCDMA做的很不巧,01年前后,全球电信业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泡沫,美国股市一下子蒸发了几万亿美元,硅谷大量公司倒闭,电信厂家纷纷大裁员,我们最大的一个对手,在美国达拉斯一天晚上就把5000人裁调了。 WCDMA出来了,但国内迟迟不发牌照,心里憋得慌,我估了一下,每等待一天,就要多支出300万,心急如焚。同时,GSM产品竞争力弱、打不开局面,CDMA联通招标失利,每年20多亿的销售还不够解决无线自身的粮草。 不能被动等待,为了生存下去,公司提出“在冬天里改变竞争格局”、“雄纠纠,气昂昂,跨过太平洋……”,市场体系瞄准海外拓展,研发体系在欧美建立研发中心,同时内部狠抓质量管理,在我当上海研究所所长期间,请来KPMG专家,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把能力提升到达到CMM5水平。 03年,GSM在国内通过边际网实现了“农村包围城市”,在海外实现了发展中国家的连续突破。CDMA选择了450M频段作为突破口,挺进了欧洲市场。 WCDMA在2003年圣诞前夜,高价中标拿下阿联酋ETISALAT和香港SUNDAY商用网络,实现WCDMA零的突破。03年,华为无线实现50亿元销售,向海外进军,活了下来,实现了第一个逆周期成长。 预研和标准,抓住产业制高点: 产品做出来了,要在行业中真正立足,必须抓住制高点。通信行业的制高点是什么呢?标准和专利,要吸取VCD行业的教训。刚开始抓预研和标准工作的时候,焦头烂额摸不着头绪,虽然我们不断提出新方案,在国际标准会议上吵不过外国白胡子老爷爷、老太太,他们在这个行业干了20年、甚至30年了,我们清一色的毛头小伙子、小姑娘,在标准会议上不会举手、不会说话。从95到05年,这几乎颗粒无收。 后来我们慢慢认识到,标准涉及各家公司的核心利益,除了勇敢地举手和说话外,技术能否被接纳更多时候还取决于台下的功课,你支持我、我支持你,或你反对我、我就反对你。随着我们研究能力越来越强、产品市场地位越来越高,公司关系、人脉关系建立好之后,我们的预研和标准逐渐得到认可。到目前,我们在 3GPP WCDMA领域通过了一百多项提案,占全部标准的7%;在3GPP2,CDMA向未来AIE发展的标准上,我们走到第2~第3的位置;在WiMAX NWG上,通过的提案全球第一。在LTE标准初期,我们加入了30项基本专利。 目前我们在各类无线通信的国际标准或技术协会上,已经有36位现任主席或副主席,其中93年上海交大毕业生孙立新是ITU-R七个主席中最年轻的一位,00年中科大毕业生夏斌、99年清华毕业生王虎分别担任WWRF相关工作组的主席和副主席(总共十个)。除了国内年轻的小伙子、小姑娘们外,我们在瑞典、法国、美国等研究所还有很多业界知名的老专家代表公司,推动无线产业的发展轨迹。 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研发: 通信所需的各种关键资源,在全球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我国有令全世界羡慕的大量优秀的毕业学生,每年高达五百万人,但在部分领域,如射频、芯片上,我们缺乏老专家,与世界最顶尖的水平还有一些差距。因此要建立移动通信领域的全球竞争优势,无线研发必须要进行全球布局。正好这些年欧美电信公司大都很不景气,他们在欧美进行着大合并、大裁员,很多已经下岗的或即将下岗的曾经管辖几百人甚至几千人的VP都愿意加入我们海外研究所一起干。我也碰到很多MIT、 STANFORD等名校毕业的博士,工作了10年、 20年甚至30年,在重新找工作。今年初我到美国,一些电信公司原来几千人的研发中心陆陆续续被关掉,能平铺上千多部车的停车场,连同一栋栋的大楼,空空荡荡。 经过几年的布局,我们已经形成了以上海的为中心的研发体系,欧洲、美国、国内各五个城市分工协作。 除了在全球建立研发分部,我们还与全世界最有创造力的专家教授合作,除了在座的各位教授和国内其他知名教授外,欧美高校对口专业著名教授、IEEE技术协会副主席、CAS/MTT专题主席和一批副主席,以及美国、俄罗斯、欧洲各国移动通信相关的工程院院士、科学院院士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欢迎这些顶级大师每年都来喝喝茶。 07年,我们开始筹建国内第一批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拉通国内产、学、研力量,牵头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推进超前技术研究、IPR和标准竞争力。与此同时,我们也把越来越多的技术的、标准的国际会议拉在中国开,推进全球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同时我们也在通过与全球最领先的运营商合作,不断围绕客户价值创新,提升产品的核心技 术竞争力。 走出others,服务全球TOP运营商: 十年前,在规划市场目标时,我们落在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阿尔卡特、北电、朗讯、摩托诺拉等后面,属于others。01年前后,抓住全球电信泡沫危机的几年时间,我们实现了逆周期成长,经过市场和研发的全球布局、管理能力的不断提升、产品的不断完善、以及在研究、标准、技术上的持续努力,我们正在走向世界第一的路上,目前华为无线产品已经服务超过100个国家: 1. GSM去年出货超过70万载频,排名世界第三,今年出货量将再翻番。 2. CDMA在新兴市场上,06年出货占约全球44.8%份额、全球第一,2007继续保持第一。 3. WCDMA在新市场上,合同数量从2004年的全球第三、到2005年全球第二、到2006年、2007年全球第一。 目前,电信领域正在经受第二次危机,欧美电信企业在合并整合的同时还在继续大裁员,我们期望抓住这个机会,争取在第四代移动通信的LTE和WiMAX体制上,从一开始就走在业界最前面。大家知道,PC时代成就了微软、IP时代成就了思科、无线通信时代成就了爱立信、互联网时代成就了GOOGLE,未来十年将是移动宽带的时代,大家猜猜几家能活下来、谁会是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