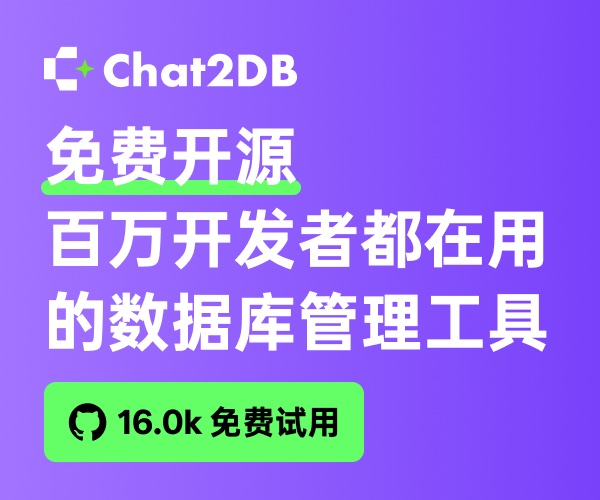95到98年我干过两次水泥工,那时候我还在上中专。
第一次是在96还是97年我记不大清楚了,放暑假的时候为了挣点学费,我找表
哥带我去工地干活儿,那个暑假雨水很多,经常停工,所以断断续续干了十天
。
第二次是在98年,我刚毕业,找不到工作,于是又和表哥去市里一个工地,在
那里干了40天。
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我和另一个小伙子把库房里的所有地板砖分类,重新码放
。地板砖都是混放的,我们要把每一箱打开,量出尺寸、归类,然后再放回去
。这样每一箱至少要移动三次,每一箱是25公斤,估计得有几千箱,一天下来
,我们竟然每人搬了几吨的东西。那天晚上我睡的很香,几乎是躺在床上就睡
着了,第二天起来的时候,身上的每个关节都吱吱做响,每块肌肉都酸疼。
在工地干活也分技术工和非技术工,我是属于没有技术那一类的,所以只能干
体力活。在以后日子里虽然都很累,但我都能把分配的工作做完。记得有一次
有一个单元楼层地板的水泥地面出现裂纹,需要返工,于是我和另外两个小伙
子被分配过去,要求一天把出问题的那间房子的地面全部扒掉。那些地面是用
水泥和石碴混凝土造的,房子一百多平米,水泥地面厚度约十公分,我们就用
大锤和钢钎一点点掀开。每一锤下去觉得整个楼都在晃,每一钎下去都有我们
的汗水。水泥地面掀完以后还要把掀下来的水泥块运到楼下,当我们全部干完
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在我们下楼回去休息的时候路过一堆的水泥块,
还为自己的劳动成果感到自豪呢。就这样到我手上磨出的第一批水泡已经干结
的时候,我似乎觉得有点儿轻松了。
然而那一次,我差点死在那里。
我和表哥一起粘地板砖,我给他供砖和水泥。砖车不太重,也就几百斤吧,我
一个人拉也不觉得费劲,但水泥车就不同了,一车水泥怎么也得有上吨重,而
且那儿的水泥车全没有轮胎,只有一个铁圈支撑着,轮子还不是圆的,车子也
不知多长时间没修过了,一拉就嘎嘎的响。我最喜欢倒水泥车的那一瞬间。车
把往上一抬,整车水泥就倒下去了,那力量要是人抓住车把不放可以把一个人
迅速抬到空中。我每次拉水泥的时候都有一个习惯,当我把水泥倒出去的时候
,脚蹬在水泥车的钢筋横梁上,手紧紧抓住车把,让它把我抬起来,那感觉像
飞一样。可我怎么也没想到问题就出在这里,那次表哥粘地板砖快到门口了,
我拉了一车水泥给他倒在门口,我照例去感受那“飞”一样的感觉,就在我把
车把抬起来的那一刹那,我突然意识到这一车是倒在门口的,车把抬起来距上
门框只有一米左右,我脚蹬着水泥车横梁,两手架在车把上,肯定会重重地撞
在门框上,那瞬间上升的力量足以撞破我的脑袋,我就算不死也得重伤。就在
那一瞬间,我下意识的低了一下头,门框就擦着我的头皮过去了,我留的是寸
头,我清楚的感觉到脑袋擦过门框时的那一阵冷风。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从车上
下来的了,只记得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现在想起
来还觉得毛骨悚然。从那以后,我再也不“飞”了。
表哥粘地板砖到一些墙角的时候,留下的空间都是不规则的,要粘地板砖就得
按它的形状来裁剪地板砖,裁剪的工具就是钳子,用钳子一点一点的修剪,我
的手掌很快就磨出了水泡,在水泡还没有愈合的时候又被磨破,直到连钳子都
拿不住,我就在手掌上缠了一块毛巾,但水泡干结的地方经常运动,不但不能
愈合反而裂开了,粘在我的白毛巾上一片片的血迹。
现在想想,那才是挣的血汗钱。我暗暗许下心愿,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干水
泥工了,当我手上磨出第十个水泡的时候,我一定要离开这个鬼地方。在我干
到第40天的时候,我终于磨出了第十个水泡。就在那一天,我向表哥告了别,
打好铺盖卷回家了。
秋天下午的阳光依旧火辣,我已经被晒得很黑了,所以不怕,骑着自行车穿过
一片片玉米田,偶尔穿过一片树阴,你会觉得风也是忽凉忽热的。这时候的蝉
叫得正是起劲,它们的声音比那些叮叮当当的声音好听多了,我也会和着它们
的声音吹起口哨。回首身后,又多了两条忽而交叉又分开的车轮的痕迹,但他
却没有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