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ing Mortal 1
跟伊万·伊里奇遭遇的原始的、19世纪的医生们相比,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实际上,考虑到我们加诸病人身上的披着新技术外衣的折磨,甚至可以说,我们比他们更不如。这一境遇已足以让我们反思,到底谁更原始。
无须同临终老人或处于生命末期的患者相处太长时间,你就可以本能地意识到,医学经常辜负其本应帮助的人们。我们把生命的余日交给治疗,结果为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好处,让这些治疗搅乱了我们的头脑、削弱了我们的身体;我们在各种机构,比如疗养院和监护室,度过最后的时光,刻板的、无形的惯例使我们同生活中真正要紧的东西相隔绝。我们一直犹犹豫豫,不肯诚实地面对衰老和垂死的窘境,本应获得的安宁缓和医疗与许多人擦肩而过,过度的技术干预反而增加了对逝者和亲属的伤害,剥夺了他们最需要的临终关怀。人们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应该如何优雅地跨越生命的终点?对此,大多数人缺少清晰的观念,而只是把命运交由医学、技术和陌生人来掌控。
我认识了她的祖母爱丽丝·霍布森。老太太当时77岁。印象中,她热情、思想独立,从不刻意掩饰她的年龄。她一头自然的白发,梳成贝蒂·戴维斯风格的发型:直发,梳向头的一侧。她的手上缀满了老年斑,皮肤皱皱巴巴的。她穿着简约但熨烫得整整齐齐的衬衫和裙子,嘴唇上抹了一点点口红,鞋跟远远超过了旁人想象的高度。
如今由于信息与传播技术(始于印刷术并扩展到互联网)的发达,老年人不再独有对知识和智慧的掌握,他们的地位动摇了,崇老文化瓦解了。新技术创造了新职业,要求新的专业技能,进一步破坏了经验和人情练达的独有价值。曾几何时,我们会向一个老前辈求教如何认知世界,现在则直接上谷歌查询;如果不懂电脑,我们的第一个念头也是求助一位少年达人。
他说她的情况非常好,思维敏捷,身体强壮。她的危险在于难以维持目前的状况。她所面临的最严峻的威胁不是肺结节或者背部疼痛,而是跌倒。每年有35万美国人因为跌倒导致髋关节骨折。其中40%的人最终进了疗养院,20%的人再也不能行走。导致跌倒的三大主要危险因素是平衡能力差、服用超过4种处方药和肌肉乏力。没有这些风险因素的老年人一年有12%的机会跌倒,三个风险因素都占齐的老年人几乎100%会跌倒。
但在当时,他并不担心;只要能上路他就高兴。在拐上138道后,夜间的车辆很稀疏。凯美瑞的车速刚好超过每小时45英里(约72千米)的限速一点点。他把车窗摇下来,手肘搁在窗框上。空气清新、凉爽,我们听着轮胎碾轧道路的声音。
他说:“多美好的夜晚,不是吗?”
我问他,如果右耳听力再次丧失,或者发生类似的灾难,他怎么办。他说不知道。“我害怕一旦我无法照顾她的话情况会怎么样,”他说,“我尽量不想太远。我不会考虑明年,这想起来太压抑了。我只想下周。”
如果马斯洛的需求层次是正确的,那么,缩小生活范围与人们追求最大限度的自我实现就是背道而驰的,你会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快乐程度会降低。但是,卡斯滕森的研究发现,结果刚好相反。人们根本没有变得不开心,而是随着年岁增长,快乐程度提高。他们比年轻时更少焦虑、压抑和愤怒。的确,他们会经历困难,也常常体会到辛酸悲苦——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经常交织在一起。但是,总体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觉得在情绪方面,生活体验变得更令人满意、更加稳定了,即便年老缩小了他们的生活范围。
在托马斯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曾赢得学校举行的每一场销售比赛。学校派孩子们为童子军或者某个体育队挨家挨户去卖蜡烛、杂志或者巧克力,他总能把销售冠军奖带回家。高中的时候,他在学生会主席竞选中胜出,并当选田径队队长。只要他愿意,他几乎可以把任何东西(包括他自己)兜售出去。
但他却是个很糟糕的学生。他的成绩很差,经常因为不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而跟老师发生冲突。不是因为他不会做作业(他是一个如饥似渴的阅读者和自学者,是那种可以自学几何、自己造船的孩子,而且他的确造了一艘),他只是无意做老师要他做的作业,而且他会毫不犹豫地直言相告。放在今天,我们会说他患了对立违抗性障碍。但在20世纪70年代,老师们只是觉得他很麻烦。
两种形象——销售天才和倔犟反抗老师的人,似乎有着同样的根源。我问托马斯他小时候有什么特别的销售技巧。他说没有,只不过“我愿意被拒绝,这就使得你成为优秀的销售员。你必须得愿意被拒绝” 。这一特性使得他学会避免他不想要的结果,懂得坚持,直到达成意愿。
然而,他从不觉得自己想要赢得任何人的赞同。有教职员想征召他加入他们在大医院的专科培训项目,或者加入他们的研究实验室。但是,他选择在纽约罗切斯特成为一名家庭医学实习医生。这并不符合哈佛渴望杰出的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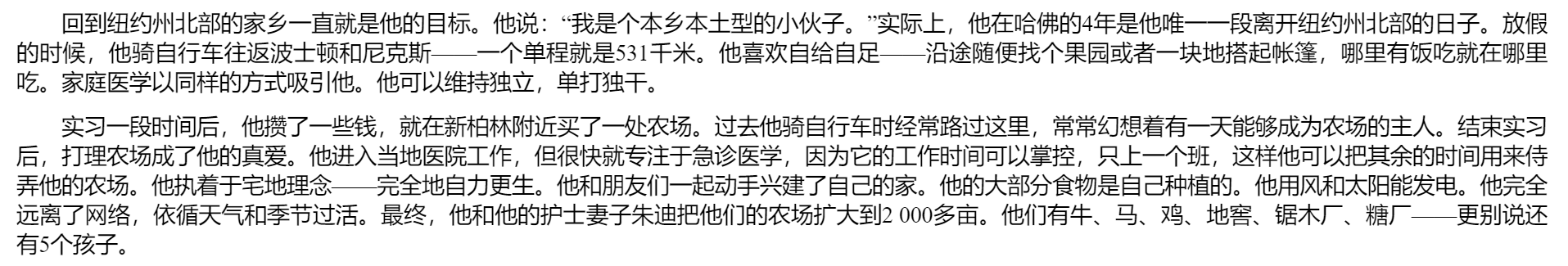
托马斯解释说:“我真心觉得这是我能够过上的最真实的生活。”
那时,他是医生,更是农夫。他蓄着保罗·班扬式的大胡子,在白大褂下更喜欢穿工装裤而不是打领带。但是急诊室的工作很耗精力。他说:“说到底,我是厌烦了上夜班。”于是,他接手了疗养院的工作。这是一份日班工作,上班时间是固定的。这份工作能有多难呢?
这个任务可不小。每个地方都有根深蒂固的做事情的文化。“文化是共享习惯和期望的总和。”托马斯告诉我。在他看来,习惯和期望已经使得机构的例行公事和安全成为比好生活更优先的考量,甚至阻碍疗养院领来一条狗同居民一起生活。他想带进来足够的动物、植物和儿童,使他们成为每个疗养院居民生活的正常部分。员工固化的日常工作会被打破,但是,这不正是目标的一部分吗?
“文化具有极大的惰性,”他说,“所以它是文化。它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它持久。文化会把创新扼杀在摇篮中。”
为了对抗惰性,他决定直接迎击那些抵制者——用托马斯的话说就是“奋力打击”。他将之看作一整套改革。他们不会领来一条狗、一只猫或者一只鸟,看看每个人的反应再做打算;他们要在几乎同一时间把所有动物引进来。
对托马斯而言,这完美地体现了他关于生物作用的理论。针对厌倦感,生物会体现出自发性;针对孤独感,生物能提供陪伴;针对无助感,生物会提供照顾其他生命的机会。
(共同体)
我们试了。想一想这样一个事实吧:我们都深切地关心我们死后世界会发生什么。如果自我利益是生命意义的主要来源,那么,如果死后一个小时, 我们认识的每个人都将被从地球上抹去,我们应该觉得无所谓。然而,这对很多人来说都很要紧,因为我们会觉得若真发生这样的事,我们的生命将毫无意 义。
唯一让死亡并非毫无意义的途径,就是把自己视为某种更大的事物的一部分:家庭、社区、社会。如果不这么想,那么,死亡只能是一种恐惧;但是如果这么想,就不是。罗伊斯认为,忠诚“通过显示为之服务的外在事务, 以及乐于提供服务的内在意愿,解决了我们庸常的存在的悖论。在这种服务中,我们的存在不是受到挫折,而是得到丰富和表达”。近期,心理学家使用“超越”(transcendence)一词表达这样一种思想。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的自我实现之上,他们提出人们有一种看见和帮助别人实现潜力的超越性愿望。

“下次如果看见你,我会认不出你。你灰蒙蒙的,”梅克沃尔告诉我,“但是你在微笑。这我看得见。”
“噢,感谢上帝,我可以自己走到卫生间。”梅克沃尔告诉我,“你会认为这没什么,因为你还年轻,等你年龄大了就明白了:生活中最好的事情就是你能自己去卫生间。”
医生们想马上开始治疗,这意味着要实施引产手术把胎儿取出来。这是6月的一个暖和的星期一,萨拉和她丈夫里奇正单独坐在产科外面安静的露台上。她握着里奇的手,他们俩竭力控制着情绪,消化刚刚听到的消息。她从来不抽烟,也没有跟抽烟的人共同生活过;她锻炼身体,饮食健康。这个诊断令她不知所措。“会好的,”里奇对她说,“我们会渡过这一关的。是的, 会很难,但是我们会有办法的。我们能够找到正确的治疗方式。”然而此 刻,他们还有个婴儿要考虑。
那个6月,他的退休晚会之后,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手术是他的天职,界定了他的人生目标和生命意义——他的忠诚。从10岁开始,当他眼见自己年轻的母亲死于疟疾时,他就立志当个医生。所以,现在这个男人要把自己怎么办?
我们见证了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转变。他一头扎进扶轮社地区总监的工作,虽然他的任期才刚刚开始。他是如此彻底地投入,连Email签名都从“阿 塔玛拉姆·葛文德医生”改为了“阿塔玛拉姆·葛文德地区总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不是试图紧紧抓住他正在丢失的坚持了一生的身份,而是设法重新定义它——他调整了自己的底线。
这就是所谓拥有自主性的意思——你不能控制生命的情形,但是,做自己生命的作者意味着要把握住自己想怎么应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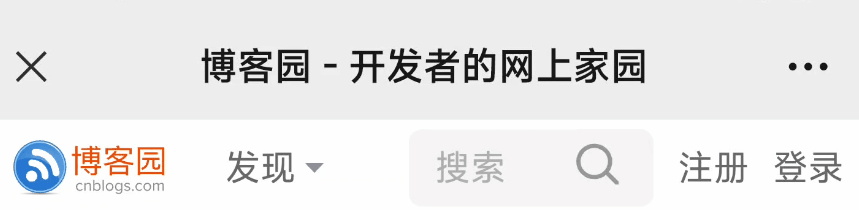
【推荐】国内首个AI IDE,深度理解中文开发场景,立即下载体验Trae
【推荐】编程新体验,更懂你的AI,立即体验豆包MarsCode编程助手
【推荐】抖音旗下AI助手豆包,你的智能百科全书,全免费不限次数
【推荐】轻量又高性能的 SSH 工具 IShell:AI 加持,快人一步
· winform 绘制太阳,地球,月球 运作规律
· 震惊!C++程序真的从main开始吗?99%的程序员都答错了
· AI与.NET技术实操系列(五):向量存储与相似性搜索在 .NET 中的实现
· 【硬核科普】Trae如何「偷看」你的代码?零基础破解AI编程运行原理
· 超详细:普通电脑也行Windows部署deepseek R1训练数据并当服务器共享给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