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避的企业家和未来的治理:创新如何改善经济和政府》笔记
一、引言

这本书的作者是乔治梅森大学的一位专门研究创新的经济学家,叫亚当·提耶尔(Adam Thierer)。

这本书的关键词是“躲避的(evasive)”,躲避什么呢?企业家躲避政府的管理。
提耶尔说的不是跟政府关系密切的那种红色企业家、不是遵纪守法的白色企业家、也不是专门从事非法勾当的黑色企业家,而是游走在法规的边缘,敢跟政府玩游戏、甚至跟政府讨价还价的“灰色”企业家。提耶尔认为,企业家为了搞创新,常常是不得不躲避。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局面呢?如果你是企业家或者你在政府部门工作,这本书会给你带来启发。但我认为,就算你对企业和政府这些事儿没有多大兴趣,这本书也能让你更有精神,你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会更有力量,因为这本书的视角很厉害。
老百姓看企业家往往有一点距离感,看政府更是仰望。提耶尔作为一个自由论派(libertarian)经济学家,他看企业家是平视,看政府则是俯视。
咱们中国政府在过去这几十年中无比支持创新,以至于我们对创新的印象是这样的,政府弄一个创新园区,把企业家请来,土地给特批,贷款给优惠,税收给减免,人才给安排,各种手续特事特办一路绿灯……但是你知道吗,这可不是一般政府的常态。
中国政府支持创新,是因为中国有个后发优势,我们的大部分创新项目都是已经验证过、确实能赚钱的项目。创新能发展经济,能升级国力,能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已经挺发达了,国力已经很强大了,人民的生活已经相当说得过去了,而你弄的这个项目到底能赚多少钱还不一定,政府还会那么迫切地支持你吗?
企业家是任何时候都想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的本能。而政府的本能,则是管制。
我举个例子。我们假设现在京东公司想要在上海市试运行“无人机送快递”,你猜上海市政府能不能批准?
当然不能。开什么玩笑,中国大城市一律禁飞无人机。无人机要是密密麻麻地在天上飞,万一掉下来什么东西伤了人怎么办?影响航空飞行怎么办?刺探了国家机密、暴露了个人隐私怎么办?事实上目前中国的无人机送货业务仅限于在边远山区做实验,城市内如果有特殊需求,必须一次一审批。
像自动驾驶汽车、3D 打印、机器人、数字货币、各种基于区块链的什么新服务,也都有类似的问题。自动驾驶汽车的技术得好到什么程度,政府才能批准它上路?如果有人要用 3D 打印机打印手枪,你怎么管理?什么样的机器人具备上岗资格?数字货币跟非法集资的差别是什么?
这些创新的特点是它不是把已有的产品或者服务变得更好更便宜,而是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产品或者服务。企业家认为这样的创新是大好事,但是政府想的是一切经济和社会活动都应该依法进行。而这些创新出来的东西,往往无法可依,甚至可能直接违反现有的法规。
所以你看,在创新活动上,企业和政府其实是有矛盾的。这跟政府腐败、官僚主义什么的都没关系,它其实是“新”和“旧”的天然矛盾。
企业家和政府大约有三个矛盾,理解了这些矛盾你才能理解创新。
- 第一个矛盾是企业家喜欢冒险,政府害怕风险。
英文中企业家叫“entrepreneur”,其实是特指那些创办新的事业、带头折腾、能弄出一个什么东西的人。你家里有几十套房子你每个月光房租就有不少钱,这不叫企业家,叫理财。企业家得是自己有主意,自己承担风险,去做事的人。因为利润本质上是来自于风险,企业家往往会被利润吸引,而不太在乎风险。像数字货币这样的创新,如果成了,能赚很多钱;如果不成,企业家本人损失可能并不大。
但是政府可不敢冒险。政府得为大多数人负责。科技圈的人喜欢新东西,但是在世界范围内,一般老百姓对科技进步和创新其实有很多质疑的声音。你要说你支持创新,那我问问你,对人类婴儿进行基因编辑,就像 2018 年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做的那样,你也支持吗?那个事儿是个特例,但是我们换位思考,在很多人眼中,转基因食品,甚至连使用化肥,都是不天然、不正确的事情。这里面没有简单的划分方法。
- 第二个矛盾是企业家希望打破现状,政府乐于维持现状。
英文中有个词叫“status quo”,中文一般翻译成“现状”,但我觉得“现状”不足以表达它的内涵。Status quo 的意思差不多是“各利益集团当前的地盘划分情况”。一个城市里所有出租车都属于政府指定的几家公司,出租车司机必须持有政府发放的牌照,这叫现状;你突然发明一个网约车业务,任何人通过手机APP就能注册成为司机,这叫打破现状。
维持现状就是保护局内人的利益,打破现状就是局外人想入局。
- 第三个矛盾是企业家要自由,政府要控制。
从个人的本能来说,如果我觉得做这件事不会伤害别人,而我喜欢做、又能做这件事,那我就可以去做,这是我的自由。但是从政府的本能来说,它希望整个社会井井有条,每个人各安其位,一切都处在可控状态。如果你这件事有可能会导致不可控的后果,我就不允许你做。
创新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驱动,而创新需要油门也需要刹车。以前中国有后发优势,政府经常扮演踩油门的角色,但是创新一旦进入无人区,不知道哪个方向一定对的时候,政府往往扮演的是踩刹车的角色。
那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和可控之间这条线应该划在哪里呢?是政府召集专家研究出来,再邀请企业家开个座谈会沟通的吗?当然不是。这条线是企业家不断刺探底线,政府偶尔反击,最后因为双方都不得已而妥协出来的。
政府通过法规约束市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都是要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违法的都是坏人,执法的都是好人。但是法规也是人定的,人都有局限性,都可能会犯错误。在企业家眼中,法规并不具有天然的神圣性。如果我们有一点博弈精神,法规就如同体育比赛的竞技规则一样。有时候你改一改规则才能让比赛更精彩。有时候为了取得胜利,只要代价合适,你可能还会故意犯规。有时候上有政策,你得下有对策。
企业家有这样对待法规的态度,可以说是“法规黑客”。总结来说,法规黑客大约有这么几个办法。
- 第一个办法是先做了再说(Permissionless Innovation)。
英文有句谚语叫「与其事先请求允许,不如事后请求原谅」。你想在某地开一个新业务,这个业务是以前没人做过的,现在还没有什么相关的法规,那你会去请示一下有关部门,这个事儿能不能做吗?别请示,先做再说。政府的风格是过于保守的,你要请示肯定是不允许,但你要先做了,而且已经做大了,政府通常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关闭你。
上世纪九十年代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时候,没有什么法规说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结果硅谷公司什么都敢做。对比之下,因为航空领域的法规十分成熟,美国公司在无人机上的研发和应用都受到限制,就没有充分发展。
以前纽约市的出租车是政府垄断的,你要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出租车,得先向政府购买一个牌照。牌照的数量极其有限,最贵的时候居然要一百万美元一个:出租车司机只能贷款买牌照,背负巨大的债务压力;乘客得多花打车费,然后还总打不到车。所有经济学家都谴责这个牌照制度,但是没有用。
然后 Uber 来了。Uber 没有去申请什么运营许可,不声不响地就在纽约发展出了十万个用户。等到纽约市当局反应过来,想要立法限制 Uber 业务的时候,Uber 号召用户向市议会施加压力:它的打车 APP 上有个按钮,你可以直接给议员发邮件。结果纽约市妥协,出租车牌照这个老大难问题就这么被躲避过去了。
共享住房公司 Airbnb、基因测序公司 23andme,也都采用了这个办法。有时候政府反应小有时候反应大,但是最后总能妥协。
- 第二个办法是制度套利(Innovation Arbitrage)。
现在是全球化时代,公司是流动的存在,企业家可以选择政府。
Uber 搞了自己的自动驾驶汽车项目,本来想在旧金山市测试,但是繁华的旧金山不允许自动驾驶汽车上路。结果边远的亚利桑那州的政府说我们允许,你来我们这里测试吧。Uber 在亚利桑那测试果然出事儿了,撞死了一个行人,亚利桑那州政府很尴尬,然后 Uber 马上转到别的州去测试。
有些有争议的医疗服务,美国不允许,但是德国允许,于是美国患者就去德国。有个硅谷公司想发射自己的物联网小卫星,美国不允许,但是印度允许,于是就去印度发射。然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批准了它的服务。
- 第三个办法是“软”法规(Soft-law)。
政府也想明白了,有些事儿不做硬性的规定,给你提供一些灰色地带。
比如说你要说直接开业服务,这恐怕不行,但是你可以先测试,只要说是测试就可以做。你还可以说是出于教育和演示的目的在做这件事。然后大家看看结果,一起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 第四个办法则是走入地下,也可以叫“去中心化”。
医疗器材都是非常贵的,有的是因为专利有的是因为垄断,其实真正因为质量的话并不会那么贵。那好,现在有 3D 打印技术了,我自己买个 3D 打印机,自己给自己打印一个假肢,给孩子弄个矫正器,行不行呢?政府会说不行,但是人们私下在做。
有个由志愿者维护的,专门让人们交流 3D打印假肢的图纸的组织叫 E-NABLE(https://enablingthefuture.org/),就能让你做成这件事。利益集团肯定反对,他们会说你这不安全什么的,但是图纸和打印方法都属于信息,而且这些信息都是开源的,这个行为本质上属于言论自由范畴。
那既然这样,有人交流专利产品的图纸行不行?3D 打印枪支的图纸行不行?这就属于地下活动了。但是在某种意义上,那些私下搞盗版的人也是企业家。
总而言之,企业家做事绝非是“守序善良”人格,可能更接近于“混乱中立”。他们为了利益而去刺探社会的底线。但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有他们,社会才能进步。
二、法规是怎样积重难返的
中国政府非常推崇简政放权,这些年国务院动不动就取消几百项行政审批。以前如果你想投资一个F1赛车场项目、或者投资一个纸浆项目,必须由发改委批准才行;一个民办学校要任命校长、或者一个大学搞个特殊专业应届毕业生的就业计划,必须教育部审批才行,现在这些规章都取消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任之初也曾经许诺,说以后我们每增加一条联邦法规,就要废除两条。
我读了亚当·提耶尔的《躲避的企业家和未来的治理》,感觉他们能不能再激进一点:也许现在每增加一条法规,应该废除二十条。
希望这一讲能让你对“政府法规”有个更有用的理解。
有人说中国的法制还不健全,其实法制不健全有时候反而是一种优势。法规是一种具有强烈不对称性的东西:出台一个法规是容易的,取消或者修改一个法规则非常困难。那么随着一个国家建立的时间越来越长,它的法规就必定是越来越臃肿。
咱们以美国为例。国会和各州的立法机关出台的规定叫“法律(law)”,政府机构出台的规定叫“规章(regulation)”,那美国总共有多少法规呢?现在的总数我不知道,但是提耶尔引用一项 1993 年的研究,说那个时候,美国就已经有超过十万条规章。我看到另一份资料显示,从 1995 到 2016 年,国会通过了 4312 条法律,联邦政府机构推出了 88899 条规章。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估计,美国现在有几十万条法规。而你想想当初刘邦进咸阳,与民约法可是才“三章”啊。几十万条法规不是闹着玩的,有经济学家测算,为了遵守和执行这些法规,仅仅是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效应,就高达 1.9 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 GDP 的 10%;这些法规拖了经济的后腿,使得美国经济从 1980 年到 2012 年每年少增长了 0.8 个百分点。0.8 个百分点对中国可能不算什么,你要知道美国每年能涨 3%就算很不错了。如果不是因为法规成本太高,2012 年的美国经济应该扩大 25%。
这些法规不但太多,而且太旧了。68% 的联邦法规从来都没被修改过,另有 17% 则只修改过一次。现在法规旧到了什么程度呢?
- 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至今仍然有这样的规定,说如果一个女人要开车,那就必须有一个男人在车的前方跑动,一边跑一边挥舞一面红旗。
- 新泽西州至今规定在公路上超车必须按喇叭。
- 美国有好几个地方仍然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耳机听随身听。
当然现在你去这些地方,违反这些法律估计也不会被抓起来,但是在理论上,你的确违法了。
所以你说美国哪里自由了?事实上现在你想做一个完全诚实守法的公民是极其困难的,你根本都不知道自己的什么行为违法。
其实政府也知道这很无奈,包括执法者也知道不可能完全依法办事。这本质上是个悖论:当法规太多太严的时候,公民和执法者都会选择无视法规。
那美国是怎么到这一步的呢?提耶尔说了大约四个问题。我看这四个问题简直是人类社会复杂系统演化的通用机制。
- 第一个问题是政府官员害怕风险,导致行动僵化。
对市长来说,如果他治下的城市经济增长了,他会因为政绩而得到升迁;一个美国的民选官员也会因为政绩而赢得下一次选举。但是对于各个政府机构中具体办事的人员来说,“立功”的好处远远小于犯错误的坏处。这些机构人员的利益所在是尽量远离麻烦。
特别是专业管理机构更是如此。美国食品药物监督局(FDA)近年来已经加快了新药的审批流程,但是仍然很慢。它在历史上有过相当无奈的记录。比如米索前列醇(Misoprostol),是一个由美国公司发明的合成药,可以用来治疗胃溃疡。早在 1985 年,美国以外的几个国家就已经批准了这个药,但是美国 FDA 直到 1988 年才批准。
为啥呢?因为它有一个副作用,可能会导致流产。那么简单的办法就是你附加一个规定,孕妇禁用不就行了吗?但就是这么一个附加规定也要折腾好长时间。而你要知道美国每年有一两万人死于胃溃疡。
只要涉及到医疗,审批就都很慢。再比如有个用于诊断皮肤癌的设备叫 MelaFind,纯粹只是给医生做诊断用,对人体无害,结果也是耗了好几年时间才批准。
- 第二个问题是制度建设跟不上技术进步。
无人机的确会有安全问题,的确需要政府的管理。但是你说无人机的安全规章,应该跟喷气式客机一样吗?当然不应该一样。但是联邦航空局(FAA)至今都没有一套专门适用于无人机新技术的安全规章,还在使用旧规章。
当然一部分原因是无人机的技术进步太快了,日新月异,可能你今天设计出来的规章明天就不合适。但航空局的做法是一步步严控,这就大大阻碍了创新。
再比如说自动驾驶汽车。有人估计,关于汽车安全的几乎所有联邦法规都已经过时了,有的过时了几十年。这些法规都非常细致,要求汽车的方向盘必须如何如何、脚踏刹车板必须如何如何,然后开车的时候司机的手必须随时都放在方向盘上,可是现在我们搞的是无人驾驶汽车,这些规定还有意义吗?
立法跟不上的结果就是执法也跟不上。航空局规定无人机绝对不可以在机场附近、在行人的头顶上、或者在夜间飞行,而且要求所有无人机在飞行之前必须取得许可证,但是美国人玩无人机都是想飞就飞,也没人管:提耶尔说一直到 2018 年,就根本没人因为无许可飞无人机而遭到罚款。
- 第三个问题是权贵资本主义。
权贵资本主义这个说法可能有点夸张,其实英文(crony capitalism)的意思范围更广,泛指一切利益集团干涉立法的行为。
一个公司从草根起家,可能还曾经靠做违法的事情取得了第一桶金,做大做强之后,就会想要影响立法。不过很多公司这时候想的可不是让立法有利于创新 —— 最爱创新的往往是新入场的、想要打破现状的企业家,老牌企业家是现状的受益者和维护者,他们想要的是阻止创新。
当然,阻止的理由都是安全啊、可控啊、为了人民的身心健康之类。一部二十世纪的通信史就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阻止创新的历史。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下,FCC 先是限制广播频道,再是限制电视台。美国人一直到 1980 年代基本上全国只能看三个台:ABC、CBS、NBC。后来有了有线电视,三大台之外的电视台仍然被限制发展。是等到互联网出现了,因为互联网不归 FCC 管,互联网公司先斩后奏,美国人民的视频音频娱乐业务才算有了真正的竞争。
所以你说美国哪里是一个真正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呢?
事实是不管你的政治制度如何,既得利益集团左右国家政策这种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1965 年有本书叫《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讲了一个像定律一样的道理。
比如现在有个政策,它的受益者是少数人,而它的成本、它带来的坏处,却是平摊在多数人身上的,那么奥尔森说,这个政策就容易被推动通过。
为啥呢?因为每个受益者得到的好处很明显,他们会积极推动它;但是受害者因为人太多,具体到每个人头上的损失很不明显,他们不会在意。
奥尔森这个逻辑的适用范围极广。贸易保护就是这么来的。比如说我们是否应该给进口汽车设定一个高关税,来保护国产汽车呢?对国产汽车的从业者来说这是跟自身命运息息相关的大事,各个汽车公司一定会对政府施加影响,要求搞保护。可是贸易保护对全国的汽车购买者是不利的,你凭什么让人买价格又贵质量又差的车?但是消费者不会为了这个事儿而组织起来去跟政府谈判。
所以这个局面是利益集团早就联合起来了,老百姓没有联合起来,于是政策一定会倾向于利益集团。
以前我听过一个笑话说「要是马有投票权,世界上就不会出现汽车」,读了提耶尔这本书我才知道这个事儿居然真的发生过。当然马没有投票权,但是 1920 年代,美国马业协会就曾经搞过一次游说活动,要求政府禁止拖拉机和汽车在城市街道上行使。
汽车该不该上道,你怎么能问马业协会的意见呢?然而这恰恰是民主的工作方式。我们知道政府对很多行业的从业者都要求拿一个“资格认证”,有这个认证才能上岗。认证制度的本意是为了消费者的安全:你不能说随便一个人,就允许他给人做手术。
但是有研究表明,认证制度并没有真的提升什么公共卫生安全。经济学家的共识是认证制度是保护现有从业者的手段。为什么美国医生的收入那么高?因为取得医生资格认证无比困难。把所有行业算一起,经济学家估算,消费者因为这个认证制度而多花了 3% 到 16% 的费用,全国少了 285 万个工作岗位。
那到底是什么人在负责批准这些资格认证的呢?当然是那些已经取得认证资格的从业者。请问这跟让马决定汽车该不该上道有什么区别?
据我了解,中国曾经一度让什么纹绣师、化妆师、美甲师都得考资格认证,要求持证上岗,你说你一个美甲师需要什么资格?好在这些认证现在已经被国务院取消了。
要想让经济发展,就应该干掉这些利益集团。1977 年,美国总统卡特推动之下,民航局废除了由各大航空公司成立的联合协调组织,逼着航空公司不能搞合谋,必须去竞争,航空业才迎来大发展,消费者才有了那么多选项。
- 第四个问题叫“组装政治(Kludgeocracy)”。
比如以前我们买电脑,有品牌机和组装机两个选择。品牌机比较贵,但是各种零部件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互相之间有很好的配合,经过了精心的测试。组装机便宜,但是容易出毛病。所谓组装政治,意思是政府各个部门本来就是对付着组装在一起,缺乏良好的维护,后来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至于积重难返。
美国总统管不了美国的政府部门,那些部门自己有自己做事的方法。美国国会已经把立法权大幅度地下放到了各个政府部门,部门想要推出一个法规就可以推出法规。因为这一摊业务已经太复杂了,你想管也管不了。
有句名言叫「一切组织天生都是改变的敌人。」当政府机构越来越大,各项法规重重叠叠互相关联在一起、以至于都没有人能完全理解这个系统的时候,你想牵一发就得动全身,你很难做出什么改变。所以政府机构只能打补丁,而无法大改。
那你说这个出路何在呢?提耶尔认为自上而下的变革太难了,我们需要企业家自下而上的力量。
三、有一种反抗叫退出
去年有一段时间有些互联网公司搞“996”工作制,也就是每天上午 9 点上班、晚上 9 点下班,每周工作 6 天,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之后又有一条新闻说“西贝”这个连锁餐馆推崇的是所谓“715”工作制,每周工作 7 天,每天工作 15 个小时!
当时网上就有很多人反对,认为这完全不合理,员工应该抗争。从世界上有“公司”这个东西开始,像这样的劳资矛盾就一直存在,有时候必须靠政府立法去保障工人的待遇。
但是你想过没有,跟奴隶制相比,公司再坏,它对人的压迫也是有限的。
因为你可以退出。如果我真的那么不喜欢 996 或者 715,我可以不在你这个公司干。公司要解雇员工,有时候会受到法规的限制;员工如果不想给哪个公司干了,谁也拦不住他。公司并不能真的限制员工的自由,它能做的仅仅是用工资之类的待遇把人吸引住。这就好像打游戏一样,如果我在这个游戏里一直都赢不了,我感到其中的规则根本就不公平,纯粹就是系统在故意压迫我,我可以关机退出。
同样道理,现在一些跨国公司所能调动的财力、人力和物力,已经超过了一般的主权国家,但是你能说一个跨国公司就是一个主权国家吗?不能。因为跨国公司不能强迫你购买它的产品或者服务。如果你不喜欢Google收集用户信息的行为,你可以抵制Google,你可以用比如说DuckDuckGo。
可退出,给人提供了最终的底气。这个局面再不好,只要你可以退出,你就仍然是自由的,你就能坚持自己最想坚持的东西。
那你说不行啊,我总要挣钱总要消费,如果所有相关的公司都已经联合起来了,执行同样的政策和服务,我加入哪家都等于是加入同一家,我又怎么能退出呢?是的,所以我们需要创新。
新技术和新公司给人增加了新的选项,使得人们可以退出原有的局面。这就是为什么创新是一种革命。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公司不好我可以退出,要是政府不好,我也可以退出吗?咱们继续讨论亚当·提耶尔的《躲避的企业家和未来的治理》。而提耶尔说,公司可以帮助政府改善治理。
上一章我们讨论了政府有种种的积重难返,但是经验表明,政府自身很难改革自己。美国政界一直在高喊什么放宽管制和机构重组这种类似于咱们中国人说的“精兵简政”的口号,但是真正做成的很少。上两次真正对政府部门动手术,还是 1985 年砍掉了“民航管理委员会(The Civil Aeronautics Board)”、1995 年砍掉了“州际商务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现在都没人记得还有这样的事了。
那如果政府机构只变大不变小、法规只增不减,这样的系统还能无限维持下去吗?就好像一台计算机,是不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把操作系统重装一遍,才比较健康呢?
这其实正是美国建国的国父们心里想的。托马斯·杰斐逊就说,政治世界里偶尔来个小叛乱,就如同物理世界里偶尔来个风暴一样,属于是必要的事件 :「上帝禁止我们连续 20 年没有叛乱」。如果统治者不经常被人民的抵抗所警告,国家又怎么能保护自由呢?
而美国人民也的确有抵抗政府的传统,不过一般不是武装叛乱。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抵抗行动一般都是采取“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的形式,是以街头运动的形式为主,通常是非暴力的。像反越战、民权运动、到几年前的“占领华尔街”、到现在正在发生的“黑人生命重要”运动,其中虽然有暴力成分,但是跟历史上那种“起义”可是两码事。
那这些运动有用吗?民权运动和反越战确实是有用,但是最近几年的“占领华尔街”、“黑人生命重要”好像没什么真正的作用。美国两党对这些议题的态度不一样,老百姓的想法也很矛盾。现在美国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达到最低点,只有 18% 的公民表示自己在多数情况下信任联邦政府,而表示自己在所有情况下都信任政府的则只有 3%。
美国的政治制度简直是已经陷入危机。提耶尔是个自由论者,主张小政府,但他可不是要搞无政府主义,他主张帮助政府改革。他提出的方法就是企业家的创新。
企业家的解决办法是给人民提供新的选项。纽约市出租车牌照问题天怒人怨但是谁也解决不了,Uber 给解决了。这一局我怎么都赢不了你,没关系,我不推翻你,我甚至都不跟你冲突,我新开一局。
我退出你。
如果没有 Uber,纽约市的人民可能都无法想象一个更好的打车系统会是什么样的。现在好了,纽约人可以退出政府设定的游戏,去玩 Uber 提供的新游戏。
所以创新最大的意义还不是提供了更好的选项,而是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选项。有这个选项在,旧的选项就受到了制衡。可能你只爱住豪华酒店,对 Airbnb 什么的共享住房不屑一顾,可以,你不感兴趣有人感兴趣,所以 Airbnb 的存在仍然让传统酒店行业感到了威胁,仍然逼着传统酒店行业降价和提高质量,仍然对你有好处。你可以不开电动车,但是电动车的存在能帮你把油价降下来。
创新能倒逼改革。如果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技术形成成熟的应用,人民可以在某些领域自己管理自己,那么政府就必须在那些领域改善管理方式,否则政府就没有存在感了。
创新就像是一个减压阀,因为允许人退出,而使得更激烈的对抗不必发生。创新又像是一个“可控燃烧”机制,主动烧掉森林里一些树木,有利于整个森林的健康生长。
提耶尔说,国家的主权在哪里?主权在人民那里。政府能提供好的服务,人民愿意让渡一些权力给政府,政府就有权。如果说这件事儿政府已经管不好了,人民发现现在有个新技术能让我们自己管自己,那就可以把这部分权力收回来。
可是难道政府就不知道利用新技术吗?
上世纪九十年代,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有些思想家曾经有过崇高的、乌托邦式的期望。1996 年,有个美国诗人叫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公然发表了《赛博空间独立宣言》,声称网络空间永远不需要受到法律的规制和政府的管辖。
当时中国的互联网还不够发达,巴洛显然不太了解中国政府。“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当然美国政府也是这个态度。事实证明独立是一个过于乐观的幻想,而且政府也很善于使用新技术。互联网给了人民更多的选项,同时也给了政府监控人民的办法。调取人民隐私数据的事儿,美国政府可是没少干。
所以新技术对政府的制衡,其实是处于某种“边际”状态:可能稍微再往这边偏一点,人民就赢了;稍微再往那边偏一点,政府就赢了。
但是提耶尔还是比较乐观的。总体来说,科技越发达、创新活动越多的地区,人民的自由度是更高,而不是更低了。是,你现在访问一个什么网站都有可能被政府知道,但你现在毕竟有可能访问那些网站。你足不出户就可以做一些事情,以前的人可没有这个选项。
而且别忘了全球化。消费者不一定能选择政府,但是跨国公司可以选择政府。技术进步使得跨国公司在各国之间搞“制度套利”变得更容易了,你美国的政策不好,我去日本干。
我们看美国政府打压华为,听起来好像是政府比跨国公司厉害,其实不然。现在的局面是世界上也只有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有能力打压跨国公司,而且美国也只是暂时地、在芯片这个极其特殊的点上,打压一下,而且可能还成功不了。
跨国公司在各国选择有利于发展的好政策,各国政府为了吸引跨国公司而纷纷自我改革,这才是大局。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再想想,现代政府的思维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
政府的本能思维是控制。最好一切尽在掌握,如果不掌握就很焦虑。有时候甚至以敢“亮剑”为自豪,把“能管”当做宣示主权的方法,仿佛不管就成了丧权辱国。有时候为了发展经济,会策略性地把管制放松一点,完了还是想管。
我认为政府部门应该克制自己这个本能。政府的职能不是“管”,而是“服务”;目的不是“可控”,而是“发展”。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都充满企业家精神,忙前忙后招商引资,那真是把自己的地盘当做公司一样去经营。
如果政府保持这样的企业家精神,那么法规其实是一种竞争手段。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法规,允许人民搞搞制度套利,这样最有利于系统的良性演化。
这个电影在内地放的是删节版,你可以去香港看完整版。市区不让飞无人机,乡村你随便飞。你不喜欢浙江的智能机器人伦理政策,欢迎你来黑龙江。这不是很好吗?
美国的联邦制度本来最有利于各个州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像亚利桑那州和加州那样用法规竞争。可是提耶尔说现在这个局面还是不行,各州的政府都在变得越来越失去活力,然后大家最愿意干的事儿是向联邦政府要钱。
四、共治时代
去年有一阵子,电视剧《清平乐》热播,人们对宋仁宗那个时代产生了强烈兴趣。有一位专爱写宋朝的历史作家叫吴钩,同步出了一本书,叫做《宋仁宗:共治时代》。而“共治”这两个字,说起来可是中国政治的大智慧。
所谓共治,就是皇帝不能说因为江山是我家打下来的、现在我有兵,就得我全说了算,你可能读过布鲁诺·德·梅斯奎塔和阿拉斯泰尔·史密斯的《独裁者手册》(The Dictator's Handbook: Why Bad Behavior is Almost Always Good Politics),任何人都不可能独自统治,统治者必须跟一个集团共同享有政权,共同治理国家。
隋唐以前,中国统治者是与贵族共治天下。你要想当官,读书确实也重要,但是家庭出身更重要。或者是皇亲国戚,或者是世家大族,权力总是掌握在很小的一个圈子手里。有时候贵族的势力太大,皇帝本人反而没权。隋唐以后中国有了科举制度,再加上像安史之乱这样的大动荡把贵族世家都整没了,到宋朝,才叫“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皇帝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专断,都得跟士大夫商量着办。如果文官集团那里通不过,皇帝说的话也不好使。
当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不是人民民主,士大夫也是一个非常小的集团。当初宋神宗用王安石变法,文官集团普遍反对,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百姓方便不就行了吗,我何必管士大夫高兴不高兴呢?但是时任枢密使的文彦博马上提醒他:「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士大夫并不代表全国人民,他们只代表自己,但是你这个政权依靠的不是百姓,而是士大夫。
如果非要搞什么阶级分析,那就是士大夫也好、贵族也好,都是“地主阶级”,都是与人民对立的,但阶级分析是个过于粗糙的工具。事实是跟“与贵族共治天下”相比,“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至少有两个先进之处。
- 第一,它是一个开放系统。不论家庭出身,只要读书好考取功名,任何人都可以做官。
当然家庭条件好的人更容易读书好,但是官员的家族传承可以回归平均,穷人可以基因变异,士大夫集团不是固定的,具有比较高的流动性。科举制度毕竟给全天下的读书人都提供了机会,那既然你有这么一个明摆着的出路,你何必冒险反对朝廷呢?
科举制度等于是搜罗了天下精英共同治理国家。宋仁宗赵祯本人并不像那些开国皇帝一样有什么雄才大略,根据回归平均的统计定律,他根本就不应该有,但是仁宗朝的政府之中却是拥有众多当时和后世都算是一流的人物,苏轼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再加上这个系统是“共治”,大家都能发挥,皇帝本人的才能薄弱可能反而还是个好事。
而事实证明只要朝廷能确保科举公平,共治政权就有很强的合法性。太平天国那么乱、满洲兵和绿营正规军都不堪用的情况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自己招兵,也要竭尽全力维护大清。
- 而与士大夫共治的第二个特点,可能更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借鉴,那就是它吸引进来的不仅仅是“新的”势力,而且是“业余”的势力。
科举选拔上来的都是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纯”读书人。科举考的标准教材,四书五经,都是所谓圣贤之道,本质上无用之学。这些读书人一上来对官场运作什么都不懂,但是他们有一腔热血,他们了解一点民间的疾苦,他们想要为百姓做事,他们是“代圣人立言”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看到不对的地方就想改变。
这些理想主义者不会办事,但是他们因为有功名,一上来就拥有压制那些专门办事的“胥吏”的权力。其实办事有啥难的?历练几年不会也会了。正是因为这些业余势力的制衡和反馈,国家的吏治才不至于败坏得太快,政府才不至于被利益集团彻底绑架。
我们看现在西方国家动不动就选一个军人、一个律师、一个医生、一个商人、一个记者、甚至一个演员当政府首脑,其实也是“业余人士”对官僚集团的制衡。他们能给政治带来新鲜空气。如果权力都掌握在那些官场老油条手里,国家就会毫无生气。
然而现在“科举”已成往事,“士大夫”已付笑谈,你要说我读书读得好,我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我要跟你们共治天下,那根本没人理你。尤其是现代政府的治理越来越专业化,只知道读圣贤书的理想主义者,既不掌握专业知识也不比政府掌握更多的第一线的情况和数据,根本没理由分享权力。
那么现代政府需要的新生力量和业余势力在哪呢?在创新活动之中,在企业家那里。这一章咱们继续讨论把亚当·提耶尔的《躲避的企业家和未来的治理》这本书。我读此书的感受是,现代政府应该与创新企业家共治天下。
注意,是与“创新企业家”共治,不是与“资本大亨”共治。提耶尔这本书写得很简单,全部的道理就是政府应该让创新者帮着改善治理。一方面是新势力进来确实有利于政府保持健康,另一方面也是技术进步太快,政府自己也的确跟不上创新的脚步,公司还可以在全球搞“制度套利”,所以“共治”是互相需要的结果。
共治不是说让企业家为所欲为,它首先就是对企业家的约束。提耶尔提倡的共治方法,是“软法规(soft law)”。软法规是一种广义的治理,它不仅仅是政府管制公司,也包括公司之间形成的行业规范、从业人员的道德自律、知识分子和老百姓的批评、当前社会自身的行为规范,可以是来自任何人群的任何制约方法。
企业家向政府要自由,但是企业家原本的自由也是人民给的。而人民的手段是市场。比如我们知道多年前 Google 公司搞了个增强现实眼镜,做得非常炫酷,功能强大,但是在市场上试用了一段时间就不了了之了,根本没有形成正式产品。为啥呢?不是因为政府不允许,而是因为消费者不喜欢。你带着 Google 眼镜跟人交往可以随时把对方的一举一动都录下来,而别人不喜欢这样。很多人明确表示抵制了之后,Google 只能取消。只要你总可以“退出”,企业家就翻不了天。
软法规的主要制定方式是“多方利益攸关方进程(Multistakeholder process)”。有时候是政府牵头,有时候是企业牵头,当前拥有这项新技术的各个公司和政府机构坐下来成立一个委员会,大家共同制定一套相关的政策。近年来比如像网络安全、私人数据安全的领域,都是用这种方法在管理。事实证明企业家是非常积极地在帮着制定法规,他们也希望自己的产品能让人放心。
现在各个行业都有公司的行业协会,有从业者的职业协会。这些协会为了维护声望,自动就会制定行业标准和职业道德,谁要是违反了,等于是会被整个行业所排斥。
而政府的权威,正好可以用在对公众的教育上。像转基因食品这些新事物,企业家说安全其实不好使,老百姓会说你是以营利为目的。政府根据科学家的意见,给一个官方的说法,效果就会好得多。
政府与企业家共治的方向必须是鼓励创新,特别要鼓励那些“先斩后奏”式的主动创新。为此提耶尔提出了几个观察和建议,其中有的在我看来很有技术含量,
- 一个是要增加竞争、去除壁垒、降低行业准入标准。什么许可证、执照之类,能取消的都要取消。如果说联邦政府已经取消了这个审批规定,你地方政府还在搞,那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也要给你纠正过来。
- 一个是尽量让市场磨合、而不是由政府先推出监管措施。政府要是先管,就很可能是保护既得利益集团。以前的工业革命和最近的信息革命都是颠覆式创新,旧的既得利益者说被颠覆就被颠覆了,这是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克林顿在九十年代放纵互联网行业发展,是他最大的贡献之一。
- 一个是应该给一些法规设定“保质期”。比如说法规颁布之日就规定它的保质期是三年,三年一到,要是政府部门没有重新颁布它,它就自动作废。
- 一个是对于新生事物,应该先假设它无害,然后谁要说它有害谁有责任举证,而不是让企业家先举证证明它无害。事实上有的政府部门,像 FCC,早在 1983 年就已经有这样的规定。但是提耶尔说这还不够,因为相关的规定也应该适用于政府部门:你这个政府部门要是想要监管无人机,你得先能证明无人机这种飞法确实有害才行。
- 一个是去监管利益均沾。以前国际贸易有个说法叫“最惠国待遇”,说你这个国家只要加入了世贸组织,那么你在任何一个贸易领域,给任何一个国家的优惠待遇,就应该同时给所有成员国这样的待遇。现在提耶尔说政府部门能不能也效法一下这个精神:如果你给任何公司一个放松监管的待遇,就应该给业务相似但是手段不同的所有公司同等的待遇。
总而言之,现代政府的健康治理已经离不开创新了。创新的本质是给世界提供活力。如果有一天从此不再有创新,一切生产方式都已经固定了,新公司就没有必要再出现,各大公司就完全可以搞世袭罔替,甚至全部收归国有,政府也完全可以把所有办事流程都固定下来,老百姓就只能该干啥干啥,那样的世界将是毫无活力的。
但创新不是开座谈会开出来的,不是学者畅想出来的,也不是政府推动出来的。创新是企业家冒着风险干出来的。我看搞创新的人比读书人更有资格参与治理国家。你要是想在现代做个能改变世界的人,你首先应该做个能自己去做事的人。
你做好了就可以成为 stakeholder,让政府也得听听你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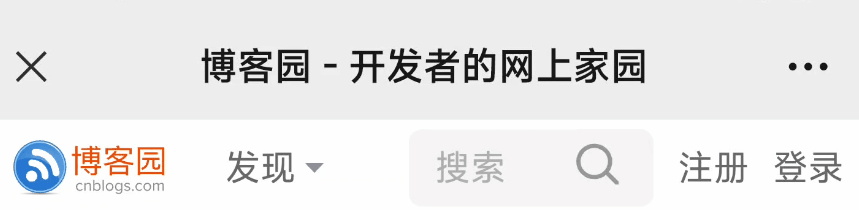
【推荐】国内首个AI IDE,深度理解中文开发场景,立即下载体验Trae
【推荐】编程新体验,更懂你的AI,立即体验豆包MarsCode编程助手
【推荐】抖音旗下AI助手豆包,你的智能百科全书,全免费不限次数
【推荐】轻量又高性能的 SSH 工具 IShell:AI 加持,快人一步
· AI与.NET技术实操系列(二):开始使用ML.NET
· 记一次.NET内存居高不下排查解决与启示
· 探究高空视频全景AR技术的实现原理
· 理解Rust引用及其生命周期标识(上)
· 浏览器原生「磁吸」效果!Anchor Positioning 锚点定位神器解析
· DeepSeek 开源周回顾「GitHub 热点速览」
· 物流快递公司核心技术能力-地址解析分单基础技术分享
· .NET 10首个预览版发布:重大改进与新特性概览!
· AI与.NET技术实操系列(二):开始使用ML.NET
· 单线程的Redis速度为什么快?
2019-12-22 进程注入行为检测技术初探
2019-12-22 Securityonion初探
2019-12-22 OSSEC HIDS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