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 动物凶猛 书摘
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孩子,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敞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
我可以无视僧恶者的发作并更加执拗同时暗自称快,但我无法辜负喜好者的期望和嘉勉,如同水变成啤酒最后又变成醋。
我喜欢用一把平平常常的钥匙经过潜心揣摩、不断测试终于打开那种机关复杂的锁。锁舌跳开“嗒”的一声,那一瞬间带给我无限欢欣,这感觉喜爱钓鱼的人很熟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攻克柏林战役的苏军老战士也很熟悉。
钥匙难道不是锁的天敌吗?
当人被迫陷人和自己的志趣相冲突的庸碌无为的生活中,作为一种姿态或是一种象征,必然会借助于一种恶习,因为与之相比恹恹生病更显得消极。
我感激我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的知识。我很同情现在的学生,他们即便认识到他们是在浪费青春也无计可施。我至今坚持认为人们之所以强迫年轻人读书并以光明的前途诱感他们,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
我一点不想最终晋升到一个高级职务上,因为在当时的我看来,那些占据高级职务的老人们是会永生的。
一切都无须争取,我只要等待,十八岁时自然会轮到我。
我是惯于群威群胆的,没有盟邦,我也惧于单枪匹马地冒天下之大不韪向老师挑衅。这就如同老鼠被迫和自己的天敌——猫妥协,接受并服从猫的权威,尽管都是些名种猫,老鼠的苦闷不言而喻。
我很小便很赞赏人们在窘境下的从容不迫和怡然自得。
那个黄昏,我已然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正常反应,视野有多大,她的形象便有多大;想象力有多丰富,她的神情就有多少种暗示。
人人手上夹着、嘴里叼着一支烟,一边吞云吐雾一边眉飞色舞地说话,很惹人注目颇有些豪踞街头顾盼自雄的倜傥劲儿。许逊递给我一支“恒大”烟,我便也站在街头吸了起来,神气活现地乜斜着眼瞅着仍络绎不绝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游行队伍,立刻体会到一种高人一等和不入俗流的优越感。
我在很长时间内都认为,父亲恰逢其时的死亡,可以使我们保持对他的敬意并以最真挚的感情怀念他,又不致在摆脱他的影响时受到道德理念和犯罪感的困扰,犹如食物的变质可以使我们心安理得地倒掉它,不必勉强硬撑着吃下去以免担上个浪费的罪名。
可能是腼腆的天性,或是从小就善于习惯于在执有坚定道德观的大人面前作伪,我一向能很好地掩饰自己的兴趣所在,愈是众目睽睽愈是若无其事。时至今日,这已经成了一种顽固的本能,常常使人误认为我很冷漠或城府颇深。
每个院落、每条走廊都洒满阳光,至今我对那座北洋时期修建的中西合璧的要人府邸在夏日的阳光照射下座座殿门、重重楼阁、根根朱柱以及院落间种类繁多的大簇花木所形成的热烈绚烂、明亮考究的效果仍感到目眩神迷和惊心悸魂。
其实那府邸在当时便已很颓败破旧了,朱漆剥落,檐生荒草,很多果木已经枯死或不再结果,金鱼池被暖气管道覆盖,殿门上的彩色镂刻玻璃大都打碎,一些有特点的建筑经过修补和翻盖已然面目全非。
她的这副腔调立刻使我如释重负,那明显的玩笑口吻和毫无半点羞惭的态度,使我觉得她什么都不会当真且问心无愧,过于荒谬的供认往往使人相信这一切都是虚构的。
我变得快活起来。
在其后的一周内,她的双唇相当真实地留在我的脸颊上,我感觉我的右脸被她那一吻感染了,肿得很高,沉甸甸的颇具分量。
这是猝不及防的有力一击。那天下午我一直晕乎乎的,思维混乱,语无伦次。但就在那种情形下,我仍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分寸,不使别人看出我心情的激动,如同一个醉酒的人更坚定地提醒自己保持理智。我以一种超乎众人之上的无耻劲头谈论这一吻,似乎每天都有一个姑娘吻我,而我对此早就习以为常。
这些穿着陆海空三军五花八门的旧军官制服的男女少年们在十多年前黯淡的街头十分醒目,个个自我感觉良好,彼此怀有敬意,脾睨众生,就像现在电影圈为自己人隆重颁奖时明星们华服盛妆聚集在一起一样。
既然我已经在一种势力面前低了头,我宁愿就此尊重所有势力的权威,对一个已然丧失了气节的人来说,更坏更为人所不齿的就是势利眼。
我多么渴望能遇见一个一起被捕的朋友,那样我便可以从他看我的眼神中观察到我是否暴露。如果没有,我发誓我要像那些仅有自首行为并未出卖同志或决心以后不再出卖的好人们一样,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成为最坚定、最不妥协的一分子。
他们已经骑上自行车,乱箭般嗖嗖地消遁于昏暗的街头。
只记得我在街上没命地跑,路边一些面相凶恶的赤膊大汉瞪着我;路灯昏黄的光晕下,一地赭红的完全粉碎的砖头屑;那个同学软绵绵地脸朝下俯卧在黑黢黢的墙根,形若一段短短的焦炭。
似乎还有他在一群人的紧紧追赶下近乎痉挛抽搐的奔跑姿态和格外惨白的脸庞以及黑洞般绝望的两只睚眦欲裂的眼睛,实际上我当时根本不可能从另一个方向迎面看到他的表情。
这就像一只勤俭的豹子把自己的猎获物挂在树上贮藏起来,可它再次回来猎物却不翼而飞。我对米兰满腔怒火!我认为这是她对我有意的欺骗和蔑视!
在我少年时代,我的感情并不像标有刻度的止咳糖浆瓶子那样易于掌握流量,常常对微不足道的小事反应过分,要么无动于衷,要么摧肝裂胆,其缝隙间不容发。这也类同于猛兽,只有关在笼子里是安全的可供观赏,一旦放出,顷刻便对一切生命产生威胁。
实际上也不是什么惊人的直觉,只不过是对自己的强烈期望信以为真了,而事实又碰巧和这期望吻合。
能过于专注的凝视常使我对自己产生怀疑,那里面总包含着过于复杂的情感。即便是毫无用心的极为清澈的一眼,也会使受注视者不安乃至自省,这就破坏了默契。我认为这属于一种冒犯。
我要不想被人当做只知听话按大人的吩咐行事的好孩子,就必须显示出标志着成熟的成年男子的能力:在格斗中表现勇猛和对异性有不可抗拒的感召力。必要的话,只得弄虚作假。
我在院门口等米兰时,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我一点也不感动,不是施教者不真诚抑或是这道理没有说服力,而是无法再感动了。类似的话我从不同渠道听过不下一千遍,我起码有一百次到两百次被感动过。这就像一个只会从空箱子往外掏鸭子的魔术师,你不能回回都对他表示惊奇。另外我也不认为过分的吹捧和寄予厚望对一个少年有什么好处,这有强迫一个体弱的人挑重担子的嫌疑,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造就一大批野心家和自大狂。
她对我一贯持友爱、亲热的态度,连笑容都是那么始终如一的甜蜜。对高晋则往往不客气,公开嘲笑他过火的豪迈与奔放。为他某一句不慎的言行,认真吵过几次架,生过几次气。有时还指使他跑腿,为她买些她临时想起来要用要吃的东西。
当我和高晋发生争执时,她便坚决地站在我这一边,逼着高晋对我让步。
对这一切,高晋虽然也不满也抱怨甚至不予理睬或消极不执行,但从没真动过火。他的脾气变得柔顺了,连汪若海有时挤对他,他也微笑听着不吭声。
他对我提起的这段往昔小插曲完全记不得了,说这种事经得太多了。我又问他米兰,他避而不答,顾左右而言他:
“多有名,传得越厉害的人我都不倦,再狂我也敢铲他。就怕那十六七的生瓜蛋子!
我为他们没注意到我的缺席深感痛心。
可那照片是真实的吗?难道在这点上我能相信我的记忆吗?为什么我写出的感觉和现在贴在我家门后的那张“三洋”挂历上的少女那么相似?
我何曾有一个字是老实的?
也许那个夏天什么事也没发生。我看到了一个少女,产生了一些惊心动魄的想象。我在这里死去活来,她在那厢一无所知。后来她循着自己轨迹消失了,我为自己增添了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
“怎么办?
这个以真诚的愿望开始述说的故事,经过我巨大、坚忍不拔的努力已变成满纸谎言。我不再敢肯定哪些是真的、确曾发生过的,哪些又是假的、经过偷梁换柱或干脆是凭空捏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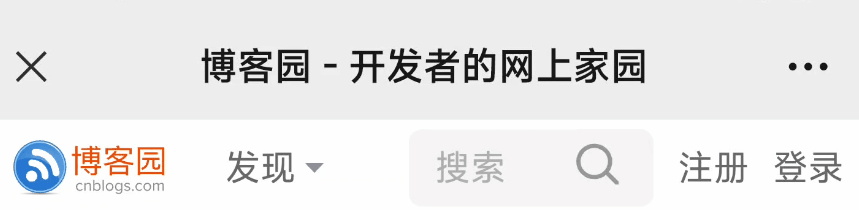
【推荐】编程新体验,更懂你的AI,立即体验豆包MarsCode编程助手
【推荐】凌霞软件回馈社区,博客园 & 1Panel & Halo 联合会员上线
【推荐】抖音旗下AI助手豆包,你的智能百科全书,全免费不限次数
【推荐】轻量又高性能的 SSH 工具 IShell:AI 加持,快人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