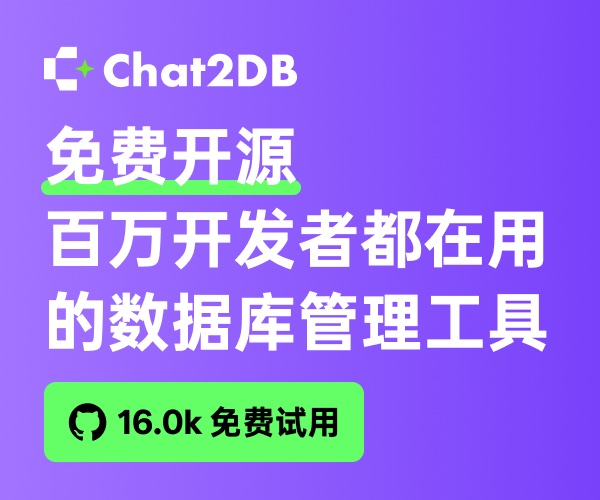梁鸿 梁庄十年 书摘
我们要走了。大胜母亲紧抓着大姐的手,她不愿我们离开。在她眼睛里,我清晰地看到死亡的倒影,看到她的恐惧。这是我从小到大在许多村庄老人眼睛里看到的。在村庄,死亡就是一次次公开的教育,让你对生命产生敬畏,同时,也慢慢习惯这样的无常。
春静的眼睛依然明亮。但是,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略微迟钝,缺乏必要的反应,那是被长期折磨后留下的痕迹。整个脸庞没有一点光彩,泛黄、僵硬,神情看上去很疲倦。她给人的感觉就好像心早已被击碎了,只是胡乱缝补一下,勉力支撑着活下去,再加上她略微沙哑、缓慢的声音,看着她,就好像她曾被人不断往水里摁。
这多么年,她一直在努力浮出水面,希望能够浴火重生,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她学佛经,识玉、卖玉,努力经营儿女的生活,也努力寻找新的爱情,那又是另一个艰难的故事了。
她一直在努力自救。
燕子说:“从小我那寡妇妈就告诉我,女孩子们就是一个‘芝麻粒儿那么大一个命’,撒哪儿是哪儿,地肥沃了,还行;地不行了,那你就完了。”
她的声音开始高亢起来,带着天然的道德和正义。那是吴镇潜藏很深却又一直被大家遵守的道德,一旦有谁逾越,便会遭受惩罚。这惩罚从来没人说出来过,也从来没人认为自己在执行,但是,你从被惩罚的人身上,一眼便能看出来。
我扭头看吴桂兰,她正在收拾地上的音响设备,把它们抬到东上,又把衣服一件件收起来。她身边的人们在聊天,两个人,三个人,好几个人,围拢在一起,专心致志地说话。所有人都背对着吴桂兰。
吴桂兰正处在这样的惩罚中。她被整个吴镇孤立和遗忘,被自己的儿女孤立和遗忘。她瘫痪在床的老头,是她被惩罚的显在标记。“谁和她说话?”即使是闲言碎语,吴桂兰也不配。也许,这是我这么多年来从没听说过她名字的原因。
我不知道吴桂兰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受到惩罚。她眼神中的渴望,她所弄出来的巨大声响,她三十年如一日地在吴镇大街上跳舞,似乎在反抗,也似乎在召唤。她兀自舞着,显示出自己的力量,也释放着善意和无望的呐喊。
“人家”,这里面包含着几层意思。一是,大家把自己从公共事务中摘了出来。村庄垃圾、房屋改造、坑塘恢复等等之类的事情,都是“人家”要管的事情,和我们这些普通人没有关系。二是,自动臣服于某种权力。“你想盖房,那非得找人家不行。”“那南水北调的工程,肯定是人家承包了啊,人家有权有势的。”在这里,梁庄的村民认同了村干部高于自己并且因此得到很多便利的事实。
因此,在梁庄人意识深处,存在着两个梁庄。一个梁庄是自己的家,自己院子和院子以内的那片地,每个梁庄人都花了大价钱来打造、修建;还有一个梁庄是“人家”的、公共的梁庄,一个宏观的、不可撼动的梁庄,跟“个人”没有关系。因此,在路边盖房的时候,都尽可能把自己的地基往路边推,哪怕自己过车也不方便。
这样一来,“人家”以及和“人家”相关的那部分梁庄事务就变成大家一起聊天议论时的对象,而不是与自已相关的生活。那么,谁来当村支书,梁庄怎么发展,梁庄的集体用地到底多少,北岗地是租还是不租,这些事就没有那么重要了。虽然,梁庄最后如何发展会涉及每个人的利益。
正月的最后一天,福伯去世了。享年八十五岁。
全家人齐心协力筹办福伯的丧礼。福伯的所有子孙,闺女儿子、女婿儿媳,外孙里孙,曾外孙曾里孙,共五十五人,全部回到梁庄。
福伯就埋在村头的自留地里。他在那块地里劳作了一辈子。他和福婶,一左一右,护在“老党委”两旁。在另一个世界,福伯仍做着妈妈的好儿子。
烧完“头七”的纸,福伯的子孙们,背着行囊,离开梁庄。
秀中熬过了歧视,熬过了贫穷,熬过了创业时期的艰难,最后,却倒在了那面墙下。凡事亲力亲为,这是他的信念。他不是不信任别人,他只是更相信自己。他的前半生都在和周围环境博弈,他被贫穷弄怕了,不允许自己浪费,不允许家人浪费,更不允许别人浪费。那一分一毫,都有他的血泪和汗水。
我也不敢想。我不能认同老六的推测。我不愿相信,那样一个宁折不弯的人,多少人劝都拉不回来的一匹野马,怎么可能自己去做自残的事情?
在我的记忆里,明太爷还是那个和我父亲彻夜长坐、沉默不语的中年人:漫漫冬夜,他们坐在堂屋的角落,守着一个燃烧的大树根,身体缩着,手伸向火。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彼此的慰藉是什么,我一直都很好奇。我是多么希望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大人,能感受到他们沉默中的交流。
如今,两个人都去了。父亲不用穿过半条街去找明太爷了。有时父亲担心找不到人,早晨五点多就起来去敲门,让他躲无可躲。明太爷也不必再承受朋友离世的伤心。明太爷在看到父亲棺材时那一刹那的苍白,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是突然意识到的分离和悲伤,是无所依靠,是两个相伴多年、已经成为彼此一部分的伙伴一下子被割裂开,那疼痛是直接且致命的。
但愿这两个好朋友,能在另一个空间找到彼此。
她又恢复了愉悦、轻快的神情,让大家站定,带头唱起来,声音清亮纯净。她的声音携带着某种奇怪的信息,慈爱,有回音,就像来自苍穹深处,那里有宽广的时间和空间。
我偷偷睁眼看了一下,灵兰大奶奶双手紧握,头微低,神情非常严肃、虔诚。我赶紧闭上眼睛,听着亲切的乡音,那乡音正在呼唤居于万物之中的上帝,让他看顾、祝福他的儿女,并救他们脱离凶恶。我感觉自己也慢慢进人到某种状态——无我的、舒缓的时间长流,无始无终的原初状态。我似乎有些理解,并且羡慕灵兰大奶奶了。
这座明亮的、干净的、被主照看的房屋,再也没有任何明太爷的痕迹。那个致命的水缸,连同他的修理器具、被褥衣服,满院的荒草、颓败,满世界的叫骂和不满,统统都被扔掉。
明太爷从这个世上彻底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