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Initial Prompts 初始提示
原作:由 苏尼尔·曼加尼 教授领导的项目研究过程
在准备图灵奖学金(2021-22)的申请时,我借鉴了三个主要提示,我将在下面列出这些提示,希望它们有助于构建阅读小组的讨论。 这三个提示的松散定义是: (1) Units of Meaning; (2) AI as Inter-discipline; (3) AI and Structuralism.前两个提示是具体的和最近的,而第三个提示则与长期兴趣相关。
(1) Units of Meaning:
2019年,我开始尝试人工智能(通过IBM在线工具)。我对人工智能后端如何基于相当普通的数据构建和关键字感到震惊。我们可以将人工智能视为尖端技术,但使其发挥作用所需的大部分内容涉及思维的基本方式和开发过程(甚至是模拟的工作方式);需要勾勒出具体的流程,标记具体的语言,并思考变量和概率。与此同时,我开始将福楼拜的小说《布瓦尔和佩库谢》渲染为一款文本冒险游戏(参见:textadventures.co.uk)。与书中两位抄写员的徒劳无功相呼应,他们从一个科学领域转向另一个科学领域,徒劳地试图获得更清晰的生活,我将这本书转换成布尔操作的文本冒险游戏的想法,终究是一项徒劳的任务。在小说的结尾,据说两名抄写员发疯了,最终又开始不加区别地抄写他们周围的一切文本(无论是重要的还是平庸的)。尽管这本书是十九世纪末写的,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把它视为互联网的预兆,因为它拥有大量的信息和“知识”。我的目的是提供小说的第一视角文本冒险,最终直接进入互联网的“荒野”。当然,整个努力需要大量(空闲)时间。从那以后,从那时起,我开始创作该项目的(基于印刷品的)“小说”,因为这似乎更适合其可能的受众。尽管如此,仅提供开头章节的游戏草稿仍然是一个有趣主意。 此外,在制作游戏时,我遇到了《AI Dungeon》,它最初于 2019 年底发布,是一款使用 AI 生成内容的文本冒险游戏。它是使用 OpenAI 创建的 GPT-2 自然语言生成神经网络的早期版本开发的,该网络允许界面生成原创的冒险叙述。它也许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更令人满意的多人游戏领域,这也许给了它更多一种“游戏”的感觉(讽刺的是涉及人类多人游戏方法)。然而,当我第一次接触 AI Dungeon 时,我对两件事感到震惊。首先,它确实能够有效地生成(看似)有意义的内容和场景。然而,我的第二个观察结果是一种不安,并不是因为我担心人工智能在生成文本方面可能同样有能力,甚至更好,而是因为不知何故,游戏玩法感觉漫无目的,甚至“不可思议”。它呈现了一个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的环境,表面上总是有意义的,但却没有任何目的感(就像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的《10.5章世界史》最后一章中令人不安的“梦”叙述)。这让我对人工智能提出了质疑,并且考虑了“矛盾智能”的潜力(从那时起我就根据福柯对相似顺序的解释进行了预测,他将其置于 16 世纪的思想中) 。
(2) AI as Inter-discipline:
今天,我们已经适应了大数据的事实,即大数据是“我们的”数据,提供了总体上并在所有可能性中描述和预测我们的模式。然而,正如凯特·克劳福德 (Kate Crawford) 在《人工智能地图集》(Atlas of AI,2021) 中所说,尽管数据集越来越大、计算能力不断增强,但我们并不一定能更好地了解自己。因此,不仅存在与数据的贪婪消费相关的生态问题,而且还存在方法论上的困境。虽然隐私问题理所当然是一个关键问题,但当我们深入了解我们的哪些数据被跟踪和计算时,往往并没有特别关注。分析粒度通常很粗糙,只不过是试图向我们推销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因此,仍然存在需要更仔细考虑的空间,需要更多地参与人工智能的设计和实施,以及至关重要的跨学科对话。凯特·克劳福德 (Kate Crawford) 在图灵研究所的一次活动中发表讲话(参见下一篇),赞扬了当代学术界日益增长的多样性(尤其是在性别方面)。然而,同样,她对某种跨学科对话精神的丧失感到遗憾,她认为,在二十世纪初,当人类学家在公共活动中与计算机科学家交谈时,这一点更为明显。她建议(未来十年迫切需要)将人工智能重新概念化为一门跨学科,并且必须扎根于每天受到这些工具影响的社区。 根据这一观察,我受到启发,重新思考我们如何理解数据及其“units of analysis”,这反过来又促使我返回并重新审视结构主义理论,特别是结构语言学和人类学,它在在各个领域也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3) AI and Structuralism:
一个特定的prompt,或者说思考,让我回到了我长期以来的兴趣:结构主义。事实上,这让我回想起大学时代阅读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对他关于使用计算机处理纸质计算的前景的简短注解特别感兴趣,他正在利用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神话数据进行计算。后来,这种兴趣与我对罗兰·巴特的长期阅读相结合,他同样提供了许多关于科学和计算的注解。尽管人文学科领域对结构主义提出了大量批评,但有理由回归其核心利益,尤其是考虑到当代计算、人工智能和自然语言处理的发展。这是相关的,例如,结构主义的愿望仍然与文化、语言和技术问题相关,以及这一早期思想史可能会影响我们近期的思维。列维-斯特劳斯热衷于控制论的发展,他意识到他的工作在统计上的局限性。例如,他的工作意义深远,为“思维结构”提出了一个案例。事实上,对于列维-斯特劳斯来说,结构主义并不是解释和梳理数据集。这是质疑自我和社会“结构”的一种方式。就他而言,在研究神话(来自世界各地)时,他考虑了神话(或数据)如何支撑我们的思维方式(而不仅仅是我们思维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能不会将数据视为我们身后的“踪迹”,而是我们存在于社会中的方式。
考虑到这些提示,该项目遵循 3 个相交的轨迹:
1. 首先,我们可以再问:结构主义的野心和抱负是什么?这些野心和抱负在控制论和计算的发展中处于什么地位?我们可以考虑与当代数据、人工智能和自然语言处理的争论有什么联系?
2. 我们可能会说,当今的艺术和人文学科范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结构主义的回应/反对。例如,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去殖民主义、女权主义、酷儿理论、新唯物主义、情感和后人文主义,都是对“units of analysis”(以及缺乏代理权)的结构主义批判性回应。这种批评的基础是什么?这与数据和人工智能当前的方法和实践有何关系?
3. 将这两个考虑因素放在一起,我们可以问,在重新思考我们对数据关系处理以及当今生活中数据的本体论地位的理解和发展时,结构主义的“回归”可能会带来什么。
总体而言,该项目响应了图灵研究所的两个战略目标:(1)方法论挑战领域; (二)公众参与工作。后者的方法是协作调查和公开的、公开的辩论。对于前者,该项目旨在为有关“在数据中寻找结构”的辩论做出贡献,并支持我们对“理论基础”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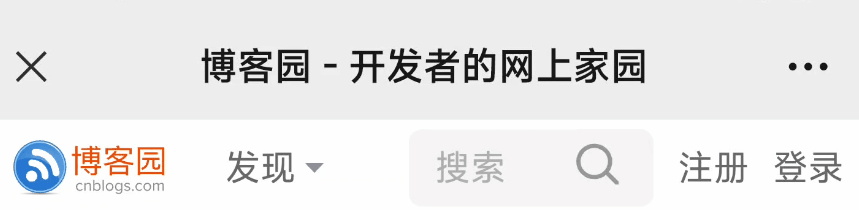
【推荐】编程新体验,更懂你的AI,立即体验豆包MarsCode编程助手
【推荐】凌霞软件回馈社区,博客园 & 1Panel & Halo 联合会员上线
【推荐】抖音旗下AI助手豆包,你的智能百科全书,全免费不限次数
【推荐】博客园社区专享云产品让利特惠,阿里云新客6.5折上折
【推荐】轻量又高性能的 SSH 工具 IShell:AI 加持,快人一步
· 清华大学推出第四讲使用 DeepSeek + DeepResearch 让科研像聊天一样简单!
· 推荐几款开源且免费的 .NET MAUI 组件库
· 实操Deepseek接入个人知识库
· 易语言 —— 开山篇
· 【全网最全教程】使用最强DeepSeekR1+联网的火山引擎,没有生成长度限制,DeepSeek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