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学家张寿武说起
华人数学家中,最有故事的我认为应该是张寿武和张益唐这“二张”。(年轻一代已经崭露头角,但这代人还有更多的可能,目前尚未积淀下可以总结的故事,“二张”是他们的上一代。)
张益唐的故事,我在之前的文章里写过了,导师不给推荐信,找不到工作,做过很多零工杂活,包括餐馆帮手、临时会计、送外卖……为生活所迫流落市井,数年间沦落到在餐饮店打杂,甚至在车里过夜。最后,他在经典的数论难题“孪生素数猜想”上取得重大突破,跻身第一流的数学家。丑小鸭变天鹅,“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张益唐
张益唐的故事说明,如果你运气不好,还是要相信个人的奋斗也很重要。
那个年代很多华人留学生都会遇到张益唐那样的困境,而像张寿武那样幸运的可能不多见。
张寿武的故事说明,运气特别好的人,也许会变成特别nice的人,最后带出出类拔萃的学生:37岁的张伟已经是麻省理工学院(MIT)数学系教授,33岁的刘一峰是耶鲁大学的副教授,加上37岁的伯克利副教授袁新意、2018中科院年度创新人物田野……
张寿武怎么运气好呢,我来列举一下。

张寿武
————
1、小时候大部分时间在田里放鸭子,乡里有100多人参加中考,5个人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他是5人中最后一名。
2、高考数学成绩只有79分,因为化学分数好分配到中山大学化学系,为了转专业,假装自己是色盲,被护士戳穿。拿着卷子向数学系的教授说明情况,最后数学系收了他。
3、为了赶化学系耽误的进度,数学系允许他只要通过考试就可以不修课,后来忘了收回这个政策,结果数学系只有他一个人所有的课都不需要考勤,只要考试合格就行了,他说:“这实际上给了我自学的时间。”
4、大学环境宽松,大一就给老师上课,原因他这样自述:
“这是特别好的运气,原因是第一次考高等代数时,考卷里有两部分题目,一部分比较抽象,一部分比较具体,其他同学都能做出具体的题目,但是做不出抽象的题目,只有我一个人能做出抽象的题目而做不出具体的题目。这时老师觉得很奇怪,让助教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我以前没有学过线性代数,只自学过抽象代数。这位老师也很想学抽象代数,但学不懂,所以让我和他一起学抽象代数,他给了我一本书,我学会后就给老师们作报告,当时还有两位副教授在听,所以,大学一年级时我们两个人就开讨论班了。这对我来说是运气非常好的事,因为当时没有多少大学生有这样的机会给老师讲课,能够自己学东西再给教授讲,这感觉很不一样,我就学得很快。”
5、考研复习,他不想重复性地做标准习题,读了波利亚(George Polya)的两卷《分析中的问题和定理》作为复习参考。
“我不喜欢做技巧性的事,喜欢做项目,一个东西要让我想两三天而不是一两个小时,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冬天时就参加考试,我的运气真是好,当时公共考试考分析和代数两项,几乎所有题目都在波利亚的书上,而且还有一道题出错了,我把题改过来后又解出来,自我感觉非常满意。”
6、很早就得到方向的指点
大学快毕业时,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一位数学教授到中山大学访问,张寿武的老师希望把他推荐给这位教授,但这位教授说:“你太年轻了,不要念这种代数,这是过时的东西。你应该念代数几何。”
7、“白送”的硕士学位
王元院士介绍德国青年数学家格尔德·法尔廷斯(Faltings)对莫德尔(Mordel)猜想的证明,说这个定理太漂亮了,证明也只用了30多页纸,但除了前言,他看不懂其中任何一段。他对王元说:“我要跟你念数论,我就念这篇文章,3年之内看懂这篇文章,你就给我一个学位。”王元说:“你看吧,看懂了就给你一个硕士学位。”
3年后,他念了一本标准代数几何的书,还是无法看懂法尔廷斯的论文,毕业时就“胡做”了一篇论文,“答辩完后,元老说,你讲的东西我们一个字也听不懂,但考虑到你每天8点之前就到办公室,很用功,这个硕士学位就送给你了,以后要靠真才实学才行。”
张寿武后来评价导师王元院士“是一个极为开明的老师。”
“他本身研究解析数论,是个大专家,居然允许自己的学生完全不做自己的东西,放在今天,他的这种度量、这种气派也是很了不起的。”

王元
(这里补充一点我的看法:王元、陈景润他们基本上把解析数论中的方法用到了极致,而要解决更困难的数学问题,就不能停留在这里。陈景润先生那代人今天依然被纪念,也有人指出他们不算一流的数学家,这要看从什么角度、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从当时的条件和背景来说,那代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从小学四年级读到有关陈景润的报告,数论研究这个梦想就在张寿武的人生中扎根。)
8、因为机遇到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的哥德费尔德(Goldfeld)教授到数学所访问,王元让张寿武陪他。哥德费尔德作报告时,张寿武就坐在第一排,不停地帮他擦黑板。但在陪他到故宫时,张寿武紧张得不得了,因为除了数学,他不会讲一句日常英语,于是便带了一本英汉字典。

哥德费尔德
在故宫买了门票后,“我发现我的运气又来了,故宫上所有的说明都有英文,不用我说一句话。我就跟在他后面,然后开始讨论数学,给他谈法尔廷斯的论文。这时我发现他完全不懂代数几何,但对我做的东西非常有兴趣。我问他我应该念什么,他说,你应该去念日本数学家志村五朗的一本书:《自守函数算术理论的介绍》”。
哥德费尔德回去后,张寿武好不容易在图书馆找到这本书,但没能念懂。这时,他开始申请出国了。他最想去的地方是普林斯顿大学,因为法尔廷斯在那里,但王元希望他去哥伦比亚大学跟哥德费尔德。后来不知为什么,他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的资料全丢了。有一天,哥德费尔德写信告诉他没收到材料,问他是否还愿意到哥伦比亚,他说:“愿意。”
结果,哥德费尔德亲自找来申请表填上,又找人写推荐信,这时王元正好在美国,他对哥德费尔德说:“张寿武是我们中国最好的学生。”张寿武的托福考了480分,当时满分是600,录取线是550,他不敢将自己的托福成绩寄过去。一段时间后,他收到了哥伦比亚的录取通知书。
9、三见法尔廷斯,“我终于感动了我的上帝”
到哥伦比亚大学,哥德费尔德建议他学自守形式,并给了他一篇文章,让他念完后做一个Gross-Zagie公式。他花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没有做出来,就对哥德费尔德说:“我做不出来,我不跟您做了,您推荐我去普林斯顿跟法尔廷斯做吧。”哥德费尔德说,不做也行,并为他到普林斯顿写了推荐信。哥德费尔德在给他的推荐信中说:张寿武在哥伦比亚学得很好,基本上不需要到普林斯顿。
张寿武专程到普林斯顿见法尔廷斯,法尔廷斯同意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他很高兴,将自己所有要说的英语全部写下来、背熟。在会面时,他对法尔廷斯说:“我很崇拜您,读过您的文章,也读过很多书。”半个小时很快到了,法尔廷斯没有说一句话,站起来就离开了,张寿武很惊讶:“他显然对我一点兴趣也没有。但他毕竟还是给了我半个小时。”

法尔廷斯
他郁闷地回到哥伦比亚大学,但还是想学法尔廷斯的学问,即算术代数几何。
他重新跟了一位现代自守形式的专家贾戈尔(Jacquet),贾戈尔每两个星期见他一次,并将自己算的东西给他。“他已经算了40多页,让我再算60多页就让我毕业,可我还没有开始算,再这样下去,他都会帮我算完。”于是,他对贾戈尔说:“我不能再跟你念了,因为你太好了。”
法国数学教授斯匹若(Szpiro)到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半年,他是张寿武见到过的最风趣的老师:
“每一两年他就要来美国一次,我跟他在一起特别轻松,他的英文很差,我的英文也很差,只有他没有说过我的英文差。上课时,他一手拿香烟,一手拿粉笔,偶尔搞错了,就把粉笔放到嘴里,用香烟在黑板上写字。他把数学讲得特别简单,但思想特别深刻,却没有任何技巧。法尔廷斯是在见到了他后受到启发,才证明了莫德尔猜想。”
斯匹若回到法国后,张寿武就没有老师了,他写信给斯匹若:能不能让我跟您念书?能不能给我一个题目?斯匹若回信给了他一个题目,只有半页纸。张寿武很用劲地做,还是做不出来,但因为他跟哥德费尔德学过两个月,跟贾戈尔学过一年,所以他算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有30多页。之后,他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参加一个活动,在酒会上第二次见到了法尔廷斯,“我告诉他我学了好多数学,有问题向他请教,希望引起他的注意”。但法尔廷斯只回了一句“不知道”,就离开了,这让张寿武很尴尬,“他一点都不在乎我”。
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后,张寿武将所有的东西都写出来,有了两篇比较像样的论文,这时斯匹若特别高兴,并在法国高等研究中心给他申请了一个博士后职位,尽管这时他还没有获得博士学位。
在法国高等研究中心,张寿武第三次见到法尔廷斯,并将自己的文章给他看,“他看后很高兴,对我笑了一笑,这是三次见面中最友好的一次,但还是没有说一句话,但这时我已经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是我最崇拜的一个人,我终于感动了我的上帝。实际上他当时只有35岁,他32岁时获得了菲尔茨奖”。
10、跟着法尔廷斯,这辈子真正学会做数学了
在普林斯顿,张寿武第一件事是问法尔廷斯能不能给他一个题目,法尔廷斯只讲了一句话:“容易的题目我都做了,剩下的都特难,比如黎曼猜想。”张寿武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种日尔曼人式的幽默,觉得很难受。
但突然有一天,法尔廷斯对他说:“我要开一门课,你记一下笔记,整理完后,我们一星期见两次,对照笔记。”
“以前学的都是零零散散的工具,没有经过大家的指点,那一年跟大家念了一年,那一年对我这辈子来说都极为重要,他的风格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法尔廷斯在课堂上讲了一位法国数学家Bismut的论文。
“这些文章特别长,基本上都是200到300页,很难念,但法尔廷斯就有这样的本事,他看了前言部分后,就有办法把别人做了多少年的东西都造出来。我觉得我没有这样的本事。”
有一次,张寿武问法尔廷斯一个分析的问题,法尔廷斯要他到图书馆去查3卷书,告诉他答案就在里面,并让他第二天给出答案。这3卷书每一卷都有1000多页,张寿武花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找到需要的那一页,于是决定自己算。
“我第一次发现自己也能算出来,特别得意。这时我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数学的,他不是哪里不懂查哪里的文献,而是哪里不懂就做哪里。后来我说,法尔廷斯做数学碰到一座山,一般人是爬雪山过草地,找一条近路走走,但他是用推土机将山推平了或者用炸弹给炸掉,他不会用技巧来做这件事,他完全是用力量来做的,他是那种力量型的,这是我在数学家中唯一见到的风格,他的力量太大了,这对我的影响很大。”
在普林斯顿跟法尔廷斯学了一年,张寿武学会了怎么做数学:“不是在图书馆里把别人的东西筹一筹,把别人的数学联在一起,而是从最基础的地方去做。”
他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博士论文答辩,法尔廷斯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也到了哥伦比亚大学,这在数学系引起了轰动,因为有时系里请他作报告他也不一定会来。
在美国申请职位很难。张寿武问教授们应该申请多少所学校,哥德费尔德说:“我的学生要申请100所,你应该申请75所。”斯匹若认为75所太多了,35所就够了,但法尔廷斯说:“一个就够了,你要去哪里?我给你写推荐信。”张寿武没有那么自信,他还是申请了30多所学校,结果哈佛、普林斯顿、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等都同意给他职位。
“法尔廷斯说得对,其实我就想去普林斯顿大学跟他再做几年。所以,我就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中心做了一年。接下来的3年里,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助理教授,大学给我的职位再加了3年。”
11、不用为求职、买房这些事烦恼
张寿武回哥伦比亚大学求职,作了一个报告,发现还有3个人在竞争这个职位,他们都很出名。报告作完了,哥德费尔德把他骂得一文不值:“你没希望了,你的英语太差了,那3个人肯定比你好。”
张寿武很愤怒,回到普林斯顿后,他发誓永远再也不回哥伦比亚大学了。然而,在一个多月后的圣诞节前夕,他突然接到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主任的电话:我们给你这个职位了。“这简直不可思议,因为这期间没有任何人跟我谈到这件事。”他说,“后来哥德费尔德解释说,我们看了所有的推荐信,你的最好,我们只能要你。”
张寿武准备回哥伦比亚,他发现自己租不起房子,看中了一幢房子也买不起。这时,哥德费尔德问他差多少钱,他将自己的存款数抄给了他,没想到哥德费尔德去找哥大的副校长了,上午去,下午就拿回一张支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只有一句口头协议:这钱是用来买房子的,不能买车。两天后,他用学校的首付款买下了房子。
就在买房子的那几天,他证明了广义波戈莫洛夫(Bogomolov)猜想。
————
张寿武的人生经历,确实是天才加幸运。他说过:
“我本人该算是个幸运儿。我小学、初中教育条件比较简陋,语文、英语老师都没有配备,但正是这极差的教育环境给了我自由的空间。初中时,就有时间凭自己兴趣读了几本高等数学书,使我的数学天分很早得到了发展,要是我的中小学课程也像今天的孩子们这样繁重,是很难有这种发挥潜质的机会的。”
这可能说明了:他的好运,他遇到的这么多开明的导师,和他最终也带出这么多好学生之间,是有关联的。
大部分人,在中国的体制下,从小学开始学到研究生阶段,还没有为数学研究做好准备。中小学阶段学的数学是欧洲中世纪的数学,大学本科数学专业学的数学是从工业革命到19世纪末的数学,研究生阶段要补习20世纪的数学,才能为研究21世纪的数学做准备。
怎么学好数学(从数学家的角度,而非应用数学的科学家或工程师的角度),张寿武说过一段话,对年轻人特别有参考价值:
“现在的年轻人如果要想学数学的话,我想他要知道现在数学家在想什么事情,他要尽早地弄清楚,根据问题本身设计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项目,就像计算机一样。计算机有一个硬盘,装什么东西是自己装,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有用往里放一下,那个东西也放一下,那差不多一个月之内你的硬盘就装满了,里面什么都放下了。我们每个人就是一个硬盘,知识就是放里面的,其实放得越少越好,你要把那些东西放得恰好可以解决那个问题,而且是速度比较快。所以这个没有一个明确的办法。如果只是说想学数学,对于学数学想做什么问题,你却不知道,这就没办法了。通常是学生问一个老师时,老师不告诉他该做什么,他说你先把基础打好,这句话是很糟糕的,为什么呢?这意味着老师教的所有的课你都得学好,现在时间还早所以你要把基础打好,就是说你的硬盘还很空,你可以往里面放,再放,其实数学有些课学不学无所谓。现在数学运算用的差不多都是19世纪的,一个数学分析,一个线性代数,其他的基本上都可以不要,想用的时候再去学,两个星期就学会了。一般任何一门课的基本原理不超过两个星期,但只不过学细了、学会怎么运算要花很长时间,这个是另一回事情。所以这个是我对于想做数学家的人的忠告,一定要小心你要干什么。”
中国学生把各门功课都学好,把基础知识学得非常细、非常扎实,这样的制度有优点,也为我国大量的工程师人才队伍奠定了基础。但中国的发展已经走到了创新的无人区,对最顶尖的一批人来说,这样的制度是不利的,他们需要因材施教,而不是陪大家一起在中世纪数学耽误时间。
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对所有人有利,听说现在有些家长,不仅要老师上课一碗水端平,如果别的孩子开小灶、上兴趣班,还要各种举报。中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大部分人都不会为吃饭、为生计发愁的阶段,但如果和张寿武那个时代的境遇相比,我们难道倒退了?
在很多方面,我们确实更规范了,张寿武那种拿自己的高考试卷去说服数学系教授的情况,是不可能再现的,这是多数人的幸运,也是少数人的不幸。
用张寿武的话说:
“我们国家能用最少的资源培养出很多人才。但想要用最少的资源培养出高尖端的人才,我想这不现实。”
制度总是有得有失,个人的命运,也是一样。
张寿武谈过张益唐:
他对数字敏感的不得了,你给他打个电话,两年后你拿起电话他就知道你是谁,不记下来,他没有本子,完全靠脑子。但是他也喜欢诗词,他一般不说话,喝酒喝到半斤的时候,一说话嘴里全是诗词,俄罗斯文学,他是55年生的,文学功底和数学功底都很好。
而谈到自己,他说:
我现在觉得最欠缺的地方是,我现在没有时间读小说,我也不知道现在有什么作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惜的地方。我过早的时候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数学方面,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知道是不对的,但现在也已经没有办法去改变了。我希望自己变成另外一种人,每天晚上睡觉前能读几本小说,读几本历史书,从不同的角度获取灵感。我读了太多关于科学的书,所以我自己坚决不会再建议其他人跟我一样。
幸与不幸,最终还是取决于每个人对自己的规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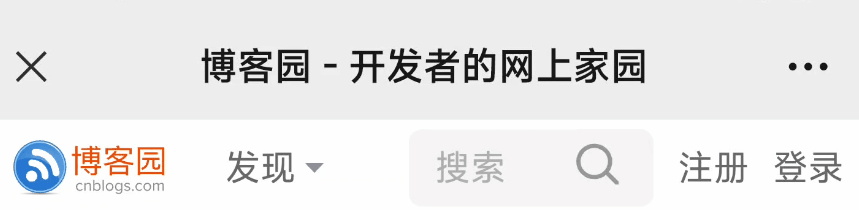
【推荐】国内首个AI IDE,深度理解中文开发场景,立即下载体验Trae
【推荐】编程新体验,更懂你的AI,立即体验豆包MarsCode编程助手
【推荐】抖音旗下AI助手豆包,你的智能百科全书,全免费不限次数
【推荐】轻量又高性能的 SSH 工具 IShell:AI 加持,快人一步
· 探究高空视频全景AR技术的实现原理
· 理解Rust引用及其生命周期标识(上)
· 浏览器原生「磁吸」效果!Anchor Positioning 锚点定位神器解析
· 没有源码,如何修改代码逻辑?
· 一个奇形怪状的面试题:Bean中的CHM要不要加volatile?
· 分享4款.NET开源、免费、实用的商城系统
· 全程不用写代码,我用AI程序员写了一个飞机大战
· MongoDB 8.0这个新功能碉堡了,比商业数据库还牛
· 白话解读 Dapr 1.15:你的「微服务管家」又秀新绝活了
· 上周热点回顾(2.24-3.2)
2018-09-13 无缘诺贝尔奖的George Dantzig——线性规划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