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山丰的一生
Yutaka Taniyama and his time
第一部分
谈及谷山丰的一生,我们首先要追溯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值得注意的是,那时日
本的情况与现在完全不同,更不能与现在甚至那时的美国和欧洲相比。“污染”还没有成
为像现在这样家喻户晓的词汇,在天晴日丽的时候,从东京市中心甚至可以看到向西70公
里外的富士山在朝阳中皑皑的山顶或是晚霞中的巍巍的轮廓。伴随着战争的灾难与离别的
年代已成为过去,但并没有被忘记,至少不再忍受饥饿。整个国家开始变得朝气蓬勃而充
满希望,尽管依然贫穷。这一点无论在整体还是个人都体现出来。谷山和他所在的那一代
人同样如此。当然,无论对于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人们在创业伊始,总是注定要与
雄心和贫穷相伴。
与那时的其他人相比,谷山他并不是特别的穷困。我想他一直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经济问
题,尽管他的生活决谈不上舒适,就如同我们大部分人一样。至少,他也均匀的分享了那
个时期广泛存在的贫困的生活。例如,他住在一间81平方英尺(7.5平方米)的单人间公
寓里,带有一个盥洗池,门后有一小块没有铺地板的部分。每间房间里都有独立的自来水
,煤气和电力供应,但是厕所每层只有一间。然而,在这所两层的公寓里,每层大约有1
2间左右的房间。至少我记得他住在二层的门牌号为20的房间,很靠近最后一间。这事实
上更像是宿舍而非公寓,但是这确是那时的普遍情况。如果要洗澡的话,则需要去公共浴
室,从他的公寓走几分钟即可以到达。澡堂是一栋破旧的木质建筑,却拥有一个诗情画意
的名字:宁静山庄。但这似乎只表达了一个还未实现的梦想,因为这做建筑位于一条狭窄
的街道中,而且街道的两旁汇集了喧闹的零售商店。而在街道旁边是一条铁道,每隔几分
钟便有列车呼啸而过。那时还没有集中供暖系统,空调更是不可想象。但是东京那不可计
数的咖啡馆在人们需要的时候,却可以提供些奢侈的凉爽。同样,那里也是探讨各种数学
与非数学问题的良好场所,咖啡只要50日元一杯。那时1美元合360日元,而谷山作为东京
大学的讲师一月的工资不会超过15,000日元。
对于家政,他似乎总是很懒散。至少他很少下厨,他总是喜欢到小店里去吃饭。在他所喜
欢的西餐中,有一道是炖舌头,250日元一盘。对于其他的高级西式菜,偶尔他才可以选
择那些最便宜的好好享受一番。除了夏天,他总是穿这一件闪烁着奇怪金属光泽的蓝绿色
的套装,我甚至想说这是他唯一的穿着。有一次他向我解释了这件衣服的由来。他的父亲
从小贩手中以极其便宜的价格买到了这件衣服的布料。但是由于这奇怪的金属色泽,家里
没有人愿意穿。最后他自愿让人用这个布料为自己做了这套衣服,因为他并不在意自己是
什么样子。他的鞋带总是松开的,并且总是拖在地上。由于他无法保证鞋带总是系紧,所
以当鞋带松的时候,他干脆就不再管它。
这就是一位早早的离开了他的生命里程的数学家,为他的同辈以及后人留下了永恒的激励
。
Yutaka Taniyama(谷山丰),出生于11月12日,1927年。他是他母亲Sahei, 和他父亲K
aku Taniyama的第三个儿子,和第六个孩子。同时他有三个兄弟和四个姐妹。而他父母都
很长寿,活过了九十岁。他的名可以表达为一个中国汉字,而且他曾经告诉我可以发音为
“Toyo”。但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似乎本来也应当这样发音。但是当他长大以后,他身
边的人,除了他的家人,都将它发音为“Yutaka”。随之他也接受了这样的称呼,从此他
就成了“Taniyama Yutaka”。至少他总是在文章上属这个名字,当然有时会是相反的顺
序。我对他的童年生活,以及国中时代几乎一无所知。唯一清楚的是在读高中时,他曾经
因为染上肺结核而休学两年。而在我的记忆中,每隔10到15分钟,他就会开始咳嗽。
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位知名的儿科医生,且对于大部分的病,都能够开药治疗。这事实上是
当时日本最为需要的医生职业类型。我只见过他一面。他在他八十多岁的时候,依然充满
活力,而我认为他应当属于那种自力自强的人。我们见面不久,他就给我在东京大学的一
位同时去见他的同事来了封信。这位老先生似乎认为我的同事在学术上并不成功,他建议
我的同事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B(或许是维生素C,当然也有可能是钙)的食品,这样对他
的脑力工作非常有利。由于这是在谷山丰去世之后,我已经没有机会去搞清楚这位父亲是
否也给他同样的建议。
谷山于1953年3月从东京大学毕业,尽管他的年龄比我大,我却是在1952年毕业。这是由
于他的疾病造成的。我在1950年时就认识他,但我们真正有了数学上的交往则要到1954年
初。当时我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归还第124卷数学年鉴,因为在那一册里有Deuring一篇关于
复乘法的代数理论的文章。谷山在几星期前将书借出。而在上一年的12月,我将我关于模
p约简代数簇的文章寄给在芝加哥的André Weil,并且我想将这套理论应用于阿贝尔簇,
尤其是椭圆曲线。在谷山给我的回信中,他告诉我他有同样的打算,并且礼貌的询问我是
否可以向他讲解一下我的理论。现在回想起来,他事实上有着更为广博的知识和更为深刻
的洞见,在数学上比我要更加成熟,但我当时还并不清楚这一点。
我依然保存着那张明信片,盖着1954年1月23日的邮戳。时隔三十年,明信片已经很旧了
,但是还是留有他清晰的笔迹。上面有他父母家的地址,他暂时住在那里。那是一个不起
眼的小镇,叫做Kisai。大约在东京大学以北30英里的地方,还是半乡村半城镇的样子。
偶然的,他出生于那里,成长于那里。而大概只有上帝才能预见到,五年半之后,我将在
那里一座庙宇的后面参加他的葬礼,站在他的墓碑前。
在我们通信期间,他是所谓的“特别研究学生”(special research student),而我则
是助理研究员(assistant),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如果真有什么不同
的话,那可能就是工资中的津贴有些不同。他在数学系,那里的教授负责本科三,四年级
的课程,而我则属于另外一个负责本科一,二年级课程的部门,位于另外一个称为通识教
育学院(College of general education)的校区。这种分隔是在此之前我们很少接触的
主要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我们双方在性格上都有些羞涩。但最终我们都成为后一个部
门的讲师。在他死去的时候,他已经晋升为副教授。
但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职位,我们在1954年到1955年期间事实上都是没有指导教师的研究
生。但我们却有教学任务,至少就我而言,相当于一所美国大学两门本科课程的教学量。
这种情况几乎适用于我们这一代所有的日本数学家。唯一的好处是我们大多数往往作为助
理研究员时便得到了终身职位。而无论怎么说,那些老一辈的数学家们都不具备指导学生
的能力。尽管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会时不时地给一些毫无意义的指导。有一次,我
们中的一员偶然的在火车上遇到一位五十多岁的教授,后者便问及前者的研究兴趣。当听
说他在研究Siegel关于二次型的理论,那位老人说到:“嗯,二次型啊。像你这样年轻,
可能还并不清楚,Minkowski在这方面有很多工作。”我的同事随后向我谈论了这件事,
他模仿着那位教师自大的样子说道:“我当然知道Minkowski的在这方面有所贡献,但是
他对Siegel的理论能有什么贡献?”我也曾经听到很多类似这样的无谓的建议和指导。
我觉得这些教授可能是在试图模仿他们的前辈,尤其是其中一位令人景仰的人物,他一定
做了很多这样的评论。但是我总倾向于认为大部分这种评论是毫无意义的。或者他们总是
试图以他们的方式表明自己依然在行,但却没有意识到像谷山这样新的一代早已超越了他
们。对于这一点,我们将随后给出证明。我必须说明谷山从未给过这种自以为是的建议,
对于那些比他年轻的人,他的建议总是专业而务实的。
不管怎样,我们都对这些滑稽无用的建议不予考虑,但把它们看作对我们的警示:我们无
法依赖别人,只有我们自己。确实,在这两代数学家中间的一代中,有一些已经成名或者
即将成名的杰出数学家。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是已经在国外,就是很快就离开了
日本。例如,Kodaira 和 iwasawa 在美国,然后Igusa 和Matsusaka 也随之而去。
在1950年左右,希尔伯特第五问题是一个经常谈论的的话题,而类域论的算术化,甚至是
格理论也被提及。但是上述问题却毫无吸引力,更多的人投入到代数几何的研究当中。在
那时,Chevalley 的《李群理论》和 Weil 的《代数几何基础》是两本被广泛阅读的书籍
。前者往往会被通读,而后者则一般会在完成前二十页的阅读后被放弃。
在他的本科时代,谷山就已经阅读了这两本书,以及Weil随后两本关于曲线与阿贝尔簇的
书籍。谷山曾经上过Masao Sugawara的《代数》这门课,他曾经写道Sugawara影响了他,
并使他步入数论领域。Sugawara是我所在的系里一位年长的教授,他曾经就复乘法,以及
高维空间的不连续群发表过一些文章。但是,我对谷山的这种说法感到疑惑,因为我觉得
Sugawara毫无创意,尽管我喜欢他并且尊重他的为人。但就我自己而言,在这段时间里,
我个人完全只受我的同代人影响,尤其是谷山。而这些人中,没有人超过三十岁。我想在
本质上,他也应当是这样。
事实也正是如此,他的学识往往来自那时许多学生自己组织的讨论班。他是那些讨论班动
力的源泉,并且如饥似渴的吸收这尽可能多的知识。他那时,也有可能是再晚一些的时候
,一定学习了Hecke关于狄利克莱级数与模形式的论文 Nos 33,35,36和38中的一部分。
当我们在同一个系里的时候,当我无法从图书馆得到相关杂志的拷贝时,他总是慷慨地将
这方面他的笔记借给我。
第二部分
他的第一个非平凡的工作是《关于阿贝尔函数域上n-分点的问题》,也许最终成为他四年
级时的论文,尽管那并不是必须完成的。由于这篇文章旨在我对他的一些个人的回忆,我
无意于在此细致的论述他的工作。所以我只简略的说这篇文章根据Hasse的一些想法,以
及Weil的一篇文章(数学年鉴 1951),给出了Mordell-Weil定理的一个证明。而在1953
年,他是日本唯一一位在此问题上具备相关工作的知识的人。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他在
Chevally于1954年春在东京大学举办的讨论班上,给出的关于这个工作的几个报告。
如前所述,他曾经一度对阿贝尔簇上的复乘法很有兴趣。他首先考虑了一条超椭圆曲线的
Jacobian簇的情形,最终归结于更一般的阿贝尔簇的情形。由于在这个领域里很多事情还
没有搞清楚,必须要面对许多困难而“奋力的战斗”,并且在不断的尝试与错误之间“艰
苦的求索”。他曾经说任何一个数学家在进行实质性的数学研究中,都会有上面描述的过
程。在他的数学中,几乎没有“徒劳无功”这个概念,至少他从未有过这样的观点。或许
在其他人看来并非如此,但是他却在“战斗与求索”之中找到了无限的乐趣。他在1955年
9月在东京-日光(Tokyo-Nikko)举办的代数数论研讨会上发表了他的结果。他在那里见
到了Weil, 并且吸收了Weil的一些观点。他随后发表了他关于阿贝尔簇和某种Hecke-L函
数的联系的文章的一个改进版本,那是那个时代的顶尖之作。(L-functions of number
fields and zeta functions of abelian varieties)
在那篇文章中并未包含的内容,以及一些与我合作的工作则开始列入计划,我在这个问题
上也取得了一些独立的成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一起工作,而合作的风格,以今天的标准
,可以被称为是“悠闲”的。我们的生活非常的放松,甚至说过于放松,相互毫无竞争可
言。这一点恐怕要被80年代的那些年轻数学家所羡慕。我们要感谢Yasuo Akizuki,因为
他说服我们为他任编辑的数学单行本系列丛书(Sereis of mathematical monographs)
撰写一册,从而加快了我们的计划。
在这段合作期间里,我经常去拜访他的“别墅”来探讨一些事情,因为那里比学校离我的
住处更近。他总是在夜里工作到很晚。我在1957年的日记写道:星期四下午,4月4日,2
:20 p.m.,我拜访了他的住宅,他还在睡觉,而他说他早上6:00才睡。另外一次,好像
是早晨晚一些时候,我敲他的门却没有回应,于是我就去了系里,花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的
火车路程。我在系里找到了他,对他说:“在此之前我去过了你的住处。”对此他则回答
:“嗯,那时我在那里吗?”他立即意识到他话中的破绽而感到非常尴尬,但是依然辩解
称:“你知道,那个时候我经常在睡觉的。”
我发现他在许多方面与我不同。例如,我一直是一个习惯于早起的人。曾经一段时间,我
认他更加理性化,而我总是随意而无常,但或许我是错的。但我们却有一些共同点:我们
都是一个大家庭中排位靠后的小孩。我是家里第五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我之所以提到
这一点,是因为我曾经很讨厌日本家庭中长子们那种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虽然他并不是那
种粗心大意的类型,但是谷山似乎天生就善于犯错误,而且绝大部分错误总是指向正确的
方向。在这一点我很羡慕他,却没有办法模仿他。对我来说,犯一个“好”的错误是何其
之难。
我们一起完成的《现代数论》于1957年7月出版。我们下一个任务显然是完成它的英文版
本。尽管我们需要以更好的形式完成它,但是我们对此却都丧失了热情。第一个显然的原
因是我们松懈了下来,因为总觉得我们至少已经写出了这本书,尽管是日文版。另外一个
原因则更加实际一些:今年秋天我将去法国,而这使我一直无法歇下来。然而,更加本质
的原因则可以引用书中前沿的一段话来说明:
我们很难说这个理论以其令人满意的形式给出。但不管如何,我们至少可以说:我们已经
在攀登的旅途中前进到了一定的高度,这使得我们可以回顾以往的脚印,并对最终的目标
有一定的认识。
用精炼的语言来说,我们必须寻找更好的表述和更加细致的结果。那一年,我们已经考虑
以adele的语言重写整个理论,或许本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我们并没有。另外,作为
一种心理反应,一旦人们证明了些什么,他总会倾向于去得到新的理论,而非去润色已知
的结果。确实,我们两人都开始对各种类型的模形式发生兴趣,而这条道路令人更加兴奋
。于是,我们在东京与巴黎之间的通信总是围绕这一方面的问题。在1958年的春天,他告
诉我一些新消息:东京迎来了Siegel和Eichler,他们将给一系列报告。前者的报告有关
二次型的约简理论,而后者则是有关他最新的研究工作。同时,在巴黎,Cartan的讨论班
开始围绕Siegel模形式展开。
我比他更加频繁的去信,而他在这段期间只回了两封信。在日期为1958年9月22日的第二
封信中,这也是他现存的信件中很晚的一封,他提到希尔伯特模形式和某种狄利克莱级数
之间的Hecke类型的关联可以由GL(2)的adele群来给出。但是,如同信中的语气所暗示的
,他的热情在减弱。他知道仅仅给出这种方法的可行性是远远不够的,这里需要一个真正
的突破。显然更多的工作需要完成;事实上他写道:由于天气太热,我已经一个月没有在
这上面工作了,但我马上会重新考虑它。或许给足够的时间让他去专心考虑,他会在这上
面成功,但是他永远地将这未完成的工作留了下来。因为他将在两个月后永远地离开我们
,而这无论对于寄信的人还是收信的人,都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
至于我们一起合作的工作,在他死后情形则完全改变,我将随后论述。而他将我独自留在
世间,我则将他未完成的工作看作我的职责。我尽可能快地去完成这项工作。尽管我对我
得到的计算公式并不完全满意,但最终在1961年的春天,“阿贝尔簇上的复乘法及其在数
论中的应用”这篇文章得以发表。文章的题目是他在一封信里建议的。我又花了十年的时
间从一个更好的观点来梳理这项工作,而后又花了五年的时间,如他所愿,采用theta函
数的方式论述了整个理论。但是,无论怎样,那个本应因此而感到高兴的男人,早已离开
了我们。
最后一部分:
谈及他的私人生活,以及他最后的日子,则首先要回到1955年。那时我们已经是同一个讨
论班的成员,而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他来到我所在的部门工作之后,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
亲密。而我们往往一起承担各种工作。例如,由于职责所需,我们要在某个办公室中一起
批改入学考试试卷,每人要分担超过5,000份。然而,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同样对考生
来说不幸的是,大部分试卷都是白卷。
在那些惬意的日子里,我们和许多其他的朋友一同分享快乐。在咖啡店中度过那些轻松的
时光,在周六的下午徜徉于市里的植物园,或者郊外的公园。在傍晚,我们则在那些专卖
鲸鱼肉的餐馆中用餐,而这在当时并不被认为是过于闲致的生活,在今天却难以想象。在
学校一天的工作之后,我们常常一起散步到很远,去拜访神道教的神社,买一些写在小纸
片上的“神谕”以自娱,那些“神谕”被认为可以告知我们的命运。
有一次我们一起在火车上时,他问我下一站的名字,我则回答:下一站将到达“车站”,
而再下一站则是“下一个车站”。这让他非常开心,因为他第一次听到这个笑话。而我则
不得不向他解释说,我只是模仿了那时收音机里一出流行喜剧的一段台词而已。他于是马
上就买了一台收音机,后来又有了一台唱片机和一堆的唱片。在我们前面提到的最后一封
信里,他写道:最近我一遍又一遍的听贝多芬的第八交响曲。我想这些和看电影大概就是
他独自一人时所有的娱乐。他很喜欢一部电影《国王与我》。我不认为他会演奏某种乐器
,更谈不上擅长运动。他不喝酒,不吸烟,也无嗜好。他并不热衷于旅游;甚或,在我看
来,他尽他所能逃避出游,或许这是由于他孱弱的身体。我想京都或许就是他一生中到过
的最远的地方了。作为一名受过教育的人,他一定读过那些经典名著。但对于那些日本或
国外的当代作家的小说,我认为他并非一名热心读者。他对历史也毫无兴趣,除非与数学
有关。
然而,他早年曾经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就一些学术上的相关话题写一些期刊文章。写作
涉及方方面面:像如何培养一名数学工作者,如何组织一个数学机构,对他人的一些旧文
章的评论,书评,等等等等。他写起这些文章来速度很快,写完之后也很少修改。或许他
是通过写作来梳理他的想法。他写作风格简单明了,比起他的报告来好很多。有时,他在
文章中会显得比谈话时显得更加兴奋。说实话,我觉得他这种喜好很可惜,这实在是在浪
费他宝贵的时间。而写每一篇文章的原因,都不足以然他花费如此多的努力。尽管我从未
向他鲜明的提及我的看法,但是有一次他听了我关于放任政策的一些看法,几天后他就给
我一份关于这个主题的粗略的手稿,其中讽刺了我在讲话时的仪态。我当然表示了不满,
他也就将那一部分删去了。
他对他的同事总是很友好,对那些比他年轻的人更是如此,他真诚地去关心他们的生活。
但是同样的,或许有些过于苛求,我想这也大大减少了他从写作中获得的乐趣。如果真的
如此,我对此并不会感到太惋惜。
我想我应当在这里结束这种散漫的对他生活的描写,而去回忆他最后的几个月。在那些时
日里,我们充满了青春的激情与愿望,可以说在各个方面,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生活
上。而谈及后者,我想那时的情绪可以用一句话概况:没有人会去相信包办婚姻——嗯,
几乎没有。或许我们中有人会认为,这种婚姻是为那些资产阶级们准备的,我们无产阶级
则应当鄙视这种邪恶的行为,当然这显然是夸大其词了。事实上,当我在1959年一个炎热
的夏日,大约是在他去世后八个月,和一些朋友一起给他的家里打电话表示慰问时,他家
里的长男,但也可能是他的爸爸,向我介绍对象,而对方则是一位知名画家的女儿。我随
之在一次舞会上尴尬的询问一位女伴该如何应对,她告诉我一本礼仪书籍建议人们应当如
此如此回答。我于是在回复中机械地重复了那些说法,但结果却是招致了一通大笑。而这
件事也就到此为止。
我曾经为一个想法感到好笑:这个女孩或许开始时也是准备介绍给谷山的。如果真的是这
样,我肯定会因次而与她结婚,尽管这个论点毫无疑问会遭到我夫人的嘲笑。但不管他的
家里是如何希望的,他自己选择了自己的伴侣,并最终获得了双方父母的同意。她的名字
叫铃木美沙子(Misako Suzuki).他常常愿意将她称为M.S.,对于她我将予以介绍。但是
我还是要先回到主题上来。
我想当他见到她时,她是他狭小而松散的社交圈中一位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我还清楚地记
得她在她母亲的帮助下,在家里举办的晚宴聚会。参加的人有谷山,山崎(K.Yamazaki)
,他的未婚妻,还有我。那是在我即将离开去法国的时候,在1957年的9月。这次聚会,
虽然是为我送别举办的,却十分平静,并不像在其它地方这种类型的聚会。我记得席间,
她就他的沉默寡言开玩笑。同样的五个人在这一年的4月也曾一起聚会,我想这几乎就应
当是他们两个人第一见面的时侯。那时候有许多这样度过的夜晚,只是随着情形不同,人
员也有所差别。
相对来说,美沙子是我的社交圈中一位新的成员,所以我一直并不是很了解她。她看起来
是那种典型的好女孩,来自于一个典型的中上阶层的家庭。她说话很流利,是标准的东京
口音。她是独女,并且要比他小五岁。当传来他们订婚的消息时,我有些吃惊。因为我曾
经模糊的感觉两人并不般配,但我却并未感到疑虑。
我随后听说他们一起租了一间很不错的公寓。他们一起为了他们的新家置办厨具,并开始
准备婚礼。在他们的朋友看来,一切充满了喜悦与希望。然而,悲剧却悄然降临了。195
8年11月17日,星期四,清晨,公寓(这是我们最先提到的那所)的房屋管理员发现他死
在他的房间里,在桌上留有一些纸张。他的遗嘱被写在其中三张纸上,而这些纸来自于他
经常用来研究数学的笔记本。上面的第一段这样写道:
直到昨天,我自己还没有明确的自杀意图。但一定有些人已经注意到,近一段时日以来,
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我都感到很疲倦。至于我自杀的原因,尽管我也不了解我自己,
但这决非由于某件特殊的事情,或者某个特定的原因。我只能说,我被对未来的绝望所困
住。或许有人会因为我的自杀而苦恼,甚至受到某种程度的打击。我由衷地希望这件事不
会为他们的将来带来阴影。但无论怎样,这实际上都是一种背叛。我请求你们原谅,将这
作为我最后一次以我自己的方式来行事。毕竟终其一生,我都在以我自己的方式行事。
他随后逐条列出了对于他的物品的安排,以及哪些书和唱片应当归还图书馆和他的朋友,
等等。对于他的未婚妻,他特别提及:“我愿意将我的唱片和唱片机送给她,如果她对此
并不感到烦恼的话。”他同时也说明了他所教授的课程“微积分”与“线性代数”的进度
,并留下了一份笔记,在上面他对这个举动所造成的不便,向他的同事们道歉。
就这样,在那个时代中一位最为杰出和开创性的数学家自己结束了自己的历程。那时离他
31岁的生日还有5天。
这无可避免的掀起了风暴,随之是葬礼,他记忆中所有的的亲友、同事聚集在一起。他们
都感到非常的迷惑,他们相互询问他自杀的缘由,但却找不到可信的原因。从他的未婚妻
那里,他们得知在那个不幸的早晨的前几天,他还打算去看望她。似乎上天注定他只能是
一个纯粹的数学家,而不能成为一个家庭中的男人。我最终以此来安慰自己,但那已是很
多年以后的事了。
不管怎样,几星期之后,人们慢慢地从震惊与悲痛中恢复了过来,似乎人们已经开始回到
日常的生活。然而,在十二月清冷的一天,美沙子在他们原本准备作为新房的公寓中自杀
。她留下了一份遗嘱,但从未公布。我只听说其中大致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曾相互承诺
,无论到哪里我们都会永远在一起。现在他离开了,我也必须离开去跟随他。”
当这一系列的悲剧发生时,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作为高等研究所中的一员。所以这些细节都
是我在1959年的春天回东京后,Kuga和Yamazaki告诉我的。谷山本应当在这一年的秋天去
高等研究院,而我也原本打算在那里再呆一年,但我最终选择了离去。
当我回家的时候,已是樱花烂漫的季节,眼帘中处处是深绿色的树叶。借助一句常用的描
述:春色轻盈的掠过。在我离开这这一年半里,东京的街道依然喧闹,依然充满世俗的气
息。但是人却不一样了。我也如此。尽管随后转型的那段时期即将到来,但在这晚春的日
子里,我只能无助的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已经无法再举办两年前那样的聚会了,那段快乐
激昂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我或许应当反问自己:谷山丰是怎样的人?这并不是去问及某个数
学史中的形象。我想说的是他的存在对于他的同代人,尤其是我,会有怎样的意义。自然
而然,我所写下的或许可以看作对这个问题的一个长长的解答。但如果简而言之,我应当
指出,写到这里,整篇文章无非是要说:对于许多跟他进行数学探讨的人来说,当然包括
我自己在内,他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或许他自己从未意识到他的意义。但是甚至与他在世
时相比,我在此刻能够更加强烈的感受到他那时在这方面高尚的慷慨大度。然而在他陷入
绝望的时候,我们却没有人给他以支持。每当念及于此,我都陷入令人心酸的悲伤之中。
小平邦彦谈数学—学习方法及其启示
已故日本数学家小平邦彦在《数学中没有捷径》一文中,通过自己学习数学的体会,谈了他对数学学习方法的理解,认为在数学学习中没有捷径可走。这似乎和今天我们所一直倡导而且也一直热衷于的学法指导又有相悖。数学的学习究竟有没有捷径可走?有没有规律可循?有没有方法可以指导?这已成为师生的共同关注的焦点。本文拟就小平邦彦的数学学习方法谈谈对我们启示。
小平邦彦回顾了他自小学至大学学习数学的心得体会及其思维历程。笔者认为,其主要学习思想不外乎两点:其一是熟记多练(熟背公式,多做笔记和反复练习);其二是培养对数学的感觉和理解。这两点其实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反复练习正是为了达到悟的结果及培养对数学的理解和感觉。用中国的一句成语来说就是熟能生巧。他认为数学的学习就是先认可已规定的公理、定义、法则等,然后反复证明练习,在不知不觉中达到对其的理解。譬如他提到对分数的除法三分之二除以五分之四,为什么要用五分之四去除时可以将分子与分母交换而去乘四分之五呢?就需要说明它的理由。但他学习算术时就没有这种说明,只学习这种规则,即用分数去除时可以将分子与分母交换后去乘,然后就在反复的计算练习中不知不觉地明白了它的意思,也就记住了。因此,也就能够非常自如地进行分数的计算及应用。为了理解数学的定理,一般是一步步循着证明的论证走,但对于证明不明白怎么办?他认为只要把不明白的证明抄写在笔记本上背出来,背出来不知不觉也就明白了,至少感觉到是懂了。他认为这种将不明白的证明在笔记本反复抄写,直到背出来为止,不失为学习数学的一种方法。而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数学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纵观他的学习数学的心得体会及思想方法,笔者认为有如下启示。
一、对数学的感觉和理解
1.小平邦彦对数学的理解
对于理解一说,小平邦彦颇有自己的见地。他认为在反复的计算练习中不知不觉地明白了它的意思,也就记住了,而所谓明白了它的意思,也并不是能够说明为什么用分数整除时可以将分子与分母交换后做乘法,而是指能够非常自如地进行分数的计算及其应用。可以说,这种理解,并非是百分之百的理解,而是知道应该怎样去做和如何灵活机动地去做,久而久之,也就渐渐地培养出了对数学的感觉。这种感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就是对数学的入门。即长久思考而不得其解的问题突然间豁然开朗,悟出了其道理。这个悟的过程,有的时候是渐进式的,即在半理解状态练习以加强理解,使理解逐渐深化;有的时候是突发式的,这便是顿悟的过程。特级教师马明老师谈到他对代数的学习及其对代数思想的理解便是顿悟的过程。那时他在学习《小代数》时,老师让他们计算长方形周长(已知长为a,宽为b),马明老师做出2(a+b),但他并不真懂,就问老师这个长方形究竟多长,老师看看他的书面答案,又看看他,半天说不出话来,马明老师又问:究竟有多长。老师说:你不是已经算出来了吗?马明老师坚持认为没有,老师又说:你不是已经算出来了吗?马明依然认为没有。在他想来,周长应是一个具体的数值,怎么会是一群抽象的符号呢?回家后反复思考老师的话,终于悟出一个道理:“用文字代表数,让未知数像已知数一样地参加运算”。原来代数就是这样!从此他的代数成绩直线上升,成为全班第一名。数学的学习本身就需要有悟的过程。有些知识需要老师详细讲解才能达到真正的理解,但有些知识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即单凭教师讲很难使学生达到理念的升华,这并不是说就完全削弱了教师的作用。而是说,学生真正去掌握知识,达到对某一数学知识的理解,并不是靠老师教出来的,而是靠学生悟出来的,将所理解的知识嵌入已有的知识结构中,也难以忘记。所谓的启发式教学、发现法教学等教学思想,其本质也无非是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达到对问题的理解和对知识的领悟。
2.东西方数学教育家对数学理解的不同观点
东西方数学学者及教育家对于先理解后接受知识,还是先接受知识再理解其意义提出异议。在第十二届国际数学教育心理学会议上,中国学者(丁尔升、张奠宙等),认为不要强调理解而忽视练习,其实理解了百分之六七十,就可以操作训练,在练习中增强理解。这和小平邦彦对数学学习的理解观点是相同的。而这一观点却受到英国资深学者Harte的反对。她说,对理解的东西进行操练才有意义,不理解的东西加以操练,时间一久就会忘记。这种歧义的产生可能缘于东西方文化背景、考试体制、教育方式以及思维特征的不同。日本和中国一样,也是考试盛行的国家。虽然他们进大学并不难,但进好大学仍有困难。而中国的考试文化导致应试教育更使得中国在教育上多强调反复操练。因此在对学习方法的理解上,东方侧重于从练习中理解,在半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练习以深化理解。而西方则更侧重于在完全理解的基础上再去练习、应用。笔者认为,作为东方文化教育背景下的中国教育,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象西方国家所倡导的方法去学习数学。依据我们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及特征,在操练前要达到对知识的完全理解是极少可能的。譬如口令立正,士兵未必理解什么是立正,但在强制下教会了,以后一旦听到“立正”口令,便会自动去做。这也恰是从做中理解的例子。目前,一些学生对数学感到难学,难以理解,且又容易钻“牛角”。如为什么要定义这个公理?公理为什么是这样而非那样表达?零为什么不能做分母?等一些在中学阶段难以接受的问题。教师除了要向学生解释这些原因,打开他们的思维结之外,还应让他们了解到在中学阶段要达到对问题的百分之百的理解是不可能的。但只要在练习中渐渐领会到数学的精神、思想和方法以达到灵活运用,那也就是我们所认为的理解了。
二、熟能生巧和题海战术
重新回顾小平邦彦的数学学习历程,无不贯穿着一个思想:反复操练、反复练习。他的这种思想似乎又和中国传统的题海战术如出一辙(即便在今天的数学教学当中,题海战术仍占有很大市场)。我们不否认题海战术有些成功之处,但其与小平邦彦的所说的反复练习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小平邦彦所提出的在反复练习中不知不觉理解,究其实质是熟能生巧。熟能生巧中的“巧”是反映了思维的创新性,是多次量变而引起质变的一个飞跃过程。正如灵感机制的发生,长久思考一个问题(包含有反复思考之意,有重复性),最终会产生灵感,这便是一个质变的过程。熟能生巧又遵循了心理学中的S—R反应理论。前提条件是要反复操练以引起刺激发生反应,这种刺激—反应达到一定程度,就发生突变,即从感性的认识达到理念的升华。熟能生巧与题海战术所不同的是前者有目的性。是为了达到对知识的理解和融汇贯通的程度而暂时进行的操练,而题海战术则是为应付考试去猜题、押题,都是将一大堆题型归类,总结成解题术,制成题让学生套模式去做,学生在根本不了解其解题思维的原则下进行大规模操练,只会有弊无利,造成学生学习时间和精力的浪费。而且这种题海战术并不是以达到学生对知识的真正理解为终极目标,而是为了考试需要,可以说是方法不当且操练过度,它使学生的学习活动停留在“重复”、“模仿”,进行“简单再生产”的水平上,从而造成了数学学习的亏缺,“题海”则是对自身造成亏缺的一种补救。如果说“题海”也能训练出“好”的学生,事实并非如此。“好”的学生之所以成为“好”的学生正在于他们冲破禁锢,挣脱出来进行独立自主地思维的结果。对小平邦彦所提倡的反复练习,我们不应将其理解为大捣题海战术,而是为生“巧”而进行的熟练,为培养对数学的感觉而进行的有目的的反复练习。
三、数学的思想、精神和方法
从小平邦彦对数学的理解角度来看,数学的学习是没有捷径可走的,熟能生巧可以说是一条古老而又唯一捷径。然而,从获取知识、通往知识高峰的道路上又是有一些捷径可走的,这便是数学的精神、思想和方法。小平邦彦认为数学学习方法即是反复练习便会不知不觉明白。而由于各人思维风格水平、知识结构和理解能力等的不同,这种不知不觉明白却不是每人都能够体验或经历到的,尤其是一些学困生,他们对数学无论怎样练习,也始终难以找到对数学的感觉。这除了小平邦彦所言及的反复操练以外,还需要把握数学的精神、思想和方法以及一些思维策略上的指导。所谓的数学学法指导意义正在于此。日本数学家米山国藏在《数学的精神、思想和方法》一文中针对许多人感到数学难学的现象,指出数学有两大特征:一是数学逻辑性强,知识系统性强,环环相扣,必须依其道而行。若反其道而行,则无论多么聪明的人都无法理解它;二是为了有助于“人类思想表达的经济化”,数学使用了比其它任何科学都要多得多的术语和记号。数学的这两大特征便决定了数学的学习不仅要依其道而行,使前继知识成为后继知识的生长点之外,还要学会数学交流,能够尽可能完全地理解数学语言。许多同学感到学习数学困难,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把握到数学的这两个特征,因而不懂得提前预习和及时巩固的作用,不懂得去揭示数学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把握其本质。其次在数学中还有一些策略、思想和思维方法,诸如抽象、概括、化归、数形结合、数学模型、归纳猜想、演绎、分类、类比、特殊化和一般化、换元法、待定系统法和配方法等等,以及升格、降格(退化)、缩格(质化)、更格和分格策略,这些用以指导学生有效学习数学的思维策略和方法都值得他们熟练掌握.把握各种策略、方法的内在核心,再辅以小平邦彦所提的反复练习以求得对数学的真正理解,我想这便是小平邦彦所谈的数学学习方法所引发的对我们的启示吧。
小平邦彦:数学的印象
小平邦彦:数学的印象
什么是数学?不太清楚。但我以为关心数学的某些人会有这样的感觉,认为数学实际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本文要叙述一个 数学家看到数学的印象,即像我这样对数学专业以外的事情就不太懂的单纯的数学家,在研究数学时,感到数学是什么呢?我是直率而不加修饰的谈这一问题以提供 读者参考。
一般认为数学是按严密的逻辑构成的科学,即使与逻辑不尽相同,却也大致一样。但是实际上,数学与逻辑没有什么关系。数学当 然应该遵循逻辑,但逻辑在数学中的作用就像文法在文学中的作用那样。书写合乎文法的文章与照着文法去写小说完全是两码事;同样,进行正确的逻辑推理与堆砌 逻辑去构成数学理论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性质。
通常的逻辑谁都明白,要是数学能归结到逻辑,那么谁都应该懂得数学了。但是初中高中很多学生理解不了数学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精通语言学但数学成绩不好的学生不在少数。所以我认为数学在本质上与逻辑不同。
数学
考 虑除数学外的自然科学,例如物理学可以说是研究自然现象中物理现象的科学。在同样的意义上,数学就是研究自然现象中数学现象的科学。因此,理解数学就要 「观察」数学现象。这里说的「观察」不是用眼睛去看,而是根据某种感觉去体会。这种感觉虽然有些难以言传,但显然是不同于逻辑推理能力之类的纯粹感觉,我 认为更接近于视觉。也可称之为直觉,为了强调是纯粹感觉,以下称此感觉为「数觉」。直觉包含着「一瞬领悟真谛」的含义,不太贴切。数学的敏锐,如同听觉的 敏锐一样,与头脑好坏没有关系(指本质上没有关系的意思,而不是统计上没有相关关系)。但是要理解数学,不靠数学便一事无成。没有数觉的人不懂数学就像五 音不全的人不懂音乐一样(这只要担当数学不行的孩子的家庭教师就马上明白。你眼前看到的事情孩子却怎么也看不见,说明起来很吃力)。数学家自己并不觉得如 在证明定理时主要是具备了数觉,所以就认为是逻辑上作了严密的证明,实际并非如此,如果把证明全部用形式逻辑记号写下看看就明白了。那就过份冗长,实际上 不可能(当然不是说证明在逻辑上不严密。而是依照数觉,那些明显的事实就略去逻辑推理而已)。最近每每谈及数学的sense(感受),而作为数学 sense基础的感觉,可以说就是数觉。数学家因为都有敏锐的数觉,自己反倒不觉得了。
数学也以自然现象为对象
把 数学的对象看作是自然现象的一部份,也许有人说这不讲道理,但是数学现象与物理现象同样是无可争辩的实际存在的,这明确表现在当数学家证明新定理时,不是 说「发明」了定理,而是说「发现」了定理。我也证明过一些新定理,但绝不是觉得自己想出来的。只不过感到偶而被我发现了早就存在的定理。
正 如大家不断指出的那样,数学对理论物理起着难以想象的作用。简直可以认为物理现象彷佛全都遵循着数学的法则。而且在许多场合,物理理论所需要的数学在该理 论被发现以前很久就已经由数学家预先准备好了。典型的例子要算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的黎曼空间了。数学对物理如此起作用,其理由何在呢?过去的说法,归结 起来是说数学是物理的语言。也许可以说,如广义相对论中黎曼几何的作用就是一种语言。但是在量子力学中,数学却真起了魔术般的神秘作用,在这里无论如何也 不能认为数学只是语言了。
翻开量子力学教科书,首先看到的是光的干涉、电子的散射等实验的说明,然后表明,光子、电子等的粒子状态可 以用波动函数(即属于某个Hilbert空间的向量)来表示并导出与若干状态的波动函数有关的迭加原理。迭加原理认为,状态A若是状态B与C的迭加,则A 的波动函数就是B的波动函数与C的波动函数的线性组合,它是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
什么叫粒子的状态呢?例如加速器内电子的状态就是由 加速器决定的,所以,粒子状态可认为是该粒子所处的环境。因此在量子力学中就用唯一的波动函数(向量)来表示复杂至极的环境。这里首先是进行简单化、数学 化的处理。状态A是状态B和C的迭加是怎么一回事呢?对于教科书中光的干涉等情形,其意义可以认为是显然的,而在一般场合,却很难理解环境A是环境B与C 的迭加的意义。虽然根据普通观测的干扰可以说不确定性原理,例如不能同时观测粒子的位置与速度,但毕竟不能把粒子同时放在位置观测装置与速度观测装置中。 就是说,粒子不能同时存在于二个环境中。那么什么又是这样二种环境的迭加呢?很难说清楚。另一方面,波动函数的线性组合演算在数学中却是完全初等的、简单 明了的。迭加原理认为,这种简明的数学演算表现了复杂奇怪状态的迭加。就是说数学的演算支配着量子力学的对象即物理现象。明白了迭加的物理意义,就知道不 是用数式表示它,而是把线性组合表示的状态迭加当作公理,反过来按数学演算来确定迭加的意义。正如R.Feynman所说,迭加原理的说明只能到此为止。 只能认为量子力学是基于数学不可思议的魔力。所以我认为,在物理现象的背后在着数学现象是无可争辩的。
数学是实验科学
物 理学家研究自然现象,在同样意义上,数学家研究着数学现象。也许有人会说,物理学家做各种各样的实验,而数学家不就是思考吗?但是,这种情况的「思考」就 是思考实验的意思,例如与「思考」考试题的性质不同。我们知道,对考试问题,只要适当组合某个确定范围内已知的事实,一小时内一定能够解决,思考的对象、 思考的方法都摆在面前。而实验则是为了调查研究原先未知的自然现象,当然其结果就无法猜想,也许什么结果也得不到。数学也完全一样,它是探究未知的数学现 象的思考实验,虽说是思考,但思考的对象是未知的,思考些什么为好也不知道。数学研究的最大困难就在于此。
思考实验中最容易理解的形 式是调查实例。例如考虑偶数最少可表为几个素数的和的问题。检查一下实际的偶数,2是素数不 算,4=2+2,6=3+3,8=3+5,10=5+5,100=47+53,...,总可以表为二个素数的和。由这一实验结果,可以猜想「除2以外的一 切偶数都可表为二个素数的和」的定理成立(这是早就有名的哥德巴赫猜想,现在还没有解决)。如果这样几次调查实例,能够猜想出定理的形式,以后就可以考虑 证明该定理,那么研究的最初难关就被突破了。当然这是数学,光堆积几个实例还不是定理的证明,证明还必须另外考虑。
初等数论些定理就 是首先从这样的实验结果出发引出猜想,然后才证明的。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由F.Enriques、G.Castelnuovo等意大利代数几何学家 得到的惊人成果中,依据实验的不在少数。实际上,J.A.Todd在1930年左右发表的论文中曾明确断言:「代数几何是实验科学」。他们的定理全部得以 严密的证明还是最近的事。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们给出的定理证明还很不完全,但是定理却是正确的。
发现新定理
最近 数学的对象一般都非常抽象,实例也还是抽象的,难以想象,因此靠调查实例来猜想定理的形式,在许多情况下首先就不可能。我不知道在这种状况下,发现新定理 的思考实验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即使说只是含含糊糊地想想思考些什么,恐怕还是不行的。实际就是那样往往是不管怎么去思考都得不到相应的结果。这么说来,数 学研究是不是非常困难的工作呢?倒也未必。有时你什么也没干,但却很自然地接二连三看到那些值得思考的事情,研究工作轻而易举地得到进展。这时感受充分表 现在夏目漱石在《十夜梦》中描述运庆雕刻金刚力士的话上。引用其中的一部份:
运庆现在横着刻完了一寸高的粗眉毛,凿刀一竖起,就斜着从上一锤打下。他熟练地凿着硬木,就在厚木屑随着锤声飞扬的时候,鼻翼已完全张开鼻孔的怒鼻的侧面已经显现出来。看起来他的进刀方法已无所顾忌,没有丝毫犹豫的样子。
「原来使用凿子那么容易,就把想象中的眉毛、鼻子作成了」,他颇为得意,自言自语道。于是,刚才的青年就说:「什么,那并非用凿子作出眉、鼻的,眉毛、鼻子本已埋在木材中了,只是靠凿子与锤子的力量挖了出来。就像从土中挖出石头一样,决不会错的」。
这种时刻,想想这世间没有比数学更容易的学科了。如果遇到有些学生对将来是否干数学还犹豫不定,就会劝告他「一定要选数学,因为再没有比数学更容易的了」。
接下去漱石的话的要点如下:
他便觉得雕刻也不过如此,谁都能干的。因此他想自己也雕个金刚力士试试,回到家,便一个接一个雕刻起后院的那堆木材。不幸的是,一块木头里也没有发现金刚力士。他终于明白了,原来明治的木头里并没有埋着金刚力士。
数学也一样,普通的木头里没有埋着定理。但从外面却看不出里面究竟埋着什么,只好雕刻着看。数学中的雕刻就是一边进行繁复的计算,一边调查文献,决不是简单的。在许多情况下什么结果也没有。因此数学研究非常费时间。可以认为,研究的成败主要取决于运气的好坏。
定理与应用
现 今的数学,由实例猜想定理是很困难的,不仅如此,定理与实例的关系看来也变了。在大学低年级的数学中;定理之为定理,乃是由于可应用于许多实例,没有应用 的定理就没有意义。好的定理可以说就是应用广泛的定理。在这个意义上,函数论的柯西积分定理是最好的数学定理之一。但最近的数学中,有广泛应用的定理几乎 见不着。岂止如此,几乎毫无应用的定理却不少。正如某君不客气地说:「现代数学只有两种,即有定理而没有应用例子的数学与只有例子而没有定理的数学」。从 现代数学的立场出发,「不管有没有应用,好的定理就是好的定理」,但我却总觉得,没有应用的定理总有点美中不足。
数学的唯一理解方法
即 使不作研究,只看看书与论文,数学也很费时间。比如只看定理而跳过证明,二三册书似乎很快就能读完的。但是实际上跳过证明去读,印象就不深,结果一无所 知。要理解数学书,只有一步一止循着证明。数学的证明不只是论证,还有思考实验的意思。所谓理解证明,也不是确认论证中没有错误,而是自己尝试重新修改思 考实验。理解也可以说是自身的体验。
难以想象的是,此外没有别的理解数学的方法。比如物理学,即使是最新的基本粒子理论,如果阅读通 俗读物,总能大致明白、至少自己认为明白了,尽管很自然地与专家的理解方法不同。这就存在着老百姓的理解方法,它与专家的理解方法不同。但是,数学不存在 老百姓的理解方法。大概不可能写出关于数学最近成果的通俗读物。
「丰富的」理论体系
现在数学的理论体系,一般是从 公理体系出发,依次证明定理。公理系仅仅是假定,只要不包含矛盾,怎么都行。数学家当然具有选取任何公理系的自由。但在实际上,公理系如果不能以丰富的理 论体系为出发点,便毫无用处。公理系不仅是无矛盾的,而且必须是丰富的。考虑到这点,公理系的选择自由就非常有限。
为了说明这件事, 把数学的理论体系比作游戏,那么公理系就相当于游戏规则。所谓公理系丰富的意思就是游戏有趣。例如在围棋盘上布子的游戏,现在知道的只有围棋、五子棋和二 类朝鲜围棋只4种类型。就是说,此刻所知道的公理系只有4个。除这4个以外,还有没有有趣的游戏呢?例如四子棋、六子棋、或者更一般的n子棋又如何呢?实 际上下n子棋,当n在4以下,先手必胜,即刻分出胜负,所以索然无味;而当n在6以上时,则永远分不出胜负,也毫无意思。发现这种新的有趣的游戏并不容 易。要找出跟围棋差不多有意思的游戏大概是不可能的。虽然这只是我的想法。数学也同样,发现丰富的公理系是极其困难的。公理系的选择自由实际上等于没有。
理论的丰富推广
数学家一般都本能地喜欢推广。例如假设存在以某个公理系A为基础的丰富的理论体系S。这时谁都会想象 到,从A中去掉若干个公理得到公理B,从B出发推广S得到理论体系T,再进行展开。稍加思索就觉得T是比S更丰富的体系,因为T乃是S的推广,但如果实际 试验一下这种推广,许多场合与期待的相反,T的内容贫乏得令人失望。这种时候,可以说T不过是S的稀疏化而不是推广。当然并非所有的推广都是稀疏化。数学 从来是依据推广而发展起来的。最近推广不断堕入稀疏化,倒不能说是一种奇怪的现象。
那么,能发展成丰富的理论的推广,其特征是什么 呢?进一步,公理系能作为丰富的理论体系的出发点的特征又是什么呢?现代数学对这种问题不感兴趣。例如,群论显然是比格论更为丰富的体系,但群的公理系优 于格的公理系之点是什么呢?又在拓朴学、代数几何、多变量函数论等等中,基本层的理论的出发点(看来似乎)是毫无价值的推广,它不过是用及数替换以前的常 数作为上同调群的系数。而实际上却是非常丰富的推广,其理由何在呢?与此相反,连续几何被看作是射影几何的令人惊叹的推广,但却没有什么发展,这又是为什 么呢?当把数学作为一种现象直接观察时,所产生的这类问题不胜枚举。虽然我并不知道,它们是否都是不屑一顾的愚蠢问题,抑或能否建立一门的回答此类问题为 目标、研究数学现象的学科,即数学现象学呢?但是如果能够建立,那一定是非常有意思的学科。为了研究数学现象,从开始起唯一明显的困难就是,首先必须对数 学的主要领域有个全面的、大概的了解。正如前面说的,为此就得花费大量的时间。没有能够写出数学的现代史我想也是由于同样的理由。
小平邦彦简介
小平邦彦(KodairaKunihiko)是日本数学家,1915年3月16日生于日本东京。
1985年荣获沃尔夫数学奖,时年70岁。
主要成就:他对复流形、代数几何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数学乃是按照严密的逻辑而构成的清晰明确的学问。”
--------小平邦彦
“数学就是研究自然现象中的数学现象的科学”
--------小平邦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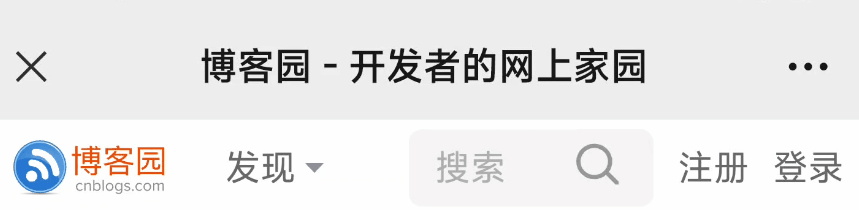
【推荐】国内首个AI IDE,深度理解中文开发场景,立即下载体验Trae
【推荐】编程新体验,更懂你的AI,立即体验豆包MarsCode编程助手
【推荐】抖音旗下AI助手豆包,你的智能百科全书,全免费不限次数
【推荐】轻量又高性能的 SSH 工具 IShell:AI 加持,快人一步
· 开发者必知的日志记录最佳实践
· SQL Server 2025 AI相关能力初探
· Linux系列:如何用 C#调用 C方法造成内存泄露
· AI与.NET技术实操系列(二):开始使用ML.NET
· 记一次.NET内存居高不下排查解决与启示
· Manus重磅发布:全球首款通用AI代理技术深度解析与实战指南
· 被坑几百块钱后,我竟然真的恢复了删除的微信聊天记录!
· 没有Manus邀请码?试试免邀请码的MGX或者开源的OpenManus吧
· 园子的第一款AI主题卫衣上架——"HELLO! HOW CAN I ASSIST YOU TODAY
· 【自荐】一款简洁、开源的在线白板工具 Drawn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