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天缺
我从很久以前就想要写一篇以此为标题的文章, 这个标题可能是大一甚至高三的时候就想到的. 但囿于各种原因没有完成. 本来想要写一个寓言故事, 但数数曾经寓言故事写了那么多, 也没有再写的必要了. 我表达欲最强的时候往往并不能真正输出 --- 那常常是我躺在床上睡前的时候. 要打起精神找一个时间, 既能够保持着能量和对世界热切的期盼, 又尚能记得对自己感到困惑时深入骨髓的反省, 这样的时候并不多. 我希望能抓紧这样的机会赶紧记录下自己的想法.
作为一个渴望创造的人, 当我学习那些前辈创造的工具的时候, 不仅想要掌握这些观念和技术, 也不能停止好奇他们何以创造出这些理论. 然而, 纵使是非常伟大的思想, 冷却到今日的教科书上的时候, 也是经过后人反复雕琢改进, 重新表述的. 历史的风沙具有的力量如此之强大, 它所吹拂之处, 所有伟大的思想, 亦或是炽热的愿望, 纵使自身大体的轮廓无法被撼动, 但细节之处终究会面目全非.
到头来, 得以完好无缺保留的, 倒是人们真实的情感表达, 表达自己的生命如何与愿望做的事情结合在一起. 诚然, 情感表达总是要有些极端的, 信念倘若照搬, 是要碰得头破血流的. 可我想起小时候看的一部漫画中的一句话, "但人生要没有些傻乎乎的话骗自己, 是否连站起来骂的勇气也没了呢?" 在这方面我倒是有点羡慕做文学和艺术创作的人: 再创作是再创作, 但原作的文字或画面终归是无可替代的 (翻译成其他语言那是另一回事).
我和不同的人相处交流似乎表现出不同的性格, 但并非我想隐瞒什么, 其实是气氛所致. 所以, 无论是我博客的读者, 还是我的以何种方式结识的朋友, 或许终归是对我有所疑惑的, 感觉并未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我. 世上的疑惑太多, 难以尽数消解. 就像我的生命中似乎也有难以解释的疑惑. 譬如说我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初中考元培班的时候感觉自己平面几何一败涂地了, 后来老师却说我数学考的是挺好的. 又例如我也不明白我一位每天早上六点钟就起来伏案工作的亲人, 倒觉得我的学习工作辛苦了.
这也是我想要写此文的原因之一: 也许看完我的一些碎碎念, 诸位能够稍微对我多一点理解, 或者未必要理解我, 至少知道我为什么会是这个 (?) 样子. 事物总有阳的一面和阴的一面, 所以我并不打算避讳. 即使是阴面, 我也尽量保持自己是在能够维持对于世界充足的善意的时候写下这些文字. 但或许总难免会有难以忍受的桥段. 如果你读到感到不适的地方, 请记住我的警告和提前支付的歉意, 可以立刻停止, 跳过或退出本文.
学校
我并非生来就是想要投身于形式科学, 正如然然 (额, 虽然但是, 我们下文就这么称呼好了) 最初也不知道自己会成为 OI 教练. 我还依稀记得初一的时候见到的然然, 当时学校有个叫 TIC 俱乐部的东西, 占据一个周末上午的时间, 然然也刚到北大附中当老师. 当时教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蚁群算法云云, 还有记得的就是有节课然然在课上给大家放电影 "楚门的世界".
后来学校要发展学科竞赛, 这个俱乐部改成 OI 相关是后来些的事, 再后来初三的时候然然给大家放了一个特奖答辩的视频 (显然大家知道这是指谁), 答辩里那一句 "我要成为理论计算机科学家" 的话后来才逐渐让我想起小时候的一些想法.
学校的数学老师不仅教授数学课, 也在每周的某天中午在学校的生物教室开设一个叫做 "妙趣数学撷英" 的小讲座, 我是那里的常客之一. 涉及的都是一些不太困难的主题, 也是我第二次知道 Polya 的 "谈谈方法" 的地方.
学校里还有一个叫做 Iris 的学长 (好吧很多人的 id 都叫 Iris). 除了在学校里留下了一些神奇的传说外, 我也有幸从他那里感受到他对于数学的如火的热情. 我大概听他讲过两次讲座, 一次是和 Polya 计数定理有关的. 彼时我倒是已经相当理解这个定理了, 但依然从他的讲座中学到了很多. 一者是他板书和讲解时如痴如醉的状态, 二是谈论后来关于在 20 世纪, 人们关于有限单群分类定理时辉煌壮阔的历史. 另一讲座是类比数学的发展和艺术史之间的联系, 还让我知道了一本叫做 "集异璧" 的书, 可惜后来我也没读过. Iris 后来去国外念书, 中途从数学转成了文学, 但兜兜转转似乎又回到了数学.
现在想来, 我对于形式科学的态度有很大程度上是收到了这些人的影响的. 当然, 还有一些对我同样巨大的影响, 我只能将其概括为, 被刻进我骨髓中的 "象牙塔" 的某些特质.
艺术
我希望我所作的事能够承载我对于艺术的理解, 即使我大概要从事形式科学. 纵然, 这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艺术的表现形式, 更没有艺术技法, 那我所自认为要承载的是什么呢? 大抵只能说是我对于 "艺术" 所希望诉求的内核所非常私人化的理解. 我宁愿相信人有能够多数达成共识的对于 "什么是美" 的产生共鸣的能力. 我希望我的创造能够承载我对于世界的热切的盼望, 一个是对于创作的事物本身, 一个是如何将我的生命和整个创作的过程相结合.
当然, 为了后者这个目标, 我所过的生活有时确实有些抽象了. 曾有段时间, 我对于学习以外的事物进行着刻意的控制和重复, 现在倒是好一些了.
回到标题, 这大概就是曾今我什么想到了 补天缺 这个词. 我仿佛总觉得, 那些人类想要知道却尚未知道的事情, 就像是远古神话中天空破缺的一个大洞. 这个创口永远不能被人们一劳永逸地填补, 但对它的追求, 对于消除内心的那种未知, 彷徨, 痛苦和不安的愿望, 却足够成为人类世代生生不息, 千万往以的原因.
但创作和创作究竟是不同的, 请允许我再做一个私人的比喻. 我愿意相信, 人们之中最为热情纯粹的那些人, 就像是手捧着一团不灭的火焰. 有的创作像是把这团火投放到一片草原上, 让它点燃, 灼烧一切, 唤醒我们周围的所有人. 而有的创作像是用火的热量铸成一把剑, 趁着余温, 向面前一堵冰冷而坚硬的墙体挥去, 试图在这堵墙上打开一丝裂痕. 不错, 曾经早就有人将这样一堵墙 --- 这样一堵坚硬, 冰冷, 难以打破的墙, 比作死亡. 这样一种创作的愿望, 就像是对于生命的力量的宣誓, 对于死亡 --- 人面对有限的生命所不得不承认的, 对于世界的有限的理解和挑战的能力 --- 的超越.
信念
我亦希望我所作的事能够承载人对于 "解决问题" 这件事本身的信念的理解. 我小时候被安利了笛卡尔的 "谈谈方法", 还有 Polya 的 "怎样解题". 所以我会在个人介绍, 以及书桌前贴一张我魔改的 "问题解决的指导原则". 在现在我思考问题一筹莫展之际, 也至少我会想起一些最基本的话在脑海里回想, 诸如 "从最简单的例子出发" 云云.
诚然, 试图遵循死念教条是难以前进的. 但我确实难以割舍人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这种所谓 "理性" 的光辉. 这种 "我们必将通过我们所守的基本原则, 完整探索我们所知的所有真理" 的信念, 一直到 Hilbert 那句著名的 "我们必将知道, 我们终将知道", 也可以看做这种信念的延续.
我感到幸运, 我至少具有基本的成熟度来用空余时间理解逻辑学内部对于这种信念的反思, 而不是仅仅受制于科普文章经过简化的模棱两可的概念. 用机械方法来探求所有真理的尝试固然是被粉碎了, 有的命题的真值亦可以在不同的相对化的世界有所改变, 一个柏拉图式的绝对的真理世界仿佛也不复存在.
但这就回到了我对于形式科学的欣赏. 初看, 形式科学的发展总是让人失望的. 人所作的定义, 似乎总是玩具的, 有失偏颇的, 不足以捕获整个现实世界的. 从这些定义和理论出发, 有时候能获得惊人的结果. 这说明它所试图描述的那个现实被得到的结论覆盖了吗? 并没有.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只是在做游戏, 或者我们一无所获.
我们对于现实的理解, 本身就在被我们所重复使用的语言所重新塑造. 科普内容看多了, 常常让人觉得世界是这样便就是这样的, 一个问题解决了, 就是得到最终答案了, 世界就和平了, 人们就幸福了. 但所有对于概念的分析基本上都不会导向如此的断言, 而是时刻提醒着我们, 要么我们不知道, 要么我们的描述是需要重新对齐的. 魔鬼仿佛向我们发出嘲笑: "你想杀死恶龙, 之后获得永远的幸福吗? 做梦去吧!"
可是, 这真的不是幸福吗? 我们的接力棒最终还是落到了自己的手上. 如果事情不能脱离我们自己对于认识的修正而得到解决, 那么我们永远不会停止思考, 不会停止让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更加增长. 面对那个永远不能填满的洞口, 我们永远都有事情做了.
我们再回到前面的问题, 那些 "从简单的例子出发" "泛化" "寻找联系" 的道理, 现在还有人不知道吗? 反复强调这些还有意义吗? 在探求道理的过程中, 总有些问题是用这些方法可以探索干净的, 也自然剩下一些看起来解决的手段更加清奇惊人的. 但毕竟, 希望是不可以没有的, 如若不相信我们可以用 所有人类可资调用的手段 去解决问题, 那我们还期盼什么呢?
也正因此, 我不断地驱策自己, 不希望放过任何自己可资调用的手段. 我希望自己在 "鄙视链" 中不卑不亢, 只是基于自己不断的学习, 和经验还有信念去判断, 什么才最接近真相. 我希望自己不放弃从尚未关联起来的事物之间试图寻找到新的联系. 我希望自己不断重新思考那些已经放在那里很久的问题, 检查是否有被遗漏的想法.
OI
我显然无法绕过 OI 谈论我对于世界的理解.
毕竟很长一段时间内 (也即中学时期) OI 都是我思考的核心主题. 由于和然然白手起家, 筚路蓝缕, 学校资源基本上只有 noip 难度的模拟赛题. 而且出于某些原因, 我后来大部分时间的工作方式都是以个人为单位, 孤独地对着公开的省选题一个一个啃. 我心里默念着那些我所铭记的准则, 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整理一切, 然后靠运气进了第一次集训队.
我最难以渡过的时间甚至不在进集训队之前, 而是在第一次进集训队和第二次之间. 可能是这个时候我才逐渐开始触碰到单凭着这些信念还不足以跨越的事物. 就像是之前提到的, 第一次摸到自己面前有一堵墙. 或许人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墙的时候, 没有经验, 难免情绪激动, 感到失望绝望.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被安利了 "约翰克里斯朵夫", 导致症状有所好转. 那句安慰我的话是如此说的:
你得对着这新来的日子抱着虔敬的心. 别想什么一年十年以后的事. 你得想到今天. 把你的理论统统丢开. 所有的理论, 哪怕是关于道德的, 都是不好的, 愚蠢的, 对人有害的. 别用暴力去挤逼人生. 先过了今天再说. 对每一天都得抱着虔诚的态度. 得爱它, 尊敬它, 尤其不能污辱它, 妨害它的发荣滋长. 便是像今天这样灰暗愁闷的日子, 你也得爱. 你不用焦心. 你先看着. 现在是冬天, 一切都睡着. 将来大地会醒过来的. 你只要跟大地一样, 像它那样的有耐性就是了. 你得虔诚, 你得等待. 如果你是好的, 一切都会顺当的. 如果你不行, 如果你是弱者, 如果你不成功, 你还是应当快乐. 因为那表示你不能再进一步. 干吗你要抱更多的希望呢? 干吗为了你做不到的事悲伤呢? 一个人应当做他能做的事. ...... Als ich kann (竭尽所能).
是吧, Als ich kann. 不过当时我没读多少, 后来把这本书补完是等到 20 岁生日之前几天了.
后来我用高三的时间以比较极端的力度试图探索各种 OI 相关的数数问题, 也算是有所收获. 尽管如此, CTT 上还是发挥出了
我知道我很容易计算出错, 所以我许多时候都是反复地算, 算多遍, 像没头苍蝇一样试探不同的可能性, 最后才搞明白标准的道理应当是如何. 记得小时候有计算错误不以为然, 亲人严肃地跟我打个比喻: 假设你是一枚火箭的工程师, 你在小数点后第几位出了一个错误, 就因为这一个错误, 火箭发射失败了. 小时候的我想到此时, 不仅自责地流泪. 如今我依然很容易把东西算错, 但没关系, 我会一直试, 直到算对, 有一次算对就够了, 只要最后算对就够了.
归根到底, 我唯一的截止时间只是自己的生命.
我也享受将一副美丽的画卷向他人徐徐展开的过程, 或许这加强了我想要同时成为一名老师和理论工作者的念头. 或许在这方面 OI 对我影响很大, 当然还有一些耳濡目染的原因.
人类
或许我是个很无趣的人, 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我对人类仿佛也有着 diao1 钻的要求. 每当我得知一件事, 我总要用我对于人类的理解来评判这件事是当做还是不当做的. 如果不当做, 那把这件事扔到垃圾堆里, 再也不关心. 如果当做, 那就是我也当做的, 于是给自己不断加码.
诚然, 我知道人是总要做选择的. 所以我试图把具体的东西都转换到抽象的层面上. 譬如道德, 譬如生活的姿态, 譬如对于劳动的态度 --- 也即我所谓的 "艺术".
即便如此, 我也清楚自己本身在脱离轨道. 我知道人维持合理些的作息是好的, 所以我用 "我要以大哉死的态度在有灵感的时候就思考问题" 把这问题搪塞了. 我知道人应当多运动, 读不同的书, 所以我用 "我怕错过必要的手段" 搪塞了.
归根到底, 我大抵尚未在 "贯彻生命的对于创作的斗争" 与 "维持人类完整的形态" 之间找到可行的平衡, 因此开始质疑后者的必要性来. 也许只是我现在的安全感还过于缺乏导致的.
还记得初三的时候语文课上讲了一点存在主义, 让大家读了一点加缪, 还有 "悉达多" 什么的. 结果兜兜转转, 也许是因为已经习惯了, 我最后还是懒得欣赏关于 "人生没有意义" 这些说辞. 但或许其实是我比较幸运, 有足够的资料来武装 "给自己赋予意义" 这一目标, 到头来我所宣誓的似乎总是古典的, 具有中心的那一套, 时而膈应他人.
似乎中学的时候有一天思考什么是信仰, 后来在心中立下了自己 "不会幻想, 不会祈祷" 这样同样中二的言论. 但现在回想起来, 那时的结论尚未经历足够严酷的考验, 以至于我最近越发动摇. 如果要我现在来说, 大概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信仰者要比一个不加反思的, 主张万事皆空的人更加真实. 这世界上的信仰并不局限于所谓勾勒出的关于神的故事, 无论是信徒, 还是主张科学的人, 还是献身艺术的人, 还是相信只靠技术就能改变世界, 还是从政者, 并不只因为这一个立场就能决定本身的性质, 同类型之内依旧对于世界各有各类型的影响. 如果最终是为了汲取精神上的力量, 对世界和他人展现善良和关爱, 那便这样好了.
太阳
我有点忘了太阳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了. 可能一个原因是 id 缩写成 EI 之后有人读成日, 也有可能是有些把别人叫 "红太阳" 的传统.
但好像不知道哪天开始, 我好像真的开始认真思考这个概念. 我想要能够解答大家提的一切问题, 希望能够觉察照顾他人细小轻微的情感, 希望将我所主张的 "希望" --- 我对于世界和命运的理解方式 --- 传递给他人.
后来我又编出一些其他概念, 什么 "偶像" 之类.
一年多前, 回想起来我确实不算虚伪. 我认识的一个人在对我剑拔弩张, 发出威胁的时候, 我虽然一方面确实担心自身的安全, 但即使在这个时候, 我也在考虑如何和平地让对方走出困境.
但即使如此, 我也很难一直保持这样的精神力. 归根到底,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愿望呢, 真的只是我自己想要这么做吗?
当我回想, 时至今日, 其实仍然能想起四年前 (还是五年来着?) 的某个下午. 我被人指着鼻子质问的那一天, 周围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迫于威压, 没有出声. 也许这才是我试图察觉他人任何细微情感的原因吗? 我按照自以为的关心方式, 在说话之前预先推演所有人可能的反应.
我十分清楚, 有时我的各种类型的情绪会涌上来: 轻蔑, 嫉妒, 愤怒, 绝望, 或者对 "他人凭什么能玩世不恭" 感到不公平, 云云. 但最终这些念头大多都没有发作过. 有时我会回想起很多年前的那个下午, 人的脸仿佛就像一盘黑白棋, 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 让颜色说翻就翻. 冷静下来, 要爱, 要善良, 我不断地告诉自己. 最后我把所有不可撤回的决策都咽回了肚子里, 最多表达一些非常隐晦的意思. 看起来, 最终还是我的 "理智" 获得了胜利, 以杀敌一万, 自损九千的方式.
有时候我会因此感到遗憾. 我似乎不是依靠直觉来当一个善良的人的人. 我的面前总是浮现出茫茫多的选项, 要打起精神来否决掉那一个个糟糕的选项, 最后留下那个最柔和的办法. 我只能这样勉励自己, 至少我在绝大多数时候都尽力了, 既然我知道要选择, 说明我还是知道良知应该是什么样子.
即便如此, 我至今也未太学会面对他人的情绪, 不过我仍然会努力的.
情感
正好记得这学期心理课的老师提到过的, 人的情感有时候像一条波动的河流, 人可以选择在河流里感受剧烈的流动, 但如果尝试把自己抽离出来, 站在岸上观察自己的情绪, 便能更好地控制了.
讽刺的是, 回想起来我一年多前倒还是无师自通地掌握着这种技术, 但到这学期上课的时候, 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回想起这种方法了.
有时我会感觉我构建出的一切实际上是极度脆弱的. 常常将一座玻璃雕塑一点点地搭建起来, 然后再一锤子将整体砸碎. 幸运的是, 这雕塑中心终归是有一个及其坚固的内核 --- 我对于创作的渴望和希望, 它让我在其它许多事情都仿佛被摧毁的时候, 依然支持我爬起来维持日常的行为, 从学习和工作中缓解痛苦.
我还记得有时他人给我的博客抓 typo 时候的烦躁, 难过甚至崩溃 --- 当然, 不要因为这个就怕给我的博客抓 typo 啊! 只是因为我对于所有的创作: 无论是写东西, 还是给他人讲述, 还是试图找寻之前从未有人见过的景象. 我把它们放在了和我生命如此紧密相连的地位, 以至于容易因为错误而对自身感到失望.
不过那又如何呢? 我仍然试图保有对自己对 "艺术" 的理解的一点执拗. 倘若人不对事物保有一点神经质的, 对于未曾填补的缺口那里感到的烧灼感, 又如何将愿望延续一直到生命的尽头呢?
心理课上, 老师曾经提及过这样一个实验. 对于刚出生的婴儿, 如果有哭闹的情况, 有的家庭遇到孩子哭闹就会毫不犹豫地抱起来哄, 而让另一组家庭遇到哭闹的时候就关掉灯光, 一家人一齐躲起来, 让小孩意识到哭闹就会在孤独的黑暗中独自度过. 当两个婴儿长大之后, 后者真的会不再哭闹了, 即使自己摔伤流血了, 也一声未吭. 但再往后, 他们会怎么样呢? 课上没有说.
我有时会偏执地以为, 具有更加细微的感受痛苦的能力, 我也应当为此而感到庆幸. 我不断地升起那些对世界过于殷切的希望, 然后因为这些希望被摧毁, 或者自省发现错误而感到痛苦. 在痛苦的海浪平息之后, 我又看到一轮新的太阳缓缓升起, 承载我对于世界的新的希望. 我不断颤栗着, 颤抖着, 希望在不断的轮回之中, 能够补上一点世界或我生命的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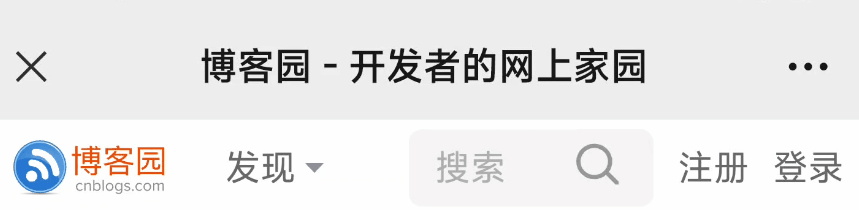
【推荐】国内首个AI IDE,深度理解中文开发场景,立即下载体验Trae
【推荐】编程新体验,更懂你的AI,立即体验豆包MarsCode编程助手
【推荐】抖音旗下AI助手豆包,你的智能百科全书,全免费不限次数
【推荐】轻量又高性能的 SSH 工具 IShell:AI 加持,快人一步
· winform 绘制太阳,地球,月球 运作规律
· AI与.NET技术实操系列(五):向量存储与相似性搜索在 .NET 中的实现
· 超详细:普通电脑也行Windows部署deepseek R1训练数据并当服务器共享给他人
· 【硬核科普】Trae如何「偷看」你的代码?零基础破解AI编程运行原理
· 上周热点回顾(3.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