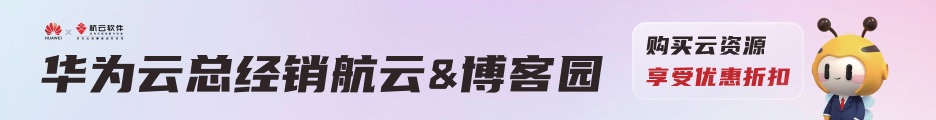绽放生命的炫美
我打小就知道地球是圆的,地球会转,这叫定律;也知道人的意志就这么脆薄,你改变不了下一秒内许多人的降生,像你阻挡不了下一秒内的老化和死亡。我在幼儿园里已学到生而为人的全部道理,而我花一生去领悟、应用,痛彻心扉。所以我开始到了这通俗而敏感,为各路艺术家百般称赞的纠葛青春年华,终于有点思想而不单是苇草一支。葱茏年华的人儿们长得畸形,神经装在皮肤外,血肉剥露,一点温柔爱抚都可变成电击麻痹,血涌成河。
你知道我感觉自己软弱又不堪一击。
我有梦想,我很主动,在呼吸;我很倔强,甚至想对困难反手回攻,虽然有时像极了孩童对石雕的张牙舞爪。我可以午夜起身到阳台深吸一口混杂泥土、叶的呼噜和鸟呼吸气味的空气,我至少是对美好有强烈的欲望与感受力。我没有进入到社会,我的心是一团棉绒,它是要被捶打的——而我现在竟已能对微小刺激痛哭流涕。
因为人是血肉之躯。
血肉之躯。
他们都说人,渺小又伟大;人就是因为这样的正负极,才会变得神秘又绝美。我感觉他们也是伟大的——他们要有怎样绝地的勇气,才会淘沥出伤痕累累的心,吞言咽理地给人希望。而我顿觉发言无力,我不能说,进入社会后被困难变成铁石心肠的人是失败的!被困苦变成随遇而安的人是失败的!只有追求自我并适应其中的人才是成功的!是谁给了我这傲视群雄地勇气,让我高傲地流露这上帝视角的话语?纪伯伦在说:你是谁,能够敞开别人的胸膛,践踏他们的尊严?我在说:我是谁,能够予别人以淳淳教导——我甚至是如堕烟海的迷失者啊!我现在从书里看到的知识,有别人的基因,他们被我的身体器官拒以千里。没有经验就不要纸上谈兵。不要再逞口舌之快了——我告诫自己——不要教导别人。
我是胆小的人,每每思至此,思路便断线,像断的铅笔头。
我感到自己很害怕也很无助:我尚未走进社会,便已神经质得如此忧伤。那么以后呢?以后会怎样?我从不拒绝被洗炼、灼烧和熔化,我希望自己要有永恒的梦,要有反抗的筋骨,谁曾讲过反抗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但,并不是谁都那么坚强和硬朗,像美的戏。
你的眼罩下有细密光点的流渗。
——我许诺我将看见。
然后我在慢慢地看见坚韧的人性,我知道我看见的光点连线,线连面,网织天上人间。人性的温润、坚韧与顽抗总令人忆起冬日火光——我在火光里看见了更多,更多人的面庞。我曾经惊异,为何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未出温室而孕育的自称温和的感情,却比不上一个在社会摸爬滚打、磨平棱角的人的善心所产生的淳厚温情?有时形容父母之爱的文辞俗而孱弱;或许正因为心灵的挫伤愈发深沉,那情感与宏大力量更是令言辞难以承载。你说我要走出,我当然也强迫自己走出——可是何为走出?我是否真正陷入?我目标的成功,世上大多数人的成功,真的是要拯救世界,特立独行,要比镁光灯的强光更加夺目吗?英雄只是被彰显与夸大的成功者。成功的人不过是被世界改造,便愈发坚韧顽强,更加要从火里沥出烫而美的真心,即使是泪水涟涟也要呈现给世界看的。
“血流得越多”
“颜色愈是深沉的。”
可我仍感觉我的文字,这么羸弱。不过我又想起了一位江西的老师。那天是学校开放日,许多外地老师前来听天文讲座,我和几个同学坐在图书馆门口探讨社内征文事务,机缘巧合,几位老师恰好走出,听见我们的谈话,便饶有兴致地与我们讨论起有关两代隔阂、应试教育、世界进步等更加宏观,实则切合严密思考的问题。那时那位来自江西的女教师这么说:
”我只是一名大学老师,但我仍在全国,甚至到国外大学去开讲座,力图改变中国应试制度。我感到我们国家需要创新人才。我感觉只要我改变一个人——即使我改变了一个人,我也是伟大的。“
那个时候是我的低谷。我曾沉重地错过了一个人的手。
我是否漏听了什么,才触发泪腺机关;
我感到身体里一根弦断了,以至于潸然泪下。
是的,不能否认,生活就是社会,我一直被改造,被肢解,拼接,我变得残缺,感到血在流失。可我仍有那么大、那么大的梦想,它很鲜活,很生动,很顽抗。可我仍有一颗真心——即便在此刻它是裂纹纵横,它也未被摧毁,即便我泣涕交横
也要拎着它给世界呈现光亮。
我的梦想这么简单:即使前方是困苦的未知,即使我在此刻的成长里找不到自我,我也不要辜负那些爱人的人和我爱的人。终有一日我要找到自己,我要舒展开来;我要用我的枝蔓改造世界。我要绽放生命的炫美。
来自一期校内报刊,尚未联系到作者LZM,谢绝转载。